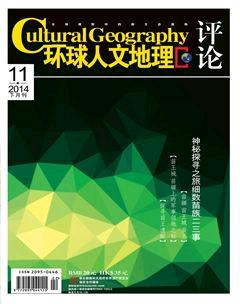人類學紀錄片《最后的山神》的人類學思想
摘要:人類學紀錄片是民族學紀錄或者民族志紀錄片,是對民族文化進行記錄的一個文化現象。《最后的山神》表現老一輩鄂倫春人的傳統的山林生活和心靈世界,反映出山林狩獵這一人類童年時期的生活方式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將最終消失的命運。人類學紀錄片就是對這方面進行搶救的獨特方式而存在。通過其真實的記錄讓人們去反思,分析傳承交流文化價值、濃厚的審美藝術價值以及引領觀眾的社會價值。
關鍵詞:人類學紀錄片;最后的山神;文化內涵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說過,文化是公眾可獲得的符號形式。人類學紀錄片所承擔的就是文化責任。紀錄片以媒介的形式記錄人類的不同文化,并非只是簡單的說教傳播,它通過最為真實的畫面聲音對人的內心產生強烈的沖擊,從而引導人們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關注。人類長久以來都認為高大的山中是神靈所棲的地方,如羅馬的朱庇特、猶太的耶和華、北歐人的奧丁都在山上。《最后的山神》便是中國鄂倫春族對山神的崇拜。
在《影視人類學概論》當中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人類學紀錄片是科學成果以及藝術形式的一個完美的結合,是紀錄片的手段在人類學研究中進行運用,以記錄作為表現內容的一個形式,而人類學則是內在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人類學的研究成果。”[1]由于在速度上比較快或者是事物比較小,這對于人們的觀察以及通過文字而無法進行準確的把握的時候,人類學紀錄片就成了這一時刻的關鍵記錄工具而存在;另外就是人類學紀錄片是在共時性以及跨文化的對比以及歷史性的文化變遷的研究過程中進行的運用。
一、《最后的山神》的簡介
鄂倫春民族自古是一個崇拜大自然的民族,信奉的是原始自然宗教。由于他們世代在大小興安嶺的原始山林中狩獵捕魚,所以他們把山神供奉為保障他們衣食的最主要的神靈。因此,老薩滿雕畫出來的山神像在他眼里就不再是現實中一尊古樸的偶像了,而是一種象征、一種意蘊,一個濃縮鄂倫春民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形態等諸多社會因素的象征體。
紀錄片是一門現在進行時的藝術,要表現鄂倫春民族的過去,只能通過圖片資料、當事人的同期聲回憶及解說詞旁白介紹等方式。天賜良機,編導發現了一位恪守先輩遺風的老薩滿及他頂禮膜拜的山神像。[2]于是,鏡頭把觀眾的視野引向了鄂倫春民族歷史的縱深。
二、人類學的運用
(一)萬物有靈觀
孟金福確信自然萬物是有靈性的。正月十五需要拜月神。他每次狩獵,都要對山神頭像頂禮膜拜地叩首祈禱。更多的場合,山神在他心中,是神靈與人性混為一體的情感在支配他的行為。比如,他發現冰雪覆蓋下的小草,總要帶回到他的“仙人住”窩棚里給老伴看,他們喜愛綠色。他不肯換新式獵槍,不肯下套子捕獵,怕誤傷了年幼的動物,這是山神不允許的。他有意用大眼漁網打魚,為的是讓小魚跑掉。總之,這就是孟金福——鄂倫春民族最后一位薩滿的個性特點。他是鄂倫春民族僅存的一位能通神的人。
(二)對神靈的敬畏
孟金福的母親是鄂倫春族最高領者,她知道很多關于山神的故事。當編導詢問有關神靈之事時候。她卻閉口不談,她說那是神靈,是不能隨便討論的。當兒子為編導跳薩滿時,她說沒有神了。薩滿是鄂倫春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領袖。薩滿溝通人神的作用主要是以跳神的形式出現的。在跳神過程中,薩滿被神“附體”后,薩滿的說、唱、舞等動作通常就被看作是神的旨意。在跳神的過程中人們將自己的心愿和要求告訴神,而神則通過薩滿之口發布自己的指令。在老一輩的鄂倫春族人心里是存在敬畏之心的。當新的生活方式不斷的對傳統進行沖擊后,樹林越來越稀,獵物越來越少,山神離他們越來越遠。
(三)對樹的崇拜
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茂密,是中國主要的林業基地。森林為居民提供了燃料、食物。他們的生活與其有密切的關系,將樹木視為崇拜對象也就成為了可能。在沒有人創造廟宇之前,人類就用森林當廟宇的祭司的。英文中廟宇(temple)的意思就是樹木。孟金福每到新的地方狩獵,總要揀一棵最粗、最直的樹砍出白茬,用斧子和木炭雕畫出一個山神頭像來,然后頂禮膜拜。狩獵成功后會將食物放入山神的嘴中,與其分享。既是沒有獲得獵物也會對山神頭像進行膜拜。在做樺皮船時候,割樺樹皮,他總是特別的小心,怕傷著樺樹的木桿,為的是使樺樹來年能長出新皮。[3]當他看見畫有山神的樹木被砍伐所表現出來的傷心、落寞是直擊人心的。在它看來樹是有生命力的,它們也會感到刀割的痛苦。神靈寄居于木中,對樹的砍伐也就是對神的不敬。一旦樹死,靈魂便消散。《最后的山神》讓人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鄂倫春人對樹的敬畏,對山神的崇拜。
(四)風葬
風葬是鄂倫春族的傳統,神秘而隆重。他們認為只有風葬才能使靈魂隨風飄回山林。在《最后的山神》里一位老人逝世,孟金福為其舉行了風葬。而在《最后的薩滿》中孟金福去世,沒有人再懂得風葬的具體儀式,為他人進行了一輩子風葬的他,最后不得不掩埋在黃土中。這就是讓人覺得最痛心最悲哀之處。
三、最后的山神
在展示這對鄂倫春民族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活標本”時,首先是把他們作為一對洋溢著生機、充滿個性活力的鄂倫春族人的老夫妻來描繪的。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孟金福,是一個在不同場合充當不同角色,呈現不同性格內涵的鄂倫春老人。他敦厚善良、平和而又固執,虔誠而又驍勇。他就是他,一位做過薩滿的鄂倫春族傳統獵手——孟金福。他又不是他,因為他和他所信奉的山神一起被攝人了攝像機,被賦予了形而上的內涵。他便從一個有血有肉的孟金福被升華成為一種象征,象征著已經結束了的鄂倫春民族的舊時代。于是,孟金福又變成了一個視覺性符號——最后的山神。
通過孟金福一家老幼之間的思想碰撞、對過去的依戀和對未來的向往,表現了他們從傳統的山林文化向現代文明的轉化過渡,揭示出鄂倫春人的內心世界。社會在前進,文明將占領任何一個角落,鄂倫春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改變,這種改變與人們思想上的演進和沖突有機地結合起來,給人以深刻的啟示。作品后半部分,老薩滿孟金福的侄女現代化的穿著和她在接受采訪時流露出的想回來拍山林里動物,以及孟金福的小兒子隨父親去打獵卻連馬都上不去,孟金福敬山神時他又表現得心不在焉、東張西望等鏡頭所謂抓拍,新一代鄂倫春民族的精神面貌、志趣愛好略見一斑。鄂倫春人順其自然地向過去告別。他們崇拜森林與山神,但如果說有山神的話,孟金福就是,他的子女是不會再過這樣的生活了,可以說這位老獵人就是最后的山神。endprint
四、人類學紀錄片的意義
在孟金福夫婦的心目中,山、林、水、火、日、月自然萬物皆有神。他們自認為是山林之子、自然之子,每到一處總要在樹上刻下一尊山神像,祈求保佑,祈求山神與他們共享歡樂,分擔不幸,還時時給山神敬煙、喂食。這種行為模式,從人類文化學上說,都是文化心理的外顯形態。所以,當他們發現一尊山神像被砍伐之時,便默默坐在禿樹兩旁,相對無言。此時,編導用了一個有剪影效果的較長固定鏡頭,把他們內心的哀傷與痛苦表現俱足。主人公上述活動都是在高寒的林區那樣特定環境中進行的。當我們看到那新奇而頗具魅力的自然景觀——或銀裝素裹,或霧靄茫茫,或月夜迷蒙,或天高云淡,還有那多次出現的夕陽、晨曦,無不感受到其中的靈性和意境,仿佛是“人化”了或“神化”了的自然。生于斯、長于斯的一代老獵人,對山林、山神的迷戀、敬重自然也被人們所理解。這種美好的心理既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哲學觀的繼承,又易于同當今國外“地理村民”保護環境、回歸自然的心愿息息相通。
文化是一個內容比較豐富的概念,而人類學紀錄片又是比較具有文化品格的電視作品,在現實意義方面具有文化價值。同時也方便于文化的傳播以及交流。嚴格來說文化也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通過影像來對文化加以了解,在紀錄片的展示下能夠對于民族的文化傳播有著促進作用,人類學紀錄片作為是對信息負載的載體,它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了民族的文化。在人類學紀錄片的文化反思表現上主要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以及現代文明的批判和對邊緣文化的關注。對邊緣文化的關注。在不同的文化之間會存在差異,文化也不是固定的,少數民族的文化屬于邊緣文化的范疇,在當前的工業社會發展中,工業生產和邊緣人群的距離越來越大,紀錄片就重新把這一記憶在人們的面前重拾起來。
五、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人類學紀錄片《最后的山神》的分析,在當前的社會發展中,希望能夠讓這一形式的影像在人們的生活中產生共鳴,對民族文化得到重視以及反思。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過程中,依附于多種的媒介技術,并不斷的得到擴散,這使得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加強,而人類學紀錄片以它獨特的方式正在發揮著其自身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雷建軍,梁君健.當代北方狩獵民族人類學紀錄片的文化敘述[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08):64—65.
[2]柳邦坤.眷戀山林、熱愛自然的鄂倫春人的心靈之歌——紀錄片《最后的山神》的人物形象塑造賞析[J]. 電影文學. 2009(22)
[3] 柳邦坤. 紀錄生活習俗 紀錄內心世界——紀錄片《最后的山神》淺析[J]. 黑河學刊. 2006(05)
作者簡介:李歡(1991——)女,土家族,湖北建始人,在讀研究生,單位: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研究方向:人類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