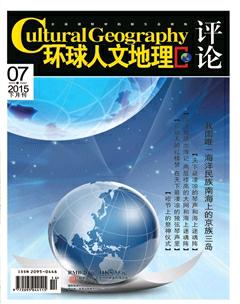論《拜月亭》中瑞蘭形象的發(fā)展變化及原因
摘要 雜劇《拜月亭》和南戲《幽閨記》敷演的都是大家閨秀王瑞蘭和書生蔣世隆的愛情故事,但兩劇中瑞蘭的形象卻有很大不同。本文重點比較兩劇中都有的情節(jié),梳理兩劇瑞蘭的不同表現(xiàn),并探究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
關鍵詞 拜月亭 幽閨記 人物形象 比較
關于“拜月亭”的故事演繹,雜劇中有元代劇作家關漢卿創(chuàng)作的《閨怨佳人拜月亭》,僅存于《元刊雜劇三十種》中。南戲則有《拜月亭記》,《拜月亭記》又名《幽閨記》(為便于行文,本文以下均稱作<幽閨記>),是宋元四大南戲之一。徐渭《南詞敘錄》中列為“宋元舊篇” ,作者不詳。南戲《幽閨記》流傳版本較多,皆明以后版本,據(jù)考證共有九種 ,經研究,現(xiàn)傳明世德堂本《拜月亭記》保持了較多的初期戲文面目,所以本文以該版本為研究文本。
一般認為,南戲《幽閨記》是根據(jù)關劇《拜月亭》改編而成,有些曲詞說白,也“隱括關漢卿雜劇詞語” 。但是,從雜劇到南戲,劇中女主人公王瑞蘭的形象有了較大的改變。
一 《拜月亭》和《幽閨記》兩劇中瑞蘭形象比較
元雜劇是一人主唱,除卻主角外,其他角色沒有唱詞。南戲是多人主唱,凡是劇中人物,都可有唱詞。而《拜月亭》是旦本劇,從頭到尾只有瑞蘭一人有唱詞。本文重點選取兩劇都有的情節(jié)場景:和番送父、蘭隆相遇、隆蘭遇強、瑞蘭拜月禱詞、瑞蘭對父親安排的反抗,來分析兩劇中瑞蘭的不同表現(xiàn)。
(一)家與國——瑞蘭情感的不同關注點
《拜月亭》和《幽閨記》的女主人公王瑞蘭身份相同,但內里表現(xiàn)有很大不同。《拜月亭》中瑞蘭的總體面貌是一種矜持的知書達理的大家閨秀形象,而《幽閨記》中,瑞蘭雖也是書香門第,但卻多了許多率性而為的天性。
這首先體現(xiàn)在王鎮(zhèn)奉命和番前的劇情中。雜劇中瑞蘭對父親和番沒有發(fā)表個人看法,在這段情節(jié)中,她首先是盡自己作為女兒的責任,然后透露出一種家國情懷,這與《幽閨記》形成鮮明對比。《幽閨記》中瑞蘭的情緒反應是抱怨、勸阻和擔憂,既是不知世事的深閨小女兒心態(tài),又有一種率性而為的天性。其次,在瑞蘭和母親逃難的途中。雜劇中瑞蘭的唱詞體現(xiàn)的是對國家興亡的擔憂,她的感情關注線索依然是由國及家,家已離散,仍不忘國之安危,仍然在問“車駕南遷甚時回” 。而在《幽閨記》相對應的情節(jié)中,瑞蘭則心心念念遠行的父親何時回,自己一家何時能夠團圓。這樣,南戲中的瑞蘭形象,就有了與雜劇中女主人公不一樣的特質。
(二)從雜劇到南戲瑞蘭性格的變化
比較雜劇與南戲,可以看出兩個瑞蘭性格有較大變化。首先,在蘭隆相遇這一節(jié)。雜劇中瑞蘭在與世隆說話前,先是暗自嘀咕,然后才“陪笑”與其說話,表明自己是在萬般無奈之下才與男子說話的。在南戲中,瑞蘭則是直截了當?shù)貑柕馈熬油睦锶ィ俊保按缆』卮鸷螅值馈肮脦胰ァ保缆”硎静环奖銜r,她又不斷重申“君子帶奴同去”,并且用起了小智謀。在這里,比之雜劇《拜月亭》,南戲中瑞蘭初遇世隆時瑞蘭所展現(xiàn)的慧黠和機智,為以后的劇情發(fā)展做了相應的鋪墊,較之雜劇瑞蘭的性格豐富了許多。
其次,在蘭隆遇強節(jié)中,相比較雜劇,又能看出瑞蘭在其主體性格主導下隨著劇情發(fā)展而帶來的小變化。在該段中,雜劇中瑞蘭先是毫不客氣地罵,當興福勸酒時,她說“你休吃酒也,恐酒后疏狂” ,并直接說明了良民與山賊不兩立的觀點。而在南戲中,當世隆與興福相認之后,瑞蘭首先是說“愁為喜,深謝得賢叔盜跖”。同樣是勸酒,瑞蘭說:“叔叔,奴家不會飲酒,免勞下禮”,然后背著眾人獨對世隆勸其離開。
最后,在父親包辦婚姻這一段中,雜劇和南戲中瑞蘭的表現(xiàn)則有很大不同。雜劇中瑞蘭面對父親的安排,并不知道該怎樣處理,最后通過客觀的巧合來化解矛盾。而“愿天下心廝愛的夫婦永無分離 ”也通過這種巧合得以實現(xiàn)。而南戲中,當瑞蘭得知父親要為她和瑞蓮招文武狀元時,在瑞蓮的鼓勵下來到父親面前陳詞。其中大段的唱詞,可以說是瑞蘭性格發(fā)展到最后的一個自然總爆發(fā)。 “《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豈曰人工!”呂天成論《拜月亭》時也說:“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見寶” ,說的正是這點。
二 《拜月亭》與《幽閨記》中瑞蘭形象不同的原因
兩劇中瑞蘭形象之所以不同,除卻雜劇和南戲本身不同的戲劇體制之外,還有不少其他原因。
(一)不同語言風格對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語言對于塑造戲劇人物形象有莫大作用,在不同作家在手中,或本色自然,或典雅清麗。《拜月亭》和《幽閨記》中的唱詞說白都可稱得上是本色當行。關漢卿的雜劇向稱本色,《拜月亭》更不用說。何良俊評《幽閨記》云:“余謂其高出《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釋中相逢》數(shù)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敘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 ”。但是,歷來論曲者對本色的理解是不相同的。李開先認為戲曲就應該是“金元風格”,其《西野春游詞》中云:“詞與詩,意同而體異” ,“用本色者為詞人之詞,否則為文人之詞矣” ,同時,其他人又有不同看法。由于論曲者對本色的理解不相同,因此盡管這兩部作品都可以稱之為本色當行之作,但語言風格不可能完全一致。關劇《拜月亭》的語言樸實自然,而南戲《幽閨記》則更顯清麗。這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對女主人公瑞蘭形象塑造的意義也是不同的。
《拜月亭》中男女主人公相會時的唱詞語言全無香艷之色,“你而今病疾兒都較痊?”、“今日這半邊鸞鏡得團圓,早則那一紙魚封不更傳”、“我便渾身上都是口,待交我怎分辯?”,顯得平淡自然。而《幽閨記》中,瑞蘭與世隆相見時,瑞蘭的表現(xiàn)則較為外露“只為伊離別苦惱恨,兩情痛感傷。默思近想憑欄望,黽勉修妝,頻來暗訪” 。通過對比可發(fā)現(xiàn)同樣的一種情節(jié)中兩劇中瑞蘭的表現(xiàn)區(qū)別很大,一個含蓄一個外露。不僅如此,在父親已經快要答應兩人的婚事后,南戲中瑞蘭還不忘叮嚀“不可忘店內的盟山誓”,這雖然使瑞蘭不如雜劇中端莊,但更加貼近人情,更符合現(xiàn)實中人物真實感情的表達需要。
(二)作家立意的變化對人物形象塑造的影響
除了以上分析,作家作劇立意的不同也會影響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拜月亭》中,關漢卿著意通過瑞蘭與世隆的愛情來表達自己反對封建家長包辦婚姻這個主題,而《幽閨記》的作者則主要是要講述亂世中瑞蘭與世隆的愛情故事,并通過這樣一個故事來反映當時廣闊的社會環(huán)境。這種立意的不同突出體現(xiàn)在南戲的作者對拜月這一行為本身的淡化上。
雜劇中瑞蘭拜月時敬了兩柱香,而在南戲中,瑞蘭只敬了一炷香。雜劇中瑞蘭鄭重其事地燒了兩柱香,而且借兩柱香許了兩個愿,表達了兩個主題:批判父親狠心;希望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與其說是瑞蘭的心聲,倒不如說是作者的觀點。而在南戲中,拜月的情節(jié)一閃而過,瑞蘭剛說完“這一炷香呵,(唱)只愿得拋閃下男兒疾較些,得再睹同歡同悅”,就被小旦瑞蓮發(fā)現(xiàn),然后就是姐妹二人互剖心事,不但瑞蘭自己不再去理會還有拜月一節(jié),連作者也沒有回頭交待拜月這件事情。原因就在于,南戲中拜月已經不再承載雜劇作者表達反封建婚姻觀念的立意了。同時,南戲的作者在瑞蘭拜月前增加了“蘭蓮自敘”一出,其實這一節(jié)是對雜劇《拜月亭》第三折的發(fā)揮,但是相比較雜劇,《蘭蓮自敘》更為詳細地剖析了瑞蘭的心跡。因此,拜月在南戲中就直接成為劇情的轉折點——也即淡化了拜月這一行為本身。而從這一淡化正可以看出南戲作者著意于寫愛情故事本身的立意。由于這種基本立意的不同,直接導致了兩個主人公的不同形象。
由以上分析可知,從雜劇《拜月亭》到南戲《幽閨記》,瑞蘭的形象有很大改變。從元初到元末,出現(xiàn)在南戲中的瑞蘭,已經不再是那個欲語還休的端莊的縉紳女子形象,而是一變?yōu)楦覑鄹液抻赂易非笮腋5膭尤诵蜗蟆P纬蛇@種變化的原因,既有劇種體制本身的原因,也有作家立意主題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徐沁君.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M]. 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2] 王季思主編. 全元戲曲[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3] 王國維. 宋元戲曲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 趙杏根. 論南戲《拜月亭》[J]. 貴州師范學院學報. 2010年5月.
[5] 俞為民. 南戲《拜月亭》考論[J]. 文學遺產. 2003年第3期.
魏巍(1990.10-),女,漢族,籍貫安徽,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古代文學專業(yè),魏晉南北朝文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