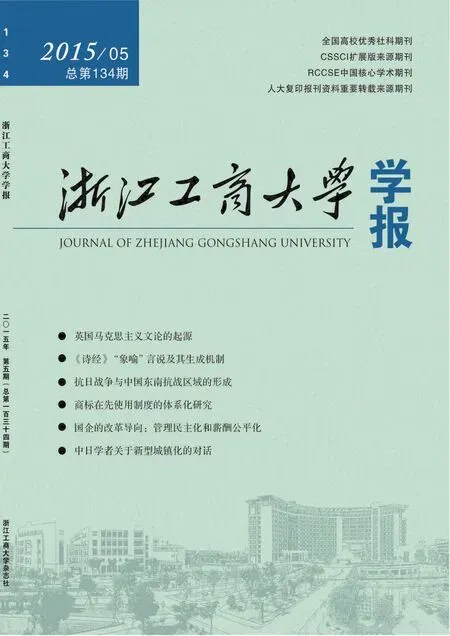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體系化研究——以“影響力”為邏輯主線
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體系化研究——以“影響力”為邏輯主線
倪朱亮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摘要:商標影響力與商標投資成正相關性。商標在先使用制度是以商標“影響力”為主線,以權利的積極權能與消極權能為內部邏輯結構而形成的統一體。在先使用商標“影響力”的大小與涉及對象直接制約在先使用權權能的內容與實現。在商標申請注冊前,爭議雙方均有使用爭議商標時,不能簡單遵從客觀使用時間先后與“誰先申請誰得”的規則,而應當根據雙方主觀狀態、使用時間的差距以及申請注冊時的“影響力”大小等因素做綜合判定商標在先使用權。在先使用商標繼續使用權的效力范圍應限制于原地域范圍,但是可在地域范圍內擴張面積、變更企業形式。
關鍵詞:投資;商標在先使用權;權能分離;影響力;效力范圍
收稿日期:2015-06-1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
作者簡介:倪朱亮,男,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B)聯合培養博士生,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研究。
中圖分類號:DF523.3文獻標志碼:A
The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Institution of Prior Use Trademarks
—Based on the Logic Thread of Influence
NI Zhu-liang
(CivilandCommercialLawSchool,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As one of approaches to invest, the legal and effective trademark use contributes and collects goodwill of trademark, which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zone of goodwill and trademark investment. The institution of prior use depends on substantial influence and is a system which has an inner logical structure comprised by positive right and negative right. Besides, the right of prior use is confined by substantial influence and relevant persons. Prior to trademark registr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right of trademark use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acts, such as the statu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the length of time of trademark use and substantial influence etc., rather than solely to the time of trademark use and registration when disputing parties used trademarks. Even though ambit of effect is restricted within the original area, the prior user can still expand its making place and change the form of business.
Key words: investment; the right of prior use; right division; substantial influence; ambit of effect
2015年4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5年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要點》,明確要求深入推進法規制度建設,依法加強市場監管和集中整治,營造公平競爭、放心消費的市場環境。與以往為營造公平競爭市場而普遍關注商標搶注、商標囤積行為等不同,這次是商標在先使用行為保護問題。
與已有文獻圍繞商標在先使用價值、構成要件的研究路徑不同,本文認為“制度創新能夠減少交換活動的交易(及生產)成本,從而實現日益復雜的交換活動”[1]。因此,首先將商標在先權使用定性為一個制度整體,再從具體行使時的不同權利形式入手,比較商標異議申請權、商標無效宣告申請權、商標侵權抗辯權、未注冊商標禁止他人使用權、繼續使用權等所產生的法律效力,進而概括分散在《商標法》第13條第二項、第32條、第33條、第44條、第45條與第59條等條文而共同構成的商標在先使用制度,是否存在直觀的內在邏輯與主線;如是,又應如何建構該制度體系以實現制度周延性。就上述問題,筆者撰文,進行法理與制度層面的研究,希冀以此拋磚引玉。
一、商標影響力與投資之間的正相關性
商標商譽是通過商標有效使用得以積累。通過使用,商標與特定的商品或服務相聯系時,才可能獲得消費者的評價,進而產生商標影響力,積累與之相關的商譽。因此,可以得出“商標——商標使用——影響力——商譽”的因果關系。
追本溯源,為規制虛假競爭行為,商標使用人在衡平法上獲得了和著作權或商譽相似的財產權地位。日本中山信弘教授主張,“標記性法律保護商業中使用的標記,但真正保護的則是標記所代表的商業信譽。商譽是經營者的財產。”[2]商標法的形成,端賴于對商標財產進行法律保護的“需求”。商標法定化的進程,其實是將商標所能帶來的各種利益以“財產語言”在法律上加以表達的過程,它體現了對商標財產屬性的歷史認同[3]。就產權而言,加藤雅信教授通過文化人類學的路徑證明,與農耕社會的所有權/財產概念產生的社會基礎一樣:通過保護所有權人,賦予社會成員對農耕、農業投資的積極性,最終實現社會整體的農業生產最大化……對土地的資本投入為零——中等——大時,土地所有權及其其他權利分別為不存在——中間性的存在或者萌芽性的存在——私人所有權的確立。(資本投入與所有權產生之間的正相關性)[4]146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這一概念,在構造上基本上是和土地所有權概念平行的,兩者具有相同的社會基礎[4]3。因此,商標權與其他權利一樣,首先保護的是商標使用人,即投資人。這與商標法的私法本質屬性相一致。盡管商標法強調保護消費者利益,但是并不支持其對商標法的立法旨意最終落腳于消費者信賴利益上。一個理性的商標使用人,是自我權益的最佳維護者。除了利他主義,商家贏得和保有顧客,是其金錢利益之所在,也更是經濟上的生存問題。商標訴訟的歷史和以此相關的實體法表明,商家總是敏感地制止混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既保護了自己的錢包,又保護了公眾的利益*In Re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476F. 2d 1357(CCPA 1973).。商標權人竭力維護使用相同商標商品的穩定質量并以此純化市場信息,并通過大量的廣告宣傳展現商標所傳遞的信息,形成商標的指示與索引功能,從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由此給予消費者帶來的利益更應該界定為反射利益[5]。因此,這也進一步論證:商標法之所以保護商標使用人利益,根本原因在于對商標使用人的投資,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不是商標法的直接目標。商標使用人通過商標使用的方式投資商標,其投資的多寡、范圍直接左右商標影響力大小。馳名商標的跨類保護,足以證明商標影響力與商標投資之間正相關的正確性。因此,當使用人投資商標越多、范圍越廣,在滿足合法、有效的商標使用標準時[6],商標的影響力范圍就越大。
二、商標在先使用權的內容
注冊制度劃分了注冊商標與未注冊商標的權利:商標注冊人在核準商品上排他性的使用核準商標,有權禁止他人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標而導致混淆。如果在商標注冊申請日之前,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存在一定影響力,則可根據《商標法》第13條第二款、第32條、第33條、第44條、第45條等規定*《商標法》第十五條第二款并不屬于本文所主張的商標在先使用制度體系。詳細緣由,將置于本文第三(三)部分予以說明。,分別主張禁止他人申請與使用與未注冊馳名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商標注冊異議、商標無效宣告;同時,根據第59條第三項,有權在原范圍內繼續使用商標而不構成侵犯商標權。針對上述不同方式,筆者將其歸納為商標在先使用的具體表現形式。關于這些行為性質,權利說認為,商標在先使用是一種民事權利[7],或商標法上的權利[8],于法定權利之外的先用權以及其他民事法律制度保護的合法權益都屬于在先權利[9]。而法益說主張,《商標法》、《民法通則》《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未注冊商標的保護是對我國注冊制度的有益補充,并非在商標法之外創設權利,使用者要取得商標法規定的權利,必須申請商標注冊,否則通過先使用所獲得的只是一種弱于權利的法益[10]。相比較權利或者法益的一體論而言,有學者主張,商標在先使用應當分為侵權抗辯意義上的商標在先使用權和權利沖突意義上商標在先使用權;是先使用人對抗商標注冊人禁止權的一個手段;前者只是一個消極性的權利[11]。然而,本文認為,商標在先使用是一項權利,是消極權能與積極權能的統一體。
(一)商標在先使用是一項權利
1.商標在先使用權利與權益之爭。“法律明確規定某某權的當然屬于權利,但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某某權而又需要保護的,不一定就不是權利。而且,權利和法益本身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有些利益隨著社會發展糾紛增多,法院通過判例將原來認為利益的轉而認定為權利,即將利益‘權利化’”。[12]誠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長孔祥俊法官指出的“由于商品名稱、包裝和裝潢的利益具有可訴性,其利益不同于反射利益,將其設置為權利問題不大,在理論上也并無大礙”[13]一樣,將商標在先使用認定為權利,并不會帶來司法上的困境。商標在先使用尚未權利類型化之前,上述理論與實踐為保護商標在先使用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支持[14]。隨著《商標法》第59條第三款明確賦予“商標在先使用人在滿足條件下有權繼續在原范圍內繼續使用商標”,商標在先使用所產生的利益已上升至權利層面。
2.商標在先使用權的立法體例與邏輯。商標在先使用權的立法體例有兩種。第一種是在專門規定商標權限制的章節條款中規定商標先用使用權。如《歐共體商標一號指令》第6條“商標效力的限制”之規定:第一款規定了合理使用的內容,第二款規定的便是商標先用權。《德國商標和其他標志保護法》第四章“保護的限制”中規定了商標先用權、合理使用等六種商標權限制類型。英國《商標法》第11條“注冊商標效力的限制”在商標權限制條款之外規定商標先用權。第二種是直接規定商標在先使用權。如日本《商標法》第四章第一節第32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商標先使用權是一種“使用該商標的權利”。意大利《商標法》在第二章“商標的使用”第九條規定了商標在先使用權。
就我國《商標法》第59條而言,前兩款是商標合理使用,第三款是商標先用權。從章節安排上看,第59條設置在商標侵權條款之后,且法律后果是注冊商標專用權人無權禁止他人使用,即符合規定的商標使用行為不構成侵權[15]。這與《歐共體商標一號指令》的立法體例相同,即專門規定商標權限制的章節條款中規定商標先用使用權。之所以我國《商標法》如此設計法律結構,其核心緣由是商標法作為私法,應當遵循保護私權(商標權)的私法體系——從權利產生、到權利行使、再到權利保護的私法邏輯。因此,商標法修改最終遵從商標注冊、使用到保護的立法體例[16]。由于商標在先使用權的主體是在先使用人,無法直接在商標權人的權利行使(即使用)章節予以規定。再則,“是權利就有邊界”,商標權保護的對立面就是商標權限制。因此,需要在商標權控制的范圍里劃出一定區域授予商標在先使用人獨占使用,這對于商標權人而言是商標權排他性的例外或限制[15];對商標在先使用人而言,卻是對其私權的肯定與保護。
3.立法目的無法改變權利本質屬性。商標在先使用權的立法目的是糾正商標注冊制度的缺陷、維護商標秩序的正義與公平[17]。該立法目的在本質上卻實現了在先使用未注冊商標和在后注冊商標的共存。與美國司法判例與《蘭哈姆法》規定商標善意共存使用原則不同,我國商標在先使用權以限制商標權的形式,與商標權共存。因該商標權因未注冊而不能獲得全國范圍的專有權效力,在特定區域內在先使用未注冊商標者可以獲得區域性的商標權,他人以不正當競爭目的在相同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商標相同或者近似標志的,在先使用人有權禁止其使用商標。
此外,《商標法》第64條規定:“注冊商標專用權人請求賠償,被控侵權人以注冊商標專用權人未使用注冊商標提出抗辯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注冊商標專用權人提供此前3年內實際使用該注冊商標的證據。注冊商標專用權人不能證明此前3年內實際使用過該注冊商標,也不能證明因侵權行為受到其他損失的,被控侵權人不承擔賠償責任。”這說明在我國采用注冊取得商標專用權的條件下注冊行為只是法律上的一種確權,并不意味著注冊取得了壟斷該商標使用的效力[18]。這也為商標在先使用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二)商標在先使用權是消極權能與積極權能的統一體
依照權利行使主被動關系,將商標在先使用權的權能分為兩類:一類是當侵權或不利即將發生或已經發生時,權利人為預防或阻止其發生或繼續而進行聲明異議與抗辯的權利,此類權能稱為消極權能。如商標異議申請權、商標無效宣告申請權、商標侵權抗辯權。另一類是以積極行為主張或行使的權利,將其稱為積極權能。如繼續使用權、商標整體轉讓權[19]。有學者認為,根據條文結構與邏輯,《商標法》第59條第三款應當是商標侵權的例外與注冊商標專用權的限制,屬于消極性權利。[11]然而,筆者認為,該解釋縮小了第59條第三款的含義。如果按照解釋論的方法,可以得出兩項內容:第一項,商標在先使用人可依此條文來抗辯注冊商標權人提起的侵權之訴;第二項,商標在先使用人可依法在原范圍內繼續使用該商標*之所以商標法賦予注冊商標權人可以要求在先使用人附加適當區別標識,其原因在于對商標注冊制度價值的維護與公平價值的平衡。因此,才將商標在先使用制度作為商標注冊取得制度的補充。。如此解釋基于兩點:其一,商標在先使用制度是彌補商標注冊制度功能上的不足。為平衡商標注冊價值與在先使用人的利益,限制商標注冊的排他性效力,使之不及于在先使用權人。為此賦予商標在先使用人侵權抗辯的權利。其二,商標在先使用人在原范圍內積極使用商標能夠保護自身利益與維持既有秩序。我國臺灣地區“商標法”將“保護商標注冊人之權利”與“保護在先使用商標者的權利”之間的調和作為商標法宗旨*參見臺灣智慧財產法院九十九年度民公上字第二號判決。,臺灣學者認為此論斷有失得當:“……善意在先使用規范之立法宗旨在于保護商標注冊申請前或表征普遍認之前,已經存在的一定事實狀態或社會關系,避免該等既有事實狀態或社會關系因外部的申請行為或普遍認知的發生,即遭否定、甚至不準其繼續存在,進而全然抹滅處于該等事實狀態或社會關系中的信賴。”[20]筆者贊同對保護在先使用商標者是建立并維護“已經存在的一定事實狀態或社會關系”的觀點。從商標在先使用人的角度,維護既有的一定事實狀態(即秩序),在本質上還是維護商標所形成的影響力。倘若商標在先使用人不能積極、主動地使用商標權,那么,商標的影響力與顯著性就會被減弱。這一點在商標弱化與淡化方面,能夠驗證商標影響力的動態性。
三、商標在先權權能與“一定影響力”之間的關系
(一)主線:“影響力”的認定
鑒于上文所述,商標在先使用權的具體行為方式包括商標異議申請權、商標無效宣告權、商標侵權抗辯權、商標繼續使用權、商標整體轉讓權等。這些權利共同構成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內容。本文認為,商標在先使用制度是以影響力為主線。商標在先使用權人行使商標異議申請權、商標無效宣告權,均須滿足他人以“不得以不正當手段搶先注冊他人已經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要求;行使商標侵權抗辯權與商標繼續使用權則是“已經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先于商標注冊人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從中推導共同要件,即“已經使用”+“一定影響力”。*之所以沒有主觀要素,原因正如我國學者所說,賦予未注冊馳名商標和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異議權和撤銷權的根據是該商標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是法律對在先使用人富有成效的使用行為的肯定和保護,與他人的注冊是否屬于惡意搶注,手段是否正當無關。(參見張玉敏:《論使用在商標制度構建中的作用——寫在商標法第三次修改之際》,載《知識產權》,2011年第9期。)但是,主觀惡意卻能從反面推導出在先使用商標是否具有“一定影響力”。對此觀點,將在第三部分(三)進行闡述。首先,“已經使用”是一個時間概念,是針對商標注冊申請日而言。通常情況下,商標在先使用人先于商標注冊人之前使用,且早于商標注冊申請日之前即已形成“一定影響力”。然而,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三款之規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因為該條沒有解釋清楚商標“一定影響力”的形成是在注冊之前即可還是先于商標注冊人使用前即已形成(如果商標注冊人在注冊之前已經使用)。(第四部分將對此問題進行詳解)其次,盡管“一定影響力”本身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念,往往需要結合具體的案情加以確定。但是“一定影響力”的要求,與《商標法》第13條關于馳名商標定義中的“為相關公眾所熟知的商標”的表述不同,理解上也應該不一樣。從體系角度上理解,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力的商標,在知名度上應當低于未注冊馳名商標。從司法實踐看,對于“一定影響力”的認定標準總體上把握不高,在先商標權人舉證證明在先商標有一定的持續使用時間、區域、銷售量或者廣告宣傳等,通常就認定其有一定影響力*具體判斷商標使用合法、有效的因素,可以綜合借鑒《商標法》第十四條以及《馳名商標司法解釋》第五條關于馳名商標認定的因素:(1)相關公眾對該商標的知曉程度;(2)商標使用的持續時間;(3)商標的任何宣傳工作的持續時間、程度和地理范圍;(4)使用該商標的商品的市場份額、銷售區域、利稅等;(5)商標宣傳或者促銷活動的方式、持續時間、程度、資金投入和地域范圍。(6)其他商標使用的事實。。同時,一般情況下,如果只有極少量的商標使用證據,則不足以認定此類情形屬于“一定影響力”的商標*參見北京市高院(2011)高行終字第365號行政判決書。。
(二)商標在先使用權權能與“影響力”大小的關系
商標在先使用制度是以“影響力”為主線,由積極權能與消極權能共同組成。在具體權能中,“影響力”的大小并不相同。域外法中,英國學者在解釋英國《商標法》第11條關于商標在先使用權(即本文的在先商標繼續使用權與商標侵權抗辯權的綜合)的規定時認為,如果在先使用商標的商譽限于特定區域范圍內,商標在先使用人可以行使在先使用抗辯;如果商標的商譽擴大到更多的區域范圍,那么在先使用人可以挑戰對其提出侵權指控的注冊商標的注冊有效性[21]。由此得出,英國《商標法》對消極權能中商標無效宣告的“一定影響力”的要求高于侵權抗辯權,即前者的影響力應該大于后者的商標影響力。此外,在日本學界與司法界,針對商標在先使用的積極權能(日本《商標法》第32條第一款)與消極權能(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一款)的“影響力”大小是否相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兩者是相同的。理由是都采用了“被需要者廣為認知”的表述;而且從歷史沿革來講,舊法第九條是現行法第32條的來源。設立第九條的原因在于:對于違反舊法第2條第一款第九項規定(現行法第4條第一款),不能進行商標注冊,但因錯誤而進行注冊時,在先使用人在一定的除斥期間內可以請求商標無效;錯過此期間的,為了保護商標達到周知程度的在先使用人,才設立舊法第9條在先使用權的規定[22]。根據學者的解釋,從條文邏輯構成來看,“著名”是在全國范圍內為相關公眾所熟悉,而“周知”則不必要求公眾認識是全國范圍內的,因此,“著名”對知名度的要求要高于“周知”。[23]這與日本特許廳、日本高等法院相一致。日本高等法院判決認為,對地域要求須是日本全國主要商業圈的同種商品經營者之間達到相當的知悉程度,而不應當限定于狹小的地域范圍之內。如果將地域范圍限定于狹小范圍內,不僅會對該地域的其他人,而且會對其他地域的其他人的商標使用造成一定影響[24]。另一種觀點認為,兩者的含義并不相同,在先使用制度中達到“被需求者廣為認知”的程度要低于拒絕商標注冊事由中所達到的程度,前者可以在狹小的低于范圍、更低的滲透度上成立[25]。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反觀我國《商標法》第32條與第59條第三款有關“一定影響力”的解釋,有學者認為,注冊商標的效力及于全國,而在先使用侵權抗辯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作為阻卻商標注冊事由的在先使用商標,應該比在先使用侵權抗辯中的在先使用商標在影響程度和范圍上要強。[11]這一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筆者認為,從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宗旨與商標注冊制度價值之間的關系分析,后者效力往往高于前者。這從商標在先使用權并無享有同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效力即可看出。除了商標搶注或者商標符號圈占之外,注冊商標會形成一定的市場秩序。如果商標在先使用人借商標無效宣告程序致使生效的商標歸于無效,由此產生的成本往往要大于維持注冊效力的成本。因此。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商標注冊異議申請與商標無效宣告程序對“一定影響力”的要求應高于商標侵權抗辯與商標繼續使用,即商標在先使用權中積極權能與消極權能的“影響力”大小要求并不相同。基于該結論,本文認為,根據商標“影響力”的大小,商標在先使用制度中,對“影響力”要求最低的最基礎權能應當是商標繼續使用權與商標侵權抗辯權;而商標異議申請權和商標無效宣告權是在前兩者權利的基礎上發展。
(三)商標在先使用權能與“影響力”涉及對象的關系
通過一定的持續使用時間、區域、銷售量或者廣告宣傳等獲得最低限度的影響力時,在具體影響力涉及對象上,是否會存在特定性及于:區域范圍內的相關公眾還是要同時及于商標注冊人?理論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標“一定影響力”只要及于一定地域范圍內的相關公眾即可;另一種觀點認為,商標的一定影響不僅應及于特定地域內的相關公眾,而且應及于商標注冊人。商標的影響及于特定地域的相關公眾是在先商標受保護的基礎,而商標的影響及于商標注冊人是在先商標得以對抗被異議人的基礎。只有具體到個案中該商標的影響力確已達到為該商標注冊申請的商標注冊人所知,商標注冊人才具有可歸綹性。因此,未注冊商標要對抗他人的注冊申請,應該要求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商標注冊人有明顯的主觀過錯。[10]對于這一問題,筆者的理解是,“一定影響力”涉及面并無最小范圍的限制,而是應當在具體案件中區分商標在先使用權的積極權能與消極權能,以此認定“影響力”是否需要涉及商標注冊人。以商標注冊異議申請與商標無效宣告——商標在先使用的消極權能為例,《商標法》第32條強調商標注冊人要有“以不正當手段搶注”的行為,即主觀上要存在損害他人利益的惡意。關于惡意的含義及其判斷標準,商標法并未給出明確的指引,但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商標法,可以采納民法上關于善意與惡意的判斷標準。民法上的善意、惡意是民法殘留在現代民法中的痕跡,從理論上說只涉及行為人知或不知的問題。不知為善意,已知為惡意,至于應知到底屬于善意還是惡意,應視情形而定[26]。商標注冊人若有主觀惡意,則需其主觀意識知曉商標在先使用人商標存在的事實。當在先使用商標的地域范圍覆蓋商標申請人所在地時,可以推定其應當知曉在先使用商標*參見北京市一中院(2006)一中行初字第191號行政判決書和北京市高院(2007)高行終字第16號行政判決書。。因為從搶注人的商標申請注冊行為來看,其應當負有最低程度的注意義務,即稍加注意即可知曉同行業者在先使用商標的存在。因此,在先使用人申請商標異議或無效宣告,除了證明在先使用商標于相關公眾中已形成一定影響力,還需證明申請人具有主觀惡意——以此證明商標影響力及于申請人。
作為同樣對在先使用商標予以保護的實體性條款,如何確定及厘清《商標法》第15條第二款與第32條后半段以及第59條第三款之間的關系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
筆者認為,商標法第15條第二款并不屬于筆者所主張的商標在先使用制度體系的內容。原因如下:不管是已有文獻還是筆者所提出的觀點,商標在先使用制度均滿足兩個構成要件:“已經使用”(時間要素)+“一定影響力”(商譽要素,法律保護的基礎)。而第十五條第二款在先使用人并不完全滿足構成要件,它存在兩種情形:第一種是在先使用商標具有一定影響力——該情形滿足要件;第二種是在先使用商標“可能是因為特別的讀音、文字組合或是域外使用等原因,而不一定在國內相關公眾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力”。盡管《商標法》第15條第二款與第32條后半段,均可被援引遏制惡意搶注申請,但兩者側重點并不相同。對于第15條第二款的適用前提,應相對強調是基于惡意的“知悉”,而使用未必需要局限中國大陸地區。因為對域外使用證據的確認和采信,其目的并非是主張系爭商標在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產生“一定影響”應予以直接保護,而是為了證明系爭商標權利歸屬這一客觀事實從而推斷申請人可能明知該商標存在的可能。這種對于使用地域的擴張解釋,將使得《商標法》第15條第二款的適用更具有操作性,也更符合《商標法》第15條對誠實信用原則和信賴利益保護的立法本意的貫徹[27]。而對于第32條后半段與第59條第三款“一定影響”的適用不僅強調真實商標使用,還需要考慮國內一定的使用規模、頻度和地域范圍。[28]由此可見,司法實踐中,適用第15條第二款時,只需要“被代理人僅證明在先使用商標的事實即可,而無須證明其商標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即所謂有一定影響)。”
對于基礎權能——商標繼續使用權(積極權能)與商標侵權抗辯權(消極權能)的行使,因制度宗旨設計是為了商標在先使用人能夠繼續使用其商標而不構成侵權,因此,只要滿足“影響力”及于一定范圍內的相關公眾即可,不要求是否及于商標注冊人。若行使基礎權能之外的權利,則需證明“影響力”及于商標注冊人。
四、特殊情形:雙方均有使用時商標在先使用權的判定
鑒于第三部分之論證,在類似的商標異議或爭議案件中,商標在先使用人首先需要證明自己對商標被異議人商標使用在先的事實;其次需要證明影響力的形成早于商標注冊申請;第三,在先使用人還需根據所主張的權能類型證明“影響力”的大小與涉及范圍。若以T1代表在先使用人最初使用商標時間、T2代表申請日、T3代表商標注冊人最初使用時間,則三者之間存在三種關系:

商標在先使用制度多數適用圖1情形,即在先使用商標在注冊申請日之前已經形成“一定影響力”,并且商標注冊人在申請日之前并無使用。然而,實踐中不時出現圖2,即在商標注冊申請日之前,在先使用人和商標注冊人雙方均有使用;甚至在個案中出現圖3,即T1與T3極其接近。那么,在圖2和圖3情況下,是以客觀時間上更早使用來確定商標權歸屬,還是在任何一方主觀均無惡意,而采用先申請先得,或是第三種根據案情綜合考慮。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類似案件做出判決前,司法實踐傾向于以客觀時間來衡量。如2006年“保花蕾”商標爭議案中,爭議申請人(即商標在先使用人)和訴爭商標權利人(商標注冊人)都證明在訴爭商標申請日之前均已使用商標。最終北京高院主要以爭議人使用時間更早為由,同時考慮了訴爭商標申請人存在主觀惡意,撤銷爭議商標*參見北京市高院(2007)高行終字第419號行政判決書。。2008年“廈港”商標異議案中,一審法院以異議人未能提交直接證據證明其使用時間明顯早于訴爭商標申請人為由,未支持異議人的主張。二審法院則是以雙方均使用,無法查明知名度近來自其中一方為由,同樣未支持異議人的主張*參見北京市高院(2008)高行終字第43號行政判決書。。2009年“黑大狀HEIDAZHUANG”商標異議案中,法院與商評委將爭議的焦點均放在異議人是否有證據證明其比被異議人更早使用*參見北京市高院(2009)高行終字第228號行政判決書。。然而,2012年“氟美斯FMS”商標爭議案中,針對類似問題從先使用標準轉向先申請標準。一審法院認為,爭議商標權利人與爭議申請人幾乎同時(盡管在客觀時間上稍微有先后)在市場上銷售“氟美斯FMS”商品,并且,截止爭議商標申請日之前,爭議商標權利人的前身在商業活動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爭議商標,并使爭議商標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此情形下,并不存在主觀惡意情形。因此沒有必要適用(原)商標法第31條的必要。二審法院則持先使用標準,認定爭議申請人于1998年6月12日使用“氟美斯FMS”,而爭議商標權人最早使用是1998年7月27日,晚于爭議申請人的使用時間,因此判決適用(原)商標法第31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則認為,雖然一般情況下,商標申請人明知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力的商標而申請注冊即可推定其具有利用他人商標商譽獲利的意圖。但是,本案事實顯示,在爭議商標申請日前,雙方幾乎同時在市場上使用相關商標且相互知曉,但雙方對相關標識的歸屬并無特別約定。此外,爭議商標權人在申請日之前,其銷售規模大于爭議申請人。因此,爭議商標權人獨立申請注冊商標并不侵犯爭議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亦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不能僅因客觀時間的一點優先,而不全面考慮(原)商標法第31條的適用要件。故判決不予撤銷*參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13)行提字第11號。。
由此,筆者總結,一般情形下(圖1),可以以使用時間先后來判斷商標在先使用權成立與否。在特殊情形下,如果僅以時間先后,有時候會導致不公平。依照上文所述,如果在先使用人的使用范圍及于商標申請人,原則上推定申請人知曉相關商標而推定存在主觀惡意。例外情形是,如果雙方均相互知曉,則需要考慮申請注冊時雙方的影響力大小。(一)如果在先使用人的影響力明顯大于另一方,則應當支持異議或選擇商標無效;(二)反之,則應當駁回異議或者維持商標效力。(三)假如雙方在申請日的影響力并沒有壓倒性優勢,則根據我國商標法“先申請原則”,判定商標在先使用成立與否。
五、商標繼續使用權的效力范圍
綜上,商標繼續使用權作為商標在先使用權的基礎權能,只要在相關公眾中形成一定影響力,即可行使之。通說認為,繼續使用權應當限于原區域范圍內在原商品上使用原商標[29]。但是否包含對產業規模與企業形式的限制,則無一致意見。同樣,在域外法領域,《歐共體商標一號指令》與日本《商標法》均只規定了商標權效力達不到的范圍,但并未對商標在先權在原有范圍內的具體權利行使方式與內容做出一定的法律解釋。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臺灣地區的商標法有頗多值得我們借鑒之處。一方面,盡管大陸與臺灣地區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海峽兩岸的經濟都經歷了非常相似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臺灣地區已經進入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階段,其商標法律制度經過幾十年的演變與發展,在立法技術上更加完善,也有較為充足的實踐經驗。因此,中國大陸地區商標法的修改可以在結合臺灣地區的先進司法與立法經驗,同時符合大陸范圍實情的前提下,妥當地進行比較法研究。我國臺灣地區“商標法”第30條刪除了原臺灣《商標法》規定的“原產銷規模”的限制,只以“原使用商品”為限。對此修法旨意,臺灣智慧財產法院解釋為,“立法過程既有意刪除‘以原產銷規模為限’,應已預見不同方式之產銷規模形態(包括在原址擴充原店面營業面積、在原地理區域開設分店與加盟商、在不同地理區域開設分店與加盟商等),若僅限于原址或僅限于原地理區域內開設分店,顯然有擅自增加法條文義所未明文之限制,自屬于無據之解釋。況且商標法對商標權人之保護部分,于有善意在先使用情形時所設立外規定,其中不乏商標在先使用者不知申請商標注冊緣故而嗣后遭他人持以申請注冊者,以此種情形下,若此利用他人不知注冊而搶先注冊者以權利應優先保護,而善意先使用者因此不得繼續發展其業務,不惟不當限制人民工作及生存權,恐亦不符誠實信用原則。”*參見臺灣智慧財產法院九十八年度刑智上易字第四十號判決。對此,臺灣學者也有持相反意見,“在先使用制度的旨意應是對既有的事實狀態或社會關系的保護,不應延伸使用。”[16]筆者認為,未注冊商標繼續使用權的效力應限于原生產的地域范圍,但在該范圍內可以擴張營業面積、開設分店或者加盟店以及變更企業組織形式。其理由如下:第一,盡管商標在先使用作為商標注冊制度有失公平的糾正機制,但是不能埋沒商標注冊制度的應有價值。實行先申請原則,在于鼓勵市場主體搶先注冊最有利于自己的商標,并盡快在全國范圍內獲得排他性;在此基礎上安心投入人力、物力與財力來打造自己的商標,擴大營業規模及地域范圍,從而促進產業的發展。因此,商標注冊制度優先考慮注冊人的未來發展可能性,并為其保留市場。即使注冊商標權人的商品最終并沒有包圍甚至淹沒在先使用人的市場,但不能因此就賦予在先使用人擴大地域范圍的權利。諾斯說,“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30]當在先使用人喪失搶先注冊商標時,就需要承擔因怠慢而付出的應有制度成本。第二,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立法宗旨在于保護既有秩序。由于在該地域范圍內,消費者已經認知未注冊商標所傳遞信息,具有秩序的特定范圍。其在原地域范圍內的擴張門面等形式,并不會打破消費者既有的認知模式。因為商標作為商品來源的索引,并不能完全替代商品質量、外觀、價格、性能等因素對消費者在購買時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未注冊商標繼續使用權只能在原有地理區域范圍內的原商品上使用,但是可以在地域范圍內擴張面積、變更企業形式。
六、結語
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為了解決分配沖突問題,社會中不對等的力量導致了各種制度解決方案。[31]商標在先使用制度與商標注冊制度便是解決如何分配商標權歸屬的方案。作為商標權限制的一種類型,商標在先使用在權利屬性上是與商標權一樣受法律保護的私權,是確定未注冊在先使用商標權利歸屬的機制。商標在先使用權的權利限制功能與商標注冊制度的糾錯功能,無法改變商標在先使用作為獨立權利存在的意義。盡管我國《商標法》有關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法條處于分散狀態,但是筆者認為“形散神不散”的商標在先使用制度有著以商標影響力為主線的權利結構。從權利結構內部分析,商標在先使用權是由積極權能與消極權能組成,并且商標影響力大小直接制約權利內容與權利行使方式。在授權確權糾紛中,原則上遵從商標注冊制度的“注冊優先”考慮商標歸屬與在先使用商標的影響力對抗注冊制度的分配規則;特殊情況下,綜合考慮在商標注冊申請日時,在先使用商標與(申請)注冊商標之間的影響力大小。就積極權能而言,未注冊商標繼續使用權只能在原有地理區域范圍內的原商品上使用,但是可以在地域范圍內擴張面積、變更企業形式。綜上,系統研究商標在先使用制度的意義,在于能夠有效協調與商標注冊制度、商標異議制度、商標無效宣告制度、馳名商標保護制度等之間的關系;在維護注冊商標權排他性的同時,保護在先使用商標,并清晰劃定商標在先使用人的權利內容與實現方式。
參考文獻:
[1]柯武剛,史曼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2.
[2]文學.商標使用與商標保護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
[3]余俊.商標法律進化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67.
[4]加藤雅信.“所有權”的誕生[M].鄭芙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46.
[5]孔祥俊.商標法適用的基本問題[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240-241.
[6]張曉.商標先用權保護探討[J].知識產權,2014(2):63-87.
[7]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適用[J].法學研究,2005(3):110-125.
[8]邱平榮,張大成.試論商標法中在先權的保護與限制[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3):74-79.
[9]凌斌.肥羊之爭:產權界定的法學和經濟學思考——兼論《商標法》第9、11、31條[J].中國法學,2008(5):170-189.
[10]馮曉青,羅曉霞.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的未注冊商標的法律保護[J].學海,2012(5):139-146.
[11]杜穎.商標先使用權解讀[J].中外法學,2014(5):1359-1373.
[12]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10.
[13]孔祥俊.商標與不正當競爭法:原理和判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9.
[14]杜穎.在先使用的未注冊保護——兼評商標法第三次修訂[J].法學家,2009(3):123-159.
[15]葉赟葆.論商標權限制體系中的商標先用權——兼談修訂后的新商標法[J].理論月刊,2014(4):121-125.
[16]張玉敏.維護公平競爭是商標法的根本宗旨——以《商標法》修改為視角[J].法學論壇,2008(2):30-36.
[17]王蓮峰.論對善意在先使用商標的保護[J].法學,2011(12):132-137.
[18]馮曉青.我國商標法修改的最新進展及其完善研究[J].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13-34.
[19]李莉.論作者精神權利的雙重性[J].中國法學,2006(3):83-92.
[20]黃銘杰.商標先使用權之效力范圍——評智慧財產法院九十八年度刑智上易字第四十號判決[J].月旦法學,2012(5):145-180.
[21]W R CORN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3rded.)[M]. London: Sweet & Maxwell,1996:630.
[22]綱野誠.商標[M].東京:有斐閣,2002:778.
[23]田村善之.知的財產法[M].4版.東京:有斐閣,2006:83.
[24]李揚.我國商標搶注法律界限之重新劃定[J].法商研究,2012(3):76-84.
[25]小野昌延.注解商標法[M].東京:株式會式青林書院,2005:804-813.
[26]曾世雄.民法總論之現代與未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28-229.
[27]胡剛.《商標法》第十五條第二款的適用[J].中華商標,2015(2):65-67.
[28]曹新明.商標先用權研究——兼論我國《商標法》第三修正案[J].法治研究,2014(9):16-24.
[29]商志超.為先用權正名[J].河北法學,2014(10):142-149.
[30]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7.
[31]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8.
(責任編輯陶舒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