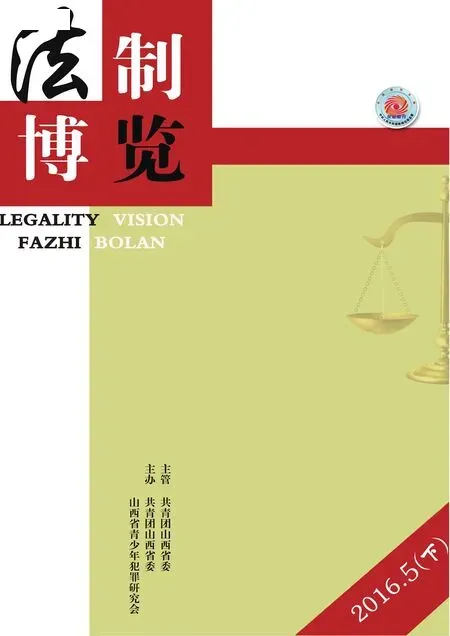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張谷泉 成楊森 蘇宇吉 黃怡雯
華東理工大學,上海 200237
?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張谷泉成楊森蘇宇吉黃怡雯
華東理工大學,上海200237
摘要:2013年8月22日,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并于9月29日上午10時正式掛牌成立。對內,標志著制度創新、政府職能轉變的開始;對外,標志著中國將深入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貿易的里程碑。在實現貿易便利化的同時,產生了許多原本未有的知識產權問題。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由貿易區模式下貨物入境、過境轉運的法律適用與監管問題以及涉外代工、定牌加工貨物出口貿易的知識產權問題。同時,本文針對所提出的問題在立法層面分四個方面提出建議。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自由貿易區;國際條約;對策建議
一、研究背景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的提升,服務貿易中的知識產權貿易及涉及知識產權的貨物貿易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大。[1]2013年8月22日,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由貿易區”),并于9月29日上午10時正式掛牌成立,標志著我國對外貿易進入了新的階段,國際上紛紛將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與中國加入WTO相提并論,認為這是中國“二次入世”的標志。上海自由貿易區在實現貿易便利化的同時,產生了許多原本未有的知識產權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及對策制定具有深刻的價值和意義。
二、自由貿易區模式下知識產權面臨的新形勢
1973年,國際海關理事會簽訂的《京都公約》中將自由貿易區定義為“一國的局部領土內運入的任何商品就進口關稅及其他各稅而言,被認定為在該國關境以外,免予實施日常的海關監管制度”。除了稅收方面的差異之外,對于自由貿易區內的知識產權而言,也顯現出區別于自由貿易區外的特殊問題。
(一)貨物入境、過境轉運的法律適用與監管新形勢
根據他國的經驗,在自由貿易區內發生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主要集中于過境或轉運過程中假冒或盜版產品。[2]上海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境內設置的自由貿易區,其本質是FTZ,除在關稅意義上能夠被視為“境內關外”之外,在法律適用上我國的法律當然適用于其管轄的全境,在政府監管方面也具備了“境內關內”的性質。自由貿易區內絕大部分知識產權問題都能通過現有機制解決,區內出現的商標假冒、版權侵權等問題,與境內區外出現的類似問題并不存在任何差異,境內區外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同樣可適用于處理自由貿易區內出現的知識產權侵權問題。
然而,對于自由貿易區特色的知識產權問題,卻無法簡單地通過現有機制來解決。自由貿易區最大的作用之一在于過境轉運,所謂“過境”是指貨物在海關控制下從一國/區海關運輸到另一國/區海關的過程,其運營指海關過境下從貨物發出海關到目的地海關的貨物運輸,[3]即一國提供運輸通道便利而貨物不進入該國境內市場流通的現象。自由貿易區在海關監管方面不同于區外,過境和轉運為進行假冒、盜版物品貿易提供了機會。對于在國外制造的貨物通過自由貿易區進入我國境內,即使該貨物存在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情形,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法律適用卻存在著一定的模糊地帶,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海關知識產權保護的職能被弱化
“入境”和“進口”屬于不同的法律概念,使得《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的適用上存在問題,海關知識產權保護與監管實際上被弱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過境貨物監管辦法》(海關總署令第38號)明確指出過境貨物是“由境外啟運,通過中國境內陸路繼續運往境外的貨物”。因而從境外進入上海自由貿易區,再經此區運往境外,并不進入我國市場的貨物屬于過境貨物,不屬于進口貨物。
在一般情況下,貨物的運輸者只有先通過海關申報,獲得相應的報關審批單之后,才能夠將貨物運輸至中國境內。然而,自由貿易區采用了與傳統制度不同的做法,在《上海自由貿易區總體方案》(簡稱《總體方案》)中對監管服務模式有所創新,推進實施“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的模式,允許企業憑進口艙單將貨物直接入區,再憑進境貨物備案清單向主管海關辦理申報手續,即貨物從“先報關,后入區”轉變為“先入區,后報關”,這使得自由貿易區形成了獨特的“境內關外”模式。我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的第二條在法律適用上進行了規定:“本條例所稱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是指海關對與進出口貨物有關并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專利權(以下統稱知識產權)實施的保護。”可以看出,《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只適用于進出口的貨物,對于只是入境但并未通過海關報關進口的貨物(包括臨時停放、轉運貨物等),《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則無法適用,這使得自由貿易區內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存在一定的監管空白地帶,隨著貨物的直接入區,過去在海關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扣留侵權嫌疑貨物的措施將在實際上被弱化。
2.知識產權部門法在認定侵權時存在障礙
我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在面對僅處于“入境”但尚未“進口”的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時,其法律適用也存在障礙。對于專利權人的保護,《專利法》僅在貨物進口時才能夠被認定為侵權,也就是說,如果在國外制造的貨物只是簡單的入境并在自由貿易區內停留,在尚未通過海關報關進口到大陸市場的情形下,并不能認定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權利人也無法依據《專利法》獲得權利救濟。只有當貨物通過海關審批并進口到大陸市場時,該行為才存在被認定為侵權的可能,如果貨物只是在自由貿易區內短暫停留之后轉運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權利人無法獲得《專利法》意義上的權利救濟。
3.判斷轉運貨物侵權的標準有待明晰
對于轉運貨物而言,判斷侵權的標準與法律適用存在模糊地帶。在一般情況下,為實現知識產權邊境保護,應適用我國法律判斷轉運貨物是否侵權并實施邊境措施,但在適用轉運國法律會影響貿易自由的情況下,為給合法貿易留下更大的空間,應在我國與轉運貨物目的國有雙邊協議的情況下,合理地適用轉運貨物目的國的法律。此時,雖然貨物已經在我國境內,但由于并未真正投入市場,其實并沒有對我國市場上的知識產權相關權利人造成實際的經濟損失,如果侵權貨物轉運到目標國家,實際上也只是損害了目標國家的相關權利人的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立法及侵權判定標準,認定侵權的難度極高,并且也存在著法律適用上的障礙。
(二)涉外代工、定牌加工貨物出口貿易的新形勢
定牌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簡稱OEM),又稱貼牌加工,是指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標準和要求,生產制造并交付帶有定作人提供的商標的商品,并由定作人向承攬人支付報酬的承攬合同關系。[4]
1.大量代工、定牌加工平臺開始建立
《上海自由貿易區總體方案》要求對自由貿易區內生產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進口所需的機器、設備等貨物予以免稅,因此未來在自由貿易區內會有大量定牌加工企業。這些企業接受定做方委托,加工使用特定商標或品牌的商品。如果企業在加工過程中未經許可使用了受我國法律保護的注冊商標,就有構成侵權的可能。對于以代工、定牌加工為主的企業而言,自由貿易區實施“境內關外”的政策模式,設立在自由貿易區內的企業在貨物的制造、生產、加工等環節盡管與區外并沒有什么區別,但是其在稅收優惠上無疑能夠獲得更大的成本優勢,一旦這些貨物出現知識產權瑕疵或侵權風險,在缺乏合適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情況下,會使得自由貿易區內變成制假之源頭,損害自由貿易區及相關企業的名聲。
2.涉外代工、定牌加工的法律適用存在爭議
如果對涉外代工、定牌加工貨物的產生或出口過程監管不到位,知識產權侵權現象頻發,上海自由貿易區可能會成為侵權、假冒、盜版商品的天堂,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及國際商會也曾經對此現象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貿易便利化并不能夠成為知識產權侵權的豁免之地。對國內定牌加工,如果承攬人未經國內商標注冊人許可而為定作人生產制造貼牌產品,那么該國內定牌加工行為被認定為商標侵權,并沒有爭議。對于涉外定牌加工,如果定作人是外國企業且在其本國擁有商標權但不在我國擁有商標使用權,國內承攬人接受委托為該外國企業定牌加工,且所定牌加工的產品全部交付給定作人在國外銷售,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是否構成商標侵權,則在理論和司法實務界存在較大爭議。
3.對于商標“使用”和“侵權”的認定存在爭議
涉我外代工、定牌加工貨物出口的新問題主要集中于商標侵權之上,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于關于商標“使用”的判定在法律規定與實踐中存在爭議。我國《商標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維護商標信譽”,因此對于商標權的保護往往不是保護一種商標設計本身,而是保護該商標背后所體現出來的商業價值。《商標法》所稱的“使用”是指:“將商標用于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書上,或者將商標用于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用于識別商品來源的行為。”
但是,筆者在開展調研時,許多企業表示在實踐中僅將商標貼在貨物之上,并未將該貨物投入市場,盡管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商標使用,但是由于該商標背后的商業價值并未得以體現,也沒有造成市場上消費者對商品的誤認或混淆,而商標侵權又要以產生實際混淆為前提。因此,如果一家企業在自由貿易區內進行侵權貨物的定牌加工行為,且并未投入市場而是轉運去了國外,則很難認定其商標侵權。2004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3條也曾經規定:對于受境外商標權人委托定牌加工且僅用于出口的商品,即使其商標與國內的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該定牌加工行為也不構成商標侵權。其理由是:“造成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是構成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前提。定牌加工是基于有權使用商標的人的明確委托,并且受委托定牌加工的商品不在中國境內銷售,不可能造成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因此,不應當認定構成侵權。盡管該規定在2006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印發的《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被刪除,但仍然沒有完全消除對OEM商標侵權糾紛的爭論。
也就是說,如果該貨物并未投入大陸市場,而是通過自由貿易區的渠道出口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將自由貿易區作為轉運地和臨時倉儲地,由于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征,該行為應當由目標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來調整,無法根據我國法律來認定商標侵權。
因此,對于假冒品牌的定牌加工行為,自由貿易區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避風港”作用,有可能會成為假冒品牌的定牌加工場所,有損害自由貿易區的聲譽。
三、上海自由貿易區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建議
(一)“境內關外”產生的法律授權瑕疵亟需解決
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本質是FTZ,在對海關的調研中,筆者發現除在關稅意義上自由貿易區被視為“境內關外”之外,從知識產權監管方面還是采用“境內關內”的模式,即將“進出境”參照“進出口”的做法進行監管,但由于法律授權具有一定的瑕疵,該問題還應當引起立法層面的重視,在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方面更是如此。
我國海關已有多年的知識產權保護經驗,TRIPs協議第51條要求各成員對涉嫌進口假冒商標或盜版的貨物采取邊境措施。這是國際條約對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所規定的最低標準,各個締約國必須遵守。但是,在自由貿易區模式下由于存在著“境內關外”的特殊監管地帶,使其職能有所束縛。筆者建議適當強化海關知識產權的監管機制,爭取在其職能范圍上有所突破,可否要求它將監管從貨物進出口延伸到在整個自由貿易區中的產品制造和銷售?可否要求其工作方式從主要依靠“主動發現然后通知權利人維權”的工作模式擴展到主動發現和高效處理并重的模式上?[5]對于出入我國邊境但并非進出口的貨物,如果有證據表明存知識產權侵權事實,也可以對其采取相應的執法措施。
(二)在出入境環節實施海關監管需考慮的國際條約
修改法律法規并非易事,根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第5條第3款的規定,過境國除未能符合可適用的海關法律和法規的情況外,來自或前往其他締約方領土的運輸不得受到任何不必要的遲延或限制;TRIPs協議也規定了“各成員方無義務對過境貨物采取中止放行程序,”即TRIPs協議并不強制成員對過境貨物采取邊境措施。[6]因此,對于海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修改,往往需要經過數年的論證過程,并且由于海關主要在進關、出關時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對過境且尚未入關的貨物實施監管,也與自由貿易區“先入區,后報關”的監管理念不一致,在入區但未報關之前日常的管理由其他行政機關完成,調整海關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條款的難度較高。
對于上述問題,筆者建議可以考慮參考負面清單的做法,直接將禁止將具有知識產權瑕疵或侵權貨物運輸至自由貿易區內等條款寫入禁止性條款,并要求貨物的所有人在運輸至我國境內時告知其予以承諾。一旦發生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并被認定侵權,需要承擔的懲罰性賠償則更重,以此博弈機制來將侵權貨物進入我國境內的風險降到最低。此外,也可以考慮對入境貨物采取跟蹤的做法,使得自由貿易區內執法機構與海關之間形成信息聯網,賦予海關主動發現并處理侵權商品的權力,一旦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商品進入海關,能夠第一時間發現并予以處理。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標準仍需不斷調整
對于自由貿易區知識產權的制度設定,各國的焦點都落在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問題之上。這里所說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標準并非在司法和執法環節的保護力度,而是指在立法層面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條款。
但是,這個問題又具有兩個相對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自由貿易區的宗旨在于消除貿易壁壘,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無疑會提高貿易壁壘,貿易便利化要求的最佳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是零保護。另一方面,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卻對技術引進、自主創新、成果轉化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能夠吸引更多的資金、人才、知識產權等生產要素。
因此,如果自由貿易區對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把握不當,那么知識產權保護就有可能成為一種貿易壁壘,進而阻礙自由貿易的發展。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知識產權立法制度都是在內因與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不斷進行調整的結果,例如,作為自由貿易港的新加坡在建國后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期間,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并不高,之后,主要是在美國以及WTO規則的推動之下,才開始逐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7]但即使到了現在,新加坡在某些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尚不如中國。
四、研究展望
筆者通過研究認為,關于自由貿易區知識產權保護,不僅可以作為立法、司法、行政部門長期研究的政策,也可以作為科研院所、事業單位的研究課題,具有很強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成立尚不滿一年,隨著貿易活動的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和知識產權糾紛也將逐漸顯現,目前的研究僅是對筆者所閱讀和調研材料的分析,尚不足以對未來問題產生規制或影響,相關立法、政策應當不斷完善,共同為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尤其是上海自由貿易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制度創新獻計獻策。
[參考文獻]
[1]周慧春.國際貿易新形勢下的上海自由貿易區知識產權保護[J].電子知識產權,2014(2).
[2]馬忠法.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下的知識產權問題[J].電子知識產權,2014(2):50-62.
[3]E4./F7 and E5/F6 of Protocol of Amend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Simplific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Customs Procedures of 18 May 1973
[4]林廣海,鄭穎.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標權問題[J].人民司法·應用,2007(23)
[5]馬忠法.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下的知識產權問題[J].電子知識產權,2014(2):50-62.
[6]張敏.WTO框架下歐盟知識產權邊境措施適用于過境貨物之合法性分析[J].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13(1):29-42.
[7]尹鋒林,張嘉榮.上海自由貿易區知識產權保護:挑戰與對策[J].電子知識產權,2014(2).
中圖分類號:D997.1;D9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5-0025-03
作者簡介:張谷泉(1994-),男,漢族,浙江溫州人,華東理工大學,研究方向:民商法。
*華東理工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成果(項目編號:s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