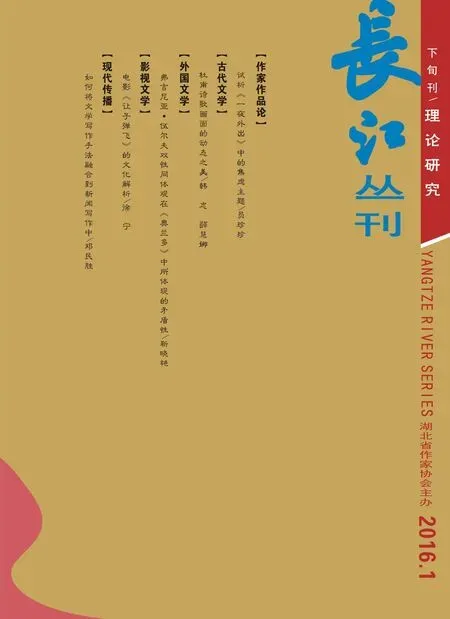明清兩代瓷器繪畫藝術中的體育活動探微
袁 予
?
明清兩代瓷器繪畫藝術中的體育活動探微
袁 予
【摘 要】瓷器繪畫作為我國傳統(tǒng)藝術表現(xiàn)形式之一,具有題材豐富和流傳較廣的特點。在出土的明清兩代瓷器文物中,不乏一些描繪體育活動的瓷器繪畫。相較而言,明清兩代瓷器繪畫主要為民間活動和軍事戰(zhàn)爭等,充滿生活氣息和時代特征。本文通過對明清兩代瓷器繪畫藝術中對體育活動的描繪,探討其內在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明清 瓷器繪畫藝術 體育活動
瓷器作為精神寄托的載體,從遠古時期開始,就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瓷器不僅是古時上至達官權貴,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用品,也凝聚了民族文化的高度發(fā)展成果,是歷史文化的結晶。“而在藝術陶瓷器的裝飾中,裝飾則反映人的精神境界,人們通常以裝飾來表達某種情感和寄托某種愿望”[1],而作為反映古時人們日常生活的載體,自然不會缺少對體育活動的描繪。無論是記錄原始社會游泳活動的“人面魚紋陶盆”,還是記錄5000年前舞蹈的舞蹈紋彩陶盆,都反映出我國優(yōu)秀的體育文化,描繪了古時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歷史軌跡,具有極強的研究價值。
在古代瓷器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體育運動中,不僅有我們熟知的蹴鞠、馬球、捶丸等球類運動,還有圍棋、象棋、六博,甚至連較為激烈的摔跤和市井的雜技都有所表現(xiàn)。而在軍事體育運動中,射箭作為古老的運動,也能從瓷器上窺見一二。《陶枕》中收錄的宋磁州窯女子蹴鞠紋枕,利用白底黑花技法,描繪了一女子背著雙手,隨意表演蹴鞠的場景。馬球運動不僅史書上有記載,出土的文物中,也不乏唐代女子打馬球彩繪陶俑。而圍棋作為我國古代棋類運動中影響最大,盛行最廣的一種,河南安陽曾出土過隋代白瓷圍棋盤,山東淄博窯則有宋金時期的陶瓷圍棋子出土。唐宋時相撲運動比較流行,曾出土過反映當時運動場景的小兒群俑和瓷畫。山東濟南出土的西漢雜技俑,反映出當時雜技的熱鬧場景,之后,河南洛陽出土的倒立俑,更是構思巧妙,令人稱奇。射箭作為一項運動十分古老,并且因為古時對軍事的重視,反映射箭的瓷器陸續(xù)出土:魏晉狩獵紋畫像磚、唐三彩紋胎騎射俑、東漢射箭紋畫像磚等等。
一、明清兩代民間體育活動開展情況
而發(fā)展到明清兩代,由于生產(chǎn)力的提高,人們的生活有了質的改變。加上對于軍事的重視和西方文化的涌入,明清兩代的體育運動呈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特點。明清兩代傳統(tǒng)節(jié)日運動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在元宵節(jié)中有“跳百索”和“走百病”的運動。明弘治年間周用有詩云:“都城燈市春頭盛,大家小家同節(jié)令。姨姨老老領小姑,攛掇梳妝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頭風。踏穿街頭雙繡履,勝飲醫(yī)方二鐘水。誰家老婦不出門,折足蹣跚曲房里。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緣。蘄州艾葉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燃”[2]。《章丘縣志》中載“正月‘元夕’,設燈棚,具攤戲。次日,過橋、走百索”,而《清嘉錄·正月·走三橋》中有載“元夕,婦女相率宵行,以卻疾病。必歷三橋而止,謂之走三橋”。明萬歷年間沈榜所著《宛署雜記》也有記載:“正月十六夜,婦女群游祈免災咎,前令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橋之所,三五相率一過,取渡厄之意。或云經(jīng)歲令無百病,暗中舉手摸城門釘一,摸中者,以為吉兆。是夜馳禁夜,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俱不閉,任民往來。廠衛(wèi)校尉巡守達旦”。此外,還有清明節(jié)時的“踏青”和無人不知的“蕩秋千”和“放風箏”。《帝京景物略·出場》中有“三月清明日……是日簪柳,游高粱橋,曰踏青”的記載。同時,從古時傳承下來的體育項目,如摔跤、圍棋、武術、射箭等等,都得到了明顯的發(fā)展。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江蘇《武進、陽湖縣合志》有載:“三月,雨絲煙柳欲清明,正兒童紙鳶飛舞時候,亦毗陵為勝。美人、蝴蝶,云際蹁躚,風弦鏦錚,清若唳鶴。大或尋丈,比夜懸燈百盞,望若燭龍徑天,甚又系煙火放之,好事所為,亦風俗之靡也。俗呼紙鳶為鷂,至日謂之。‘放斷鷂’云”[3],生動描繪了放風箏的場景。而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招遠縣志》則描繪了蕩秋千的盛景:“正月十六日殘燈,皆游玩,不禁夜。婦女相伴為秋千戲……三月‘清明,男女簪柳。士人攜榼尊招飲,野外尋樂,謂之踏青。女子即’上元節(jié)‘秋千,習輕趫為戲,有立秋千、轉秋千二者”。多種運動和多種文化的交流、碰撞,讓明清兩代的體育活動十分昌盛,豐富多彩。
這種豐富多彩的特點,直接反映到明清兩代的瓷器繪畫藝術中。明清瓷器繪畫中表現(xiàn)體育的手法多種多樣,不拘一格,依托的載體也各不相同。明代成弘時期,瓷器繪畫中的風格偏淡雅,而到了清代康乾盛世時期,題材變得十分豐富。不僅有兒童嬉戲的場景,還有蹴鞠、武術、雜技等各種運動,對于軍事戰(zhàn)爭的描繪也相當?shù)轿唬绕涫乔嗷ù缮侠L畫對體育的描繪,比起其他瓷器更加獨特、到位。
二、明清兩代瓷器繪畫藝術中的體育活動
明清時期的瓷器在我國瓷器整體發(fā)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意義,在明清兩代瓷器繪畫藝術上,古代工匠對于體育運動的描述無論在范圍還是技巧上,都有了質的提升。明晚期“明紅綠彩嬰戲圖碗”(圖1)描繪的是兩個孩童正在玩耍,畫面中,兩個孩童一左一右,一前一后,揮舞著雙臂,似是在進行賽跑的游戲。前面的孩童著紅衣、綠色褲子,而后面的孩童身著綠衣,紅色褲子,色彩鮮艷,孩童之間的玩耍氣氛營造得相當?shù)轿弧Ec之相對的是清晚期“青花嬰戲圖紋大盤”(圖2),盤面的繪畫中有八個孩童,正中的孩童用白布蒙著雙眼,高舉雙手,似在威嚇附近其他孩童。而其他七個孩童呈上一下一左三右二圍成一圈,在蒙眼孩童的四周游蕩,這些孩童玩的正是“鬼抓人”的捉迷藏活動。畫面中的孩童神情各異,舉止滑稽,有蹲坐在地的,有作勢要跑的,有倒在地上不肯起來的,有準備去扶倒地孩童的,有兩個孩童站在一起,似是正要打算加入的,甚至還有一個孩童拿著樹枝,樹枝上掛著一條魚燈。整個畫面將孩童的可愛、調皮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躍然紙上,令人嘆服。與之相同的是,在另一件“清晚青花嬰戲圖紋盤”(圖3)中,九個孩童玩起“老鷹抓小雞”的活動。畫面中,八個孩童排在一列,一個抓著一人的后背,緊緊靠在一起,最前面的孩童張開雙手,作保護的姿勢。八個孩童面部表情類似,衣著打扮也近乎相同。最右側的孩童面部表情不同,衣著打扮也有些許差異,同樣張開雙手,卻是要抓住隊伍里的人。畫面整體感很強,充分體現(xiàn)了孩童的活力和朝氣,令人莞爾。

圖1 明紅綠彩嬰戲圖碗

圖2 青花嬰戲圖紋大盤

圖3 清晚青花嬰戲圖紋盤
由于無論是明末還是清初、清末,都是社會動蕩的時期,戰(zhàn)事頻繁,社會凋零,明清兩代瓷器繪畫中對于軍事的描繪也相對其他朝代有著自己的風格。在古代,由于對體育活動沒有明確的定義和規(guī)范,養(yǎng)生、雜技、游戲、軍事、球類、棋類等等都是體育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由軍事戰(zhàn)斗技能轉化而來的軍事體育,由于軍事戰(zhàn)斗技能有明顯的觀賞性和實用性,也成為統(tǒng)治者推崇的體育活動之一。“大明萬歷釉里紅刀馬人物瑞獸銜環(huán)輔首將軍罐”(圖4)中描繪了明軍戰(zhàn)斗的場景,構圖中中間有一人,高舉黃色紅邊旗幟,不遠處有停泊的戰(zhàn)船和軍營,似是正在進攻。雖然畫面中并未勾勒戰(zhàn)爭的場景,但卻渲染了大戰(zhàn)的來臨,將戰(zhàn)爭的殘酷和激烈描繪得淋漓盡致,讓人好奇接下來戰(zhàn)爭的走向。“清晚期哥釉粉彩刀馬格斗紋瓷罐”(圖5)中用灰色的旗幟和綠色的旗幟作為區(qū)別,描繪了一場正在進行的戰(zhàn)斗。背景有豎木建造而成的扶欄,應該是一座橋上。遠處寥寥幾筆勾勒出山的形狀,此起彼伏。畫面右側為手持彎刀和盾牌的士兵,左側同樣為士兵,但一位騎著高頭大馬的將軍尤其引人注意。與“清中晚期釉里紅刀馬格斗紋瓷缸”不同的是,畫面中對于人物和馬匹的描繪相當精細,不僅武器、衣物、裝飾都進行了精心刻畫,甚至馬匹身體各處的顏色區(qū)別都體現(xiàn)了出來,馬匹的馬鬃和將軍的胡須也有詳細的刻畫。雖然明清兩代瓷器對于軍事的刻畫要有所突破,但受于軍事題材瓷器出現(xiàn)時期的約束,社會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上處于消極狀態(tài),對于瓷器畫面的刻畫也就相對單一、雷同,缺乏藝術性和想象力。

圖4 大明萬歷釉里紅刀馬人物瑞獸銜環(huán)輔首將軍罐

圖5 清晚期哥釉粉彩刀馬格斗紋瓷罐
除此之外,還可以在一些傳世的瓷器藏品和碎片中,看到豐富的體育活動。如明晚期青花瓷碗外壁描繪的兒童習武圖、明晚期青花瓷片上描繪的兒童習拳圖和兒童摔跤圖、明晚期青花瓷盤殘片上描繪的兒童蹴鞠圖、明晚期青花瓷碗殘片上描繪的兒童溜冰圖和女童蕩千秋的圖案等。
三、明清兩代瓷器繪畫藝術中體育的文化內涵
在我國,瓷器文化與體育活動的發(fā)展交相輝映,相互表現(xiàn),互為融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在表現(xiàn)題材上,山水風景、人物形象、音樂舞蹈都成為題材的一部分,而在載體上,不僅有瓷盤、瓷碗,還有瓷罐、瓷瓶等等,在工藝上,有青花瓷、粉彩瓷,還有釉里紅、五彩瓷等等。這些成就,為體育活動在瓷器繪畫中的表現(xiàn)提供了物質、社會和技術基礎。
相對而言,明清兩代瓷器繪畫中對體育活動的描繪,更加具有社會生活氣息,加重了對普通社會群眾日常體育活動的關注。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生產(chǎn)力的提高,社會大眾對于瓷器需求的增多和對品質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瓷器生產(chǎn)開始迎合社會大眾的喜好,瓷器繪畫的內容也得到進一步拓展。同時,由于明清兩代對外交流的增多,瓷器作為我國與茶葉齊名的象征物,得到當時國外貴族和普通百姓的歡迎和追捧。我國瓷器的對外出口,擴大了明清兩代體育活動的影響范圍,也將體育題材瓷器繪畫藝術的地位提高到極高的層次上。明清時期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富足的百姓生活和廣泛的市場需求,帶動了瓷器繪畫藝術中對體育活動描繪的進步和發(fā)展。以史為鑒,在我國現(xiàn)代體育的發(fā)展過程中,應當重視將體育與藝術進行結合,在為藝術提供題材和靈感的同時,也能進一步促進我國體育事業(yè)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洪志華,宋迎東.中國古代陶瓷文化藝術中蘊涵的體育文化探析[J].中國陶瓷,2008(12):86~89.
[2]王廣宇,單亞萍.陶瓷文化對體育運動的影響[J].中國陶瓷,2007(01):40~41.
[3]魯芬芳.試析我國古代陶瓷對國外的影響[J].陶瓷研究,1993(03):166~168.
(作者單位:常州市文物保護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