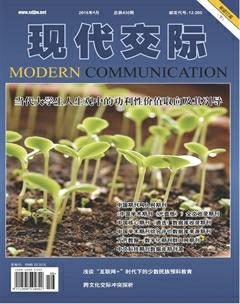大慶地區歷史文化遺跡在黑龍江流域文明中的價值
王勇 崔永鋒 王真真
[摘要]大慶地區的歷史文化遺跡分布于城市所轄的五區四縣,嫩江與松花江流經大慶境內,在今天的肇源縣匯合并且向東北方向最終流入黑龍江,可以說,大慶地區的文明是黑龍江流域文明的一部分。諸多的文化遺跡承載著相應的文化內涵,見證了這座城市歷史文化的變遷,同時也在一定的時間維度內構筑著這一區域的文化生態系統。大慶的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單一的,而是黑龍江流域文明的延伸與補充,演繹出黑龍江流域幾個典型的文化時期所反饋出的日常生產生活模式的變化過程,勾勒出自然環境與人類生存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展現出人與自然博弈下的生命張力。我們認為大慶地區歷史文化遺跡是黑龍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變遷的一個樣本、黑龍江流域局部經濟生活模式演變的典型案例,大慶是黑龍江流域文化復興的一個實踐基地。
[關鍵詞]歷史文化 黑龍江流域 文化生態 經濟生活模式 實踐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8-0058-03
“據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表明,大慶共有文物遺址319處,包括古遺址208處、古墓葬14處、古建筑1處、近現代遺址89處、其他類遺址7處。其中文化遺址266處,石油工業遺址53處;4處國保單位、10處省保單位、83處市保單位。”[1]我市的文化遺跡在五區四縣境內皆有分布,古代文化遺址多集中于肇源縣、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大同區這三個地方,其中肇源縣的白金寶遺址、小拉哈遺址被確定為國家級的歷史文化遺址,此外肇源縣還有望海屯古城等兩處省級歷史文化遺址;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有省級文化遺址四座;大同區有省級歷史文化遺址一座。從目前我市考古發現來看,大慶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遺跡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夏商周)、遼金時代、清代等時期。近現代歷史文化遺存主要有石油文化遺存、中東鐵路文化遺存、抗日及剿匪時期歷史文化遺存,其中文化價值較高的主要集中在石油文化遺存與中東鐵路文化遺存中。石油文化遺存主要集中在大慶市內五區境內,在石油文化遺存中,“松基三井”和“鐵人第一口井”屬于國家級保護文物。中東鐵路文化遺存主要集中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境內,讓胡路區也有一點,其屬于省內中東鐵路文化的一部分。抗日及剿匪時期歷史文化遺存主要集中于肇州、肇源等地。
嫩江與松花江流經大慶境內,在今天的肇源縣匯合并且向東北方向最終流入黑龍江,可以說,大慶地區的文明是黑龍江流域文明的一部分。諸多的文化遺跡承載著相應的文化內涵,見證了這座城市歷史文化的變遷,同時也在一定的時間維度內構筑著這一區域的文化生態系統,大慶的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單一的,而是黑龍江流域文明的延伸與補充,演繹出黑龍江流域幾個典型的文化時期所反饋出的日常生產生活模式的變化過程,勾勒出自然環境與人類生存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展現出人與自然博弈下的生命張力。
一、大慶地區歷史文化遺跡是黑龍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變遷的一個樣本
位于肇源縣民意鄉大廟村的白金堡文化曾經被推測為昂昂溪文化的延伸,很有可能是“北夫余族先世的文化遺留”[2P25],白金堡文化遺址充分地證明,“濊貊人已經從新石器時代發展到青銅時代”[3P2]白金堡文化的發現填補了松嫩平原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過渡時期的文化考古空白,“其豐富的遺存和文化內涵,激起人們對松嫩平原古代先民的生活情景無限的遐想和探究。”[4P22]濊貊人是生存在大慶地區的早期民族,其屬于夫余族的北支,后來逐漸地融合到肅慎、東胡民族系統之中,其開辟了這一地區的文明。
位于肇源縣的出河店古戰場遺址,則記錄了這一區域內女真與契丹人之間的一場決定命運博弈,據史料記載,為紀念金太祖以少勝多,肇基王績于此,也因為此地位置重要,故在此地設置城防,取名為肇州。除肇源外,在我市的杜蒙縣、肇州縣及大同區有大量的遼金時代的文化遺址,多以村屯遺址為主,充分地體現了契丹民族、女真民族對中原文明的接受,以及這一地區在遼金時代的經濟文化的繁榮程度。另據王禹浪先生所著《金代黑龍江述略》統計,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黑龍江省共發現具有一定文化價值的金代大小古城遺址共計157個,其中大慶市共有10個,主要集中于肇源縣境內,一般周長在1000米以下的較多,周長超過1000米的古城有位于肇源縣民意鄉健民村的他代海古城,周長1240米,以及位于肇源三站鄉的望海屯古城,周長3000米,這些城垣均和古肇州城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其屬于金代肇州文化的一部分,目前位于肇東縣境內的八里城遺址(周長4000米)也同屬于金代肇州文化的一部分。
元代存在的歷史時間較短,但對大慶市歷史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目前尚未發現典型的元代歷史文化遺存,但從史料上可以發現“金元之際的戰爭,把遼金建立的古城變為廢墟,人口減少,土地荒蕪。”[3P10]元世祖登基之后,伴隨政治軍事的穩定,開始經營肇州地區,派劉哈喇八都魯重建肇州城。今天位于肇東縣境內的八里城遺址,是元代肇州的遺址。這里的民族結構發生了變化,元朝在此地實行屯田,“1295年肇州蒙古屯田萬戶府設置時,那里有蒙古、乞里吉斯(吉爾吉斯)、女真、水達達、漢人等650戶,屯田1500傾,元政府把參加乃顏、哈丹叛亂的叛軍,以及宋朝投降的漢軍和東北各族人民,還有一部分罪稍輕的犯人,發配到肇州屯田。到元末,肇州人口最多可達4至5萬人。”[3P10]
明代生活在肇州的主要民族有兀良哈蒙古和海西女真,到清代前期,1648年設立郭爾羅斯后旗,管轄今天大同區及三肇一帶。同年設置杜爾伯特旗,管轄今天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市區大部及林甸、安達等地。兩個旗的設置,說明在清代初期的時候本地的民族主要由蒙古族構成。從一些清代遺址來分析,比如肇源一帶的清代文化遺跡,這里的文化生態是以游牧文化為核心的蒙古族文化,以及沿江一帶以漁獵為代表的滿族、錫伯族文化,還存在著以農耕為基礎的站人文化(站人,指的是清初三藩的部下,主要以漢文化為主),各種文化共存,共同支撐了這一地區在經濟文化的繁榮。值得一提的是“站人接受漢人、蒙古人、滿人、云南少數民族的熏染,形成特有的生活習慣和風俗。”在中東鐵路建成前后,出于經濟及政治利益的考慮,先是蒙旗私自招民人開墾熟地,這一方面不單是蒙人這樣做,東北黑龍江、吉林等地的滿人也這樣做,東北歷史上著名的闖關東的時代到來了,關內人口的遷入,充實了東北的人口以及勞動力,活躍了這一地方的市場,沙俄在東北建設中東鐵路之后,為了防止沙俄的滲透,清政府先后四次出放“蒙荒”。來自河北、山東一帶的漢族人進入,加速了這一地區的生產力水平、經營模式的改變,也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在石油大會戰的大潮中,在大慶油田的建設開發中,來自全國各地的石油工作者及家屬匯集于大慶油田,使得大慶地區成為一個移民人口占主體的新興工業基地,但傳統的民俗、民族文化并沒有因為移民的浪潮所遮蔽,大慶的文化兼容并包,但卻保持著濃郁的地域特色,那種草原民族特有的氣質與大慶會戰時期的革命英雄主義、闖關東精神有機地契合形成了大慶人熱情、好客,勇于開拓、不畏困難的實踐精神。
民族的遷徙,所帶來的是文化生態的演變,這種生態的演變包括民族之間文化的博弈與對抗,也包括著民族之間文化的溝通與圓融,最后不同的文化之間形成了耦合的狀態,推動了社會文化的演進,各種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同構了這一區域的文化生態系統,縱觀大慶的歷史文化,盡管這一地區在歷史上屬于少數民族文化圈,但中華文明的影響,早在白金寶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在本地的出土文物來看,遼金時代漢民族的文化、乃至貨幣都已經在這個區域出現,從元代開始,漢族人就已經在此地耕種,特別是清代站人的遷入以及闖關東的移民潮的到來,漢民族文化直接與當地的少數民族文化相交流,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可以說大慶的歷史文化遺跡為世人提供了黑龍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變遷的一個樣本。
二、大慶地區歷史文化遺跡是黑龍江流域局部經濟生活模式演變的典型案例
大慶市境內一些歷史文化遺跡,充分地展現了特定時空內的經濟狀況,雖然不是當時的經濟全貌,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時的經濟發展的程度,歷史文化遺跡中所滲透的信息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個黑龍江流域局部經濟生活模式的典型案例。
白金寶文化出土的物件器皿,表明了濊貊人在手工業方面已經掌握精致石器、蚌器、骨器的制作,但需要說明的是他們還掌握了青銅器、陶器的制作,從器皿的性用上判斷濊貊人在漁獵、手工業甚至農業方面都有較大的發展。白金堡遺址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在黑龍江流域局部地區中具有典型的普遍意義,“與白金寶文化相似的遺址,分布在以嫩江中下游和松花江上、中游為中心的松嫩平原上。可以說白金寶文化的提出,為推動松嫩平原及鄰區從石器時代經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礎。”[5P30-32]
在大同區老山頭鄉金代遺址中發現的“大片的鐵煉渣,這里四周為平原,沒有鐵礦石可采,說明這里是粗鐵制造和鍛造加工的地方。另外,肇州鹽堿地比較大,盛產食鹽和堿。八里城出土熬鹽的工具證明了這一點”[3P7]“肇州鹽是金代上京路各地居民食鹽的主要供應地。”[2P174]“金代遺址還出土了少量的瓷器、銅器。托古翻身屯曾出土銅盆、銅佛。1978年,在巴彥縣還出土了‘肇州司侯司監造的鸞鳥銅鏡。”[3P7]金代商業發達,一些金代遺址頻繁地發現大量的宋朝貨幣,驗證當時商業交往的頻繁,以及中原王朝對塞外政權經濟文化的影響。
在近代中東鐵路的修建,將現代文明植入這個區域,據《蒙古地志》記載“鐵路兩側開墾地的大部分農產品,由該鐵路北運南輸,其中安達站是哈爾濱以北,齊齊哈爾以南的大站”[6P105],這里成為糧食和農產品的中轉站,鐵路也方便了本地的農產品、堿、活魚和畜產等輸送出去,這里的堿產量在民國初年“年產量約達兩千萬斤,向齊齊哈爾、哈爾濱、伯都納、長春等地出售。”[6P105]但一些日用品諸如,布匹、雜貨、調料、陶瓷器皿、石油等都需要外部臨近大城市供給。
肇州縣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伴隨著漢族人的遷入民族工商業興起,比如“1903年徐家圍子燒鍋建成。成為全縣第一個工廠,接下來全縣又有一些工業部門主要生產桌椅、車輛、青紅磚、鐮刀等”[3P25],到了“1914年,全縣有較大的工廠七座,其中5家是燒鍋,兩家生產豆麻油。清末民初肇州縣的商業豐樂最繁華為全境經貿中心,其次是老街基、縣城、大同等城鎮,這里的商戶主要來自長春一帶。”[3P25]
石油會戰及石油工業建設歷史文化遺存,主要由松基三井、鐵人第一口井、大慶油田歷史陳列館、鐵人紀念館等傳統歷史文化遺存與大慶石油博物館、大慶科技館、油立方等新興的具有科普文化功能的紀念場館構成,此外還包含石油石化企業單位自身的歷史陳列館室等。這種文明的意義主要呈現在以下三個維度,歷史維度上,其記載著大慶工業的發展歷史,有助于我們總結反思歷史,借鑒歷史經驗,推動城市工業發展實踐的高速穩步進行;在科學維度上其普及了石油科技知識,開拓人們的文化視野;在倫理維度上,其充分演繹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引導對市民日常價值觀實踐。具體說,其為我們展示了陸相沉積理論指導下我國石油勘探領域的超越與升華,讓我看到了老一代石油人的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以及大慶石油勘探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豎起的歷史豐碑,老一代科技工作者、油田的廣大干部職工家屬堅守自己的崗位,恪盡職守,榮耀了這片土地,也照亮了新中國工業前進的方向。
縱觀大慶歷史文化遺跡所呈現出的特定境遇中的經濟現狀,我們發現,在這一地區的歷史上,經濟發展幾度沉浮,其有自身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也有產業結構單調不協調的弊端。《蒙古地志》中記載,養雞業的突然崛起來自于附近大城市諸如哈爾濱的需求量大,而且利潤高,這體現了養殖行業對周邊市場的依賴,這種依賴有積極和消極兩面。郭爾羅斯后旗(肇州、肇源、肇東、大同區)一帶,盛產馬,牛羊數量少是因為附近哈爾濱城市需求量大,而杜爾伯特旗的馬匹由于日俄戰爭時俄國的大量征用,至民國初年尚未恢復其原來產量的十分之三四。在這種境況下雙方本可以結合各自的需求進行合作,但是那種封建式的經濟,所缺乏的正是一種開放的合作的機制。不過在各自為政中,封建主也會考慮自身的需求,這是一種生存的本能。還有一些地方特產如“皮硝,還有一些野生藥材出產也沒有人采集。”[6P94],這說明對一些潛在的市場,身為局內人的我們往往缺乏必要的調研和關注。我們認為要保持經濟、文化的持續繁榮就必須發揚傳統文化中的銳意進取、和實生物、慎思篤行的精神,摒棄消極保守、孤軍單干、缺乏統籌協調、盲目跟進的思想。此外,我們要注意交通網絡的建設,當時肇州地區的基層中心建設按照的是以驛站為中心的格局設置的,而古驛站所承載的不單純是軍事功能,更有其經濟功能,比如海西西陸路、清代的邊臺等驛站路線均在此境內穿過,我們要利用一帶一路的大環境打開區域內的一代一路的小環境。
黑龍江流域的經濟可能受到行政區劃、自然環境、遺跡傳統的經濟圈等因素的制約,因此以文化考古的方式,反思其中某一個區域的歷史經濟發展演變,總結經驗教訓,并結合當前的地情做出有益于局部和整體的判斷對構建一帶一路視域下的區域經濟聯合體十分重要。
三、大慶是黑龍江流域文化復興的一個實踐基地
大慶地區的歷史文化遺跡的發現、發掘、保護、宣傳不斷地沿著科學有序的思路進行。其實在大慶地區保護恢復歷史文化遺跡,對黑龍江流域文明的保護和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我們所提倡文化復興,這種復興不是單純地復古,而是批判繼承歷史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并且結合實際創新文化新模式,更好地傳播中華文明。
第一,歷史文化遺存建設過程中我們要采用文化哲學的方法,將歷史文化遺存分好類,將我市的歷史文化遺存分為工業文明、闖關東移民文化、中東鐵路文化、草原文明、農業文明等若干個文化群落,將歷史與日常生活相契合,讓每一個文明下面都能孵化出一種代表性實體經濟,特別加大生態經濟方面的權重,以此作為頂層設想,將這些經濟實體融合到城市的旅游文化中形成一個在旅游經濟引領下的新的經濟網絡。
第二,歷史文化遺存建設要與市民文化素養建設相結合。要讓家鄉的歷史深入人心,必須加強人們的歷史文化素養,在義務教育與日常宣傳領域普及地方的歷史文化知識。這樣做并不多余,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有數百個歷史文化遺跡,但是能夠保存下來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的并不多。在整個城市的文物普查中,離我們最近的一些近現代建筑,也由于一些自然或者人為的原因遭到破壞,破敗不堪或者蕩然無存,我市境內的中東鐵路建筑群也像省內及黑龍江流域其他地方的中東鐵路建筑群一樣面臨著這樣的境遇,如果不是從事相關研究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平時鐵路邊不起眼的黃色小房子和當年一個龐大的工程與黑龍江的近代化有關系。許多文物都毀于戰亂、動亂的浩劫之中,一些古代遺址也淹沒于自然的風化之中,有誰會在意那些不起眼的土圍子呢?文物考古部門的石碑見證了發掘遺址的過程,但是又有多少人對這個感興趣呢?也許更多的人對文物關心是在于文物能夠賣個好價錢。如果我們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那么我們也不能夠正視自己的根本,這樣的人極容易陷入歷史的虛無主義。
第三,加強城市區域歷史文化研究,通過古籍、歷史檔案整理,對一些已經毀滅的文化遺存進行修復,發揮其文化價值,這種修復在國內許多地區都存在過。比如,雙城的魁星閣、江西的滕王閣、杭州的雷峰塔等。但一切要依據歷史文獻的記錄,尊重歷史,沿著歷史的軌跡去進行,這樣才能夠彰顯恢復古建筑的文化意義。
第四,大慶地區歷史文化遺存的發掘、研究工作需要調動的不單是省市兩級的考古與博物館學的專業人士,還需要各個學科的相關專家,由于行政區劃的改變,歷史地理與現實地理之間還存在著很多的差別,因此需要跨區進行系統研究,比如古肇州包含今天的綏化地區的肇東市、古杜爾伯特包含今天綏化地區的安達市,這樣的例子在整個黑龍江流域文明研究、發掘的過程中也是經常遇到的。
第五,加強學術交流,我們經常會有黑龍江流域歷史的研究會議,希望這樣的研究會議多吸收地方的一些研究者參加,而且應當覆蓋整個流域的具有文化代表的地區,加強學術交流提升學術縱深。
四、小結
大慶的歷史文化遺跡從多個層面反映了松嫩平原西部近五千余年的歷史變遷,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幾度出現文化斷裂,但在其與中原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下,幾度在這個區域內打造出高度的文明,而且在這塊土地上民族文化的圓融鑄就了這里的文化傳統,這里的經濟模式從單一走向多元,生活模式由游牧走向定居,這里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在黑龍江流域乃至東北其他地方都具有典型性,這里的文化建設實踐,本身是黑龍江流域文明建設的一部分,同時對整個黑龍江流域文明建設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1]大慶遺跡.[EB/OL]大慶地情網:http://dqdqw.daqing.gov.cn.
[2]吳文銜,張泰湘,魏國忠.黑龍江古代簡史[M].哈爾濱:北方文物雜志社,1987.
[3]劉邦中,周德中,王樹文.肇州歷史[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4]米大偉.黑龍江歷史[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12.
[5]李福民.白金寶文化探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
[6]布林,柏原孝九,濱田純一.蒙古地志[M].呼和浩特: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資料復制社,1986.
責任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