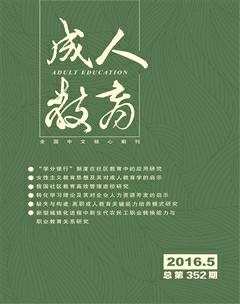女性主義教育思想及其對成人教育學的啟示
常杉杉
【摘要】女性主義發展的根本宗旨是為了爭取男女兩性在各方面擁有平等的權力,西方三次女性主義運動浪潮,產生了諸多女性主義的流派,也促進了教育領域內的女性主義教育思想的發展。文章對三次女性主義浪潮及其影響下的教育思想進行簡單總結,并嘗試從六個角度分析了對成人教育學發展的啟示,以期在女性主義思想的積極影響下促進成人教育學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關鍵詞】女性主義;成人教育;啟示
【中圖分類號】G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794(2016)05000804
女性主義,也被稱為女權主義、婦女解放、性別平權主義等,世界范圍內的女權運動、女性主義發展的根本宗旨都是為了爭取實現兩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擁有平等的權力。人類歷史上,“人權”的概念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但人權的概念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并不包括女權。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來源豐富,最早有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思想,還有種族平等運動、后現代主義思想等等,女性主義教育思想隨著女性主義思潮的不斷發展呈現多元化的狀態。
一、三次女性主義運動浪潮及與之對應的女性主義教育思想1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次浪潮(the firstwave)
17—18世紀,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爆發資產階級革命,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號,但是曾經參與革命、為之奮斗的女性在戰后仍未得到和男性一樣的平等權利,從而引發了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爆發,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上半葉形成了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次浪潮,她們要求獲得與男性平等的社會、政治、經濟等權利。具有代表性的有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權辯護——關于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泰勒(Harriet Hardy Taylor Mill)的《婦女的選舉權》(Enfranchisement of Women)、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西蒙·波夫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等著作。
該階段女性主義思潮主要表現為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自由主義崇尚理性,認為人生來是自由平等的,都有推理能力,在受教育后應該具有同等的理性,因此教育應強調人性,對男女應給予同質的對待。早期自由主義重在對“父權制”①觀念的批判,“父權制”下的教育主張男女不同角色的培養,如盧梭指出,男女性別的差異不僅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一個完善的市民社會所需要的;同時,在道德培養方面也有著天然的差別,女性受母親的影響只需要做到服從與禮節,洛克也認為在某些方面不同的性別應不同對待。[1]他們認為教育應依性別差異而有所區分。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對“父權制”在教育主張上的批判,指向當時的教育系統改革,著眼于“平等的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社會化和性別刻板印象”(socialization and sex stereotyping)以及“性別歧視”(sex discrimination),力爭消除性別壓迫、追求女性與男性的平等教育權。他們甚至提出了實踐中的具體建議,一方面從提高社會成員的意識入手,讓大家充分認識教育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努力避免這種不平等現象;另一方面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為女性的平等受教育權提供保障。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對于女性追求自由與機會平等,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等的改革發揮了巨大的價值,可以看成是所有女性主義流派的出發點、起點,后來的女性主義流派以它作為改造、修正的對象。
2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the secondwave)
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是女性主義較早階段在英美國家婦女要求參政等運動的延伸,它伴隨著美國黑人解放運動、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等民主運動而生。“個人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被認為是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中被廣為流傳的一句口號,它把婦女的解放與社會改造相結合,試圖從社會中尋求女性被壓迫的根源。美國《平等權利修正案》(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ERA)早在1923年就被提出,在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中復興,最終在最后期限的1982年以三州之差未獲批準,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走向低潮。具有代表性的是女權主義者貝蒂·弗蕾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等。
相比較第一次女性主義運動者所關注的兩性機會平等,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更加強調女性的獨特性,矛頭直接指向造成女性偏見的社會意識形態,強調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它不僅看到了女性和男性在表面的社會分工上的不同,更加深入到了思維的深度,不僅局限于政治層面,更擴展到了文學、宗教、法律、哲學等多個方面。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浪潮期間產生出了諸多流派,如激進的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Marxist and Socialist Feminism)、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和心理分析的女性主義(Psychoanalytic Feminism)等等。激進的女性主義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以權力、統治和等級制為特征的“父權制”(patriarchy),在兩性差別的觀點上,經歷了從女性處于劣勢的歸因向否定男性、肯定女性的生理狀態的轉變過程,強調凸顯女性獨特的價值,將矛頭指向男性群體,并且提出了培養女性意識的主張,認為女性應該接受針對自身的教育或者再教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觀在內容上是基本一致的,她們是以修正激進的女性主義的姿態出現的,兩者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傾向于認為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是階級歧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可以看成是馬克思女性主義和激進的女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把原因總結為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相互作用造成的現實后果,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都認定婦女受壓迫是其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產物。黑人女性主義主要是批判種族歧視、父權制社會對黑人女性的雙重壓迫,以及在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差別對待。心理分析的女性主義著重研究女性受壓迫如何影響著她們的生活和性別特征,它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根植于她們的靈魂——女性獨特的養育分工,女性尋求解放需要有一種源于“內在的”和社會的革命。
這一時期的教育受到該階段女性主義思潮多種流派的影響,對當時的主流知識提出挑戰,研究課程和教學方法中帶有女性歧視的內容,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課程和教學方法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盡管該階段女性主義理論流派林林總總,但她們的主要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批判性別歧視,爭取消除兩性差異。較之之前的女性主義思想,她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明顯的先進性,但是依然沒有走出兩性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3女性主義運動第三次浪潮(the thirdwave)
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國家先后步入后工業時代,電子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社會職業以服務行業為主,理論知識占據主導地位。第三次浪潮女性主義受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影響,發展成為后現代女性主義。后現代女性主義批判挑戰關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敘事(Grand Theories),反對對性別、階級、種族做宏觀分析,主張局部的、區域性的、有歷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質的理論和實踐;反對傳統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論(Dualism),提倡多元整合的思維模式;反對同一性,關注并強調性別的文化差異,呼喚關注女性內在的千差萬別的經驗;反對男性霸權對于女性的壓迫,致力于建構女性話語,發出女性的聲音,主張與男性全面合作,建立和諧的伙伴關系,在差異中追求平等,在平等中彰顯個性與獨立。后現代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有琳達·奧爾科夫(Linda Alcoff)、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露絲·伊麗加萊(Luce Irigaray)等。
該階段女性主義思潮主要表現為批判的女性主義(Critical Feminism)和后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Poststructural Feminism)。批判的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其基本理論可以概括為多元民主、權力理論和社會性別。后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則更強調創造觀察和認識事物的新途徑,她們試圖用“多元性”、“差異性”等術語來闡述社會關系,重視“結構”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她們認為,個體是通過主動參與各種對話從而逐漸成長、成熟的,“正是沖突的話語形式中的語言使我們成為有意識的思考著的主體,賦予世界以意義,并使之流播”。[2]她們推崇“反話語”(reversediscourse)的表達方式,倡導在教育語境中女性的自我覺醒,同時關注女性的各種行為,重視賦予女性利益以特殊的權利,并分析在各種對話中女性權利的運用與保護、壓迫是怎樣發生的、以及如何進行反抗。
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有兩大派別,一是本質論,她們承認“男性”和“女性”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范疇,繼承、修正了傳統女性主義的理論,重新討論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女性解放的可能性。[3]本質論女性主義下的教育學對課堂中支配與被支配、壓制與被壓制的關系做出挑戰,認為每個人都處在權力關系中并行使著權力,認為知識是建立在差異的基礎上,而這種差異是建立在女性主體的、特殊的、自然發生的、有沖突性的歷史之上的;另一派別是建構論,她們否認“男性”、“女性”的觀念,認為基于兩性平等觀的討論本身就是男權思維的體現和延續,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建構論女性主義下的教育學倡導女性的思維方式——包容、合作、自然的內在關愛,試圖全面改善教育境況。后現代女性主義者認識到“女性身份”才是構成了女性成長、歷史和現實處境的獨特之處,在她們的教育討論中那些由于性別差異而帶來的個體、社會、歷史和民族的獨特性獲得了充分的表現,而這些才是教育的最重要的內容。[4]
二、對成人教育學的啟示
當代社會處于一個復雜的歷史轉型時期,多元的社會文化相互交鋒、碰撞、整合,雖然女性主義各流派的思想各異,都有其進步和局限所在,我們愿意摘取其進步的意義賦予成人教育更好的發展。
1從意識層面的角度——對成人教育價值觀的女性主義改造
著名美國教育學家約翰·杜威指出,“教育是達到分享社會意識的過程中的一種調節作用,而以這種社會意識為基礎的個人活動的適應是改造社會的唯一可靠的方法。”[5]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角色、兩性文化都可以看成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反映和維護現存的政治經濟結構的,在政治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也必然在意識形態中占統治地位。在現代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和“父權制”實則是一體兩面,這種意識形態和文化既是男女不平等的源泉,又把這種不平等合理化了。[6]女性主義教育觀體現了女性主義哲學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審視和批評其中的性別歧視因素,倡導一種開放的、多元的價值觀,建構新的成人教育教育觀。將女性主義提倡的注重關懷與情感、追求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價值觀補充到現有的成人教育觀中,建立女性主義成人教育觀體系。創造一個使女性可以說話、具有話語權的哲學空間,以自己對世界的認識、解釋加強女性對現實的改造。
2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度——接受并正確認識性別的自然差異
教育者、受教育者都應承認男女性別在客觀上的差異性和不可改變性,認可由此帶來的男性教育和女性教育差異的必然選擇,基于此,首先應該培養成人(尤指女性)對自己性別的愉悅認同,同時尊重對方性別的自然差異,女性教育的出發點應該是以承認這一自然差異為前提。從女性成長的自然規律的角度,成年女性必然經歷婚戀、生育及哺乳等時期,這個時期的女性尤其容易喪失自我的獨立性,產生更加強烈的依賴男性的心理,與此鮮明對比的是同階段的男性的自我意識不斷強化、膨脹,往往帶來了男性成功比例較大的現實結果。因此,成人教育應鼓勵女性強化自身的獨立意識,摒棄自卑或受歧視的觀念,形成女性自我發展的內在動力。
3從教學內容的角度——將性別意識納入主流課程
課程是女性主義教育所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成人教育領域亦是如此。課程是教育內容的體現,無論是課程政策或者內容的制定者還是執行者對于個體性別差異的認識往往是欠缺的,往往容易導致造成一種男性話語霸權的局面,因此,在課程中融入性別意識是反思和重構整個成人教育課程的重要任務。首先,從課程政策方面看,通過增加決策領導層中女性的比例來賦予女性群體更大的權力;其次,從課程的執行來看,通過平衡師資性別比例優化教學環境,更需要加強成人師資的培養,增強他們在教學中的性別意識,更多地關注女性群體的特點、尊重她們的學習方式等。性別研究課程可以包括女性解放的歷史、女性現狀的概述、女性對于教育的參與、女性權益等等,更應該包含女性主義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它不僅僅是以某種具體內容的形式而存在,還可以存在于各個學科之間成為一種重要的、具有指導性的價值觀,性別課程發展的要求應當是以課程為媒介把性別意識納入到主流課程中去。
4從成人經驗的角度——促進學習和積累
在成人教育學理論中,經驗是一種學習資源,它隨著成人自身的不斷發展成熟而逐漸積累并不斷豐富,是他們主動學習所依賴的資源。事實上大量的女性是從傳統的生活實踐的結果中接受教育的,就在這樣世世代代自發和隨機的過程中,無數女性的生命活力逐漸萎縮,遠未達到她們原可達到的發展水平。[7]成人在社會和生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承擔著不同的任務,每個人會因為性別角色、社會角色的不同,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產生不同的理解與追求,成人教育應該幫助不同領域內的女性做出合理的選擇,幫助她們提高認識、樹立正確的心態。
5從培養目標的角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所有教育的根本目標都是大寫的人字,都是為了達到人的完整實現,女性主義思想的發展無疑深化了這一理念。女性主義哲學家塞拉·貝恩哈比卜(Seyla Benhabib)認為,“一個解放了的社會和充分發展的個人暗示著另外的社會和個人……因此,未來的方案始于在我們的需要和愿望方面進行一場革命”。女性主義本身是多元的,對于未來的藍圖的描繪也是豐富多彩的,但他們共同奮斗的最基本目標是女性和所有被壓迫者的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
6從成人教育研究的角度——以歷史發展的眼光積極尋求法律與政策的保障
教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背景中的,沿著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教育的歷史發展,不同的歷史時期凸顯出不同的主題,如今,在中國女性受教育的權利已寫入莊嚴的憲法,并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支持和保障,但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女性教育依然不斷涌現出許多新的問題,成人教育研究者應不斷加強女性教育所必需的社會條件和保障機制的研究,積極探索、不斷尋求女性教育和發展的新的法律與政策保障。
女性主義的發展、各流派之間的爭辯本身呈現出了一種超文化的方法論,女性主義本身至今沒有統一的思想,而承認自身理論的局限性,接受各流派思想的差異這一表現和姿態,較之于一味追求“平等”更有利于女性解放,這種“圣杯”式的女性思維對成人教育學的發展、對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無疑也是具有積極促進作用的。
【注釋】
①“父權制”一詞由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于1970年在《性政治》一書中首次提出。
【參考文獻】
[1]甘永濤.傳統、現代、后現代:當代女性主義教育的三重視野[J].教育科學,2007,23(2):22.
[2]克里斯·威登(Chris Weedon).女性主義與后結構主義[J].林樹明,譯.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1994—2010:68.(翻譯來源于《女性主義實踐和后結構主義理論》(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1987)
[3]張文軍.后現代女性主義教育學述評[J].比較教育研究,2000,(2):8.
[4]甘永濤,王新華.后現代女性主義教育學的來龍去脈[J].比較教育學,2008,(3):20.
[5]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M].趙祥麟,任鐘印,吳志宏,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4.
[6]肖巍.女性主義教育觀及其實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60.
[7]葉瀾.女性教育研究深化之我見[J].中國婦運,1995,(3):20.
【Abstract】The fundamental tenet of Feminism is struggling of getting the equal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all aspects. Several of genres of Feminism have been presented in the three waves of Western feminist movements, so did the feminist pedagogy.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m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enlightenment to andragogy in six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ndragogy und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of Feminism.
【Key words】Feminism; andragogy; enlightenment
(編輯/趙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