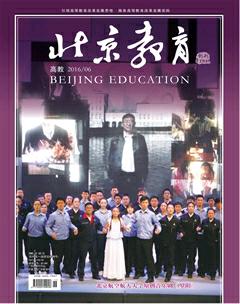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意義
張翼星
摘 要:“通識教育”的名稱和實施,雖然源于西方,但并不是什么單純的“舶來品”,我國從古代到現代也有著相近的豐富資源有待我們深入發掘。“通識教育”是一種自由、通達的教育,一種重視文明、人才傳統的教育,一種拓寬基礎、培養高端人才的教育。近十年來,各大學在本科生教學中設置通選課,開展通識教育。但究竟為何開展通識教育?如何合理設置通選課?這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通盤考慮、合理安排的問題。
關鍵詞:通識教育;通才;現代大學;通選課程
美國現代“通識教育”蹤跡
現代研究型大學,究竟主要培養專才還是通才?古典人文教育與各門科學內容和方法的教育、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它們的關系和位置應當是怎樣的?現代通識教育的嘗試,出現于1917年—1919年的哥倫比亞大學。直至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逐漸形成哥倫比亞大學本科通識教育的體系與制度,隨后在美國各大學通行起來。
美國關于通識教育的闡述和部署,有兩個基本文獻。一個是芝加哥大學原校長哈欽斯(Robert M. Hutchins)在1936年發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國》,其中第三章專講“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尖銳批評了當時在美國的中學與大學只為升學考試服務的應試教育傾向,批評了大學里的功利主義和唯市場取向的專業設置和教學內容,使研究型大學日益變成職業培訓的場所,這只會導致大學理念的消失。在哈欽斯看來,現代大學的教育應當首先是一種“共同教育”(Common Education),即“通識教育”,才能有一種共同的文化語言,在專業上互相溝通。現代大學必須有自己獨立的教育理念,培養共同的精神與文化根基。現代大學若要成為現代科學的創新之所,應當首先成為“文明傳承之所”,這就要求探討人類的“永恒問題”,即“共同人性”與本民族的族類特性問題。哈欽斯還主張把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兩年制擴展為四年制,通識教育的學分占全部學分的一半。但他的這種觀點和主張首先在芝加哥大學內引起激烈爭論,甚至遭到尖銳批評,直到1942年才被正式通過,從此芝加哥大學便建立了強化通識教育的本科體制。雖然后來又將四年制改為前兩年通識教育,后兩年向專業方向分流,但哈欽斯奠定了本科階段以通識教育為基礎并以經典閱讀為中心的傳統,芝加哥大學也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典范。
另一個基本文獻是1945年哈佛大學在校長科南特(James B. Conant)領導下發表的報告《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一般稱“哈佛紅皮書”),對美國和國際上許多大學都有持久的影響。在科南特看來,通識教育關系到國家高質量人才的成長,更加關系到美國的未來。與哈欽斯的理念密切聯系,科南特關于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要為美國現代社會奠定共同的文明基礎,為此就必須開設各種形式的“西方文明”課,并以西方經典的閱讀為中心,這便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最基本的內容與方式。
總的來看,現代美國流行的通識教育的顯著特點有四個:一是通識教育的宗旨,是取得對西方文明傳統和美國歷史的認同,以求奠定美國現代社會的共同文化基礎,因而通識教育的主線,便是西方文明史,或有關西方文明的各類課程。雖難免有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缺陷,但在現代高等教育中尋求文明傳統的共同體認,增強對人類和民族文明的社會責任感,是值得借鑒的。二是通識教育的教學方式,是以對西方文明經典著作廣泛而深層的閱讀為中心。這貫穿在各門課程和各種教學環節中。三是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是經過專門機構通盤考慮、反復研究和精心設計的。四是通識教育課一般都由一流學者親自講授,并以多種形式組織學生討論。
我國通識教育的資源
我國教育界將英語中的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譯成“通識教育”,包含民族傳統教育思想的成分。儒家經典《禮記·學記》,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教育文獻,其中指定的九年計劃要求“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中庸》所概括的學習程序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由此可見,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內容上首先要求“博學”,講究“會通”或“貫通”,或稱“知類通達”。孔子也說:“吾道一以貫之。”早期儒家的教育項目稱為“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已大致包含我們今日所說的“德、智、體、美”育,或“文科”與“理科”的內容。儒家要求培養的人,是“士”“君子”以至“圣人”,應當是一種完善的人格:學與思結合,知與行合一,德、仁、勇兼備的人。當然,秦漢以后,兩千多年的文化專制主義和偏執的“獨尊儒術”,又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遠遠落后于西方。明清之際富于民主性的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大都反對文化專制,批評科舉制度,主張“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梁啟超為京師大學堂草擬的第一個辦學章程中便有“中西并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的規定,這顯然繼承了我國傳統教育思想的優秀遺產。
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于1917年任校長以后,著重吸取德國教育家洪堡的教育思想和柏林大學的辦學經驗,并且對西方各大學博采眾長,結合中國傳統教育的優點,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張與措施,把一所充滿官僚腐敗習氣的舊學堂改造成一所現代型的研究型大學。他鼓勵“順自然、展個性”,主張“德、智、體、美”育全面發展,塑造一種“健全的人格”,并且主張溝通文、理,要求理工科的學生也學些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具備人文情懷;學文科的學生也學些自然科學知識,具備科學精神。特別是他明確提出并堅決貫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這在中國現代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開一代新風。
在北京大學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都曾興起過通識教育和學術繁榮的高潮。實際上主持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工作的梅貽琦曾著《大學一解》一文,論及“通”與“專”的關系。有人認為,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大學畢業生應為一通才,也應為一專家,即通專并重。梅貽琦指出:“大學期間,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因為通識為專才之基礎,在大學本科幾年的時間內難以通專并舉、同時達到。造就專才,可另有大學研究院、高級專科學校或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去完成。關于治學中的“通”與“專”或“博”與“約”的關系,胡適曾比喻為埃及的金字塔,“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底子寬,才能上得去。endprint
曾任清華大學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務長的潘光旦認為中國傳統教育首先是教人做一個“人”或做一個“士”。這種“士”的教育,從理智方面說,就是“推十合一”。他指出:“泛濫無歸的人患在推十之后,不能合一;執一不化的人,患在未嘗推十,早就合一。”潘光旦可能是我國教育界中最早翻譯和使用“通識教育”的人。他融會中西,既吸收和借鑒了中西教育思想,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與其他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通才,而不是專才或“匠人”,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通識”的內容應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三大方面。這就要求我們將自然、社會與人視為一體,融會貫通地思考人生與世界的各種問題,從而為更高的專深研究奠定基礎。參照西方和美國的大學制度,潘光旦明確主張大學不要過早劃分專業,至少延緩到本科第三學年,第一學年可以考慮設置“自然科學通論”“社會科學通論”“文化概論”“宇宙與人生”之類的通識課程。
綜上所述,“通識教育”的名稱和實施,雖然源于西方,但并不是什么單純的“舶來品”,我國從古代到現代也有著相近的豐富資源有待我們深入發掘。總的來看,“通識教育”是一種自由、通達的教育,一種重視文明、人才傳統的教育,一種拓寬基礎、培養高端人才的教育。如果說,美國現代大學的 “通識教育”更加側重于西方文明史、文明傳統的話,我國歷來強調的通識教育,更側重于“博學”“會通”“合十推一”,培養“健全人格”與通才的一面。
我國當前實施的“通識教育”,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現代教育的經驗與長處,但不能是美國現代“通識教育”的單純“移植”或照搬,應當結合我國的傳統與現實,走出一條富于時代和民族特色、培養高質量人才的路子。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曾照搬蘇聯模式,強調“專業對口”和“專才”的培養,把專業和教研室劃分得很細、很窄,設立屏障,互不介入,造成“隔行如隔山”的“隧道效果”。這使學生、教師的知識和視野備受限制,缺乏深造的基礎和條件。這種模式對我國教育的影響頗深,至今并未完全清理。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狀況有所改變,但隨后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實用主義、急功近利的勢頭又驟然興起。應用型、時尚型、贏利型的學科與專業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熱門”,大大削弱了基礎學科、基本理論與基本訓練的地位,人文基礎學科(文、史、哲)和人文精神呈現衰退趨勢。這兩種傾向,正是十年來我國大學很少出現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強調博學和知類通達、強調文明傳統和人文精神的通識教育,既是補偏救弊、培養杰出人才、實現民族振興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我國教育領域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的自覺與共識。
當前我國通識教育的問題與建議
十多年來,我國大學大致設定前一年半側重通識教育,后兩年半為寬口徑的專業教育,并允許學生在前一年半內重新選擇專業。門類與科目多樣的通選課可供學生選修,一般很受歡迎,也比較有利于學生個性與興趣的發展。由此可見,通識教育是有成績的,但仍存在若干重要問題,迫切需要加強研究、得到及時解決。
通識教育是國際現代教育的一大潮流,也符合培養現代化、高質量人才的需要。但當前通識教育僅限于采取劃分學習年限、設置通選課程(包括設置幾類科目、分別規定學分等)、在試點學院安排導師制、可改變專業、學習年限有一定彈性等。但這些都還限于表面,對于通識教育的意義與要求并未充分研究和討論,缺乏自覺的共識,存在某些盲目、誤解和阻力。實施現代通識教育,既要汲取西方的先進經驗,又要繼承我國的優秀遺產,融合中西,走出自己的路子。因此,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發掘我國從古代到現代的教育資源,而這方面的工作尚未認真開展,應當引起我們重視。
通選課究竟應該如何合理設置?怎樣達到通識教育的要求?這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通盤考慮、合理安排的問題。當前的通選課,確實有一批水平較高、反映教師學術專長、受到學生歡迎的課程。學科比較齊全的綜合性大學,每年能開出一大批各類名目的課程,供全校個性各異、興趣多樣的學生選修,可謂是大學里的一種進步。但當前的通選課,經常呈現自發狀態,缺乏統籌規劃和嚴格的評審制度。課程雖然較多,但也顯得比較雜亂,像是一個“大拼盤”,而且有些教師與學生對通選課并不重視。有的教師由于課時短,授課內容往往前緊后松,很少有閱讀經典和組織討論的時間;有的學生把通選課視為“附屬課”“輔助課”,對內容貧乏的課稱為“水課”,但卻樂于輕松取得學分。若年年如此重復,不作規劃與改進,便難以達到通識教育的應有效果。
對于通識教育的基本含義與要求是什么,學界存在不同觀點。而筆者個人理解其主要包含兩方面:一是拓寬基礎、溝通文理,為專業深造創造條件;二是融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陶冶,提升學生的個人氣質。通選課的設置和建設,可考慮沿著這兩個方面進行,而為了達到這兩方面的要求,主要依靠對中西文明史上各種經典讀本的深層閱讀與探討來完成,而不是依靠通選課程的設置數量來實現。這是通識教育最薄弱的環節,迫切需要有關部門從長計議,廣大師生狠下功夫。
合理的通識教育,絕不是削弱或排斥專業教育,恰恰是要在更高層次上推進專業教育,培養專門人才,培養有國際影響的科學家、思想家、發明家……中學是基礎教育階段,筆者個人理解,中學的教育就是一種初級階段的通識教育,它應當與大學的通識教育相銜接。因此,筆者不主張在中學實行文理分科。在課程設置上,如何正確而恰當地處理通選課與專業課的關系,通選課與文化素質課、傳統政治課的關系,都需要作適當調整,盡量避免重復、節省時間、提高質量、注重效果,盡力調動學生的興趣和主動性。山東大學曾著力建設兩門課程:一是“中國民族精神”;二是“中國文獻經典”。由于其富于開創性,質量高、收效大,深受學生歡迎。這種課程是適合通識教育要求的,而且可以與文化素質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熔于一爐,事半功倍,豈不是很好么?當然,西方的文明史與經典閱讀,也應當著重安排。
以上一系列問題,迫切需要一個統一的中心機構,組織一批有熱情、有水平的學者,定期研究、討論,進行總體的規劃與設置,只有這樣才能使通識教育名副其實地向前推進。有的國外大學早已成立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并定期出版刊物,這是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
[責任編輯:卜 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