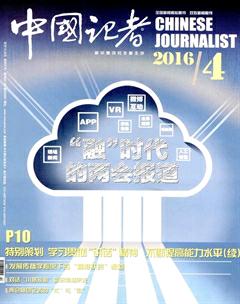如何建設媒介扶貧信息傳播的新話語
李紅艷
內容提要 如何將國家戰略與大眾媒介傳播結合起來。一直是政府、企業和大眾媒介研究者和從業者關注的問題。針對中央提出的精準扶貧戰略,作者從發展傳播學的角度。認為媒體應從四個角度建設扶貧報道的新話語。以共享發展理念為核心,展開媒介扶貧信息報道的時空化,發展和建設新的扶貧文化,培育專業的媒介信息傳播者。
關鍵詞 精準扶貧 大眾媒介 扶貧報道
中國的精準扶貧戰略如何通過大眾媒介獲得更好的助力呢?筆者認為,最主要的著力點是大眾媒介應該建沒扶貧報道的新話語,具體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以共享發展為基本理念,在精準扶貧與媒介報道的精準性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表達關系
作為種新的扶貧話語,“精準挾貧”這四個字本身對扶貧的內涵和外延做了明確規定。關鍵在于媒介報道如何在精準上做文章,將媒介報道的精準性與精準扶貧的話語“對照”起來。這里的“對照”并非是照搬的意思,媒介的屬性決定其在對某一問題報道上尋找“熱點”的必然性,但是如何保持“熱點”的持續性,需要媒介對“熱點”進行一定的“經營”或者“營銷”。
換言之,精準扶貧背后的共享發展理念是建設新的媒介扶貧報道話題的起點。共享發展這一理念因此也是精準扶貧與媒介報道的精準性之間建立有效表達關系的國家與社會背景。在這種背景中。媒介報道的“熱點”可以拓展到政治文化經濟及社會變遷與流動等議題報道上。其中也應該有對城鄉地理空間差異上的政治和文化表達、對城鄉社會之間以扶貧為中介而展開的多元化問題的討論,更應該集中在共享意義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討論,從而在多層次的媒介報道中,將精準的扶貧政策落腳到廣泛的社會背景中。在建設新的扶貧話語報道模式的同時,大大拓寬對政策本身的傳播力度。
從發展傳播學角度來說,共享發展是一種行動視角下的參與式發展理念,通過媒介滲透及使用和信息技術擴散來促進國家與社會的現代化、促進人的現代化。精準扶貧則是將這種參與式的理念投射到國家戰略上,通過規劃與行動的模式實現共享意義下的多贏。媒介不僅成為報道精準扶貧的平臺,也是參與者共同構建精準扶貧話語的平臺。
二、發現和重構大眾媒介與扶貧政策發布之間的時間關系
大眾媒介在以往關于扶貧的報道中,與政策發布之間的時間關系有序列不清晰的現象。有些報道,過了幾年再看,改改時間都可以再用了,而重構這個新的時間關系,需要從扶貧政策的歷史、政治社會背景、經濟文化背景以及國際環境、乃至于技術變遷等因素等方面著手。比如精準扶貧的概念是針對什么情況提出來的?又有哪些發展?或許這些問題,在大眾媒體報道中部已經有所涉及,但是報道的效力并沒有呈現出來
例如,在2015年11月27日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要沒定時間表,實現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癥。要留出緩沖期,在一定時間內實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實行嚴格評估,按照摘帽標準驗收,要實行逐戶銷號,做到脫貧到人,脫沒脫貧要同群眾—起算賬,要群眾認賬。”扶貧政策沒定時間表,相應的媒介報道也要沒定時間表。這種時間表的設立,需要媒介組織從建設新的扶貧話語開始。
筆者從事農民工與農民調查,曾經對媒介關于農民工稱謂與農民工政策之間做出縱向比較,發現政策頒布與媒介報道之間會出現滯后與錯位的現象。出現這種現象,往往是在政策頒布與媒介報道的時間關系處理上沒有做系統安排,因此媒介報道中出現多義性的政策報道,這一點很容易影響媒介報道的效力。
三、建設新的媒介扶貧信息傳播話語與建設一種新的扶貧文化息息相關
如何尋找和重新厘定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一種新的話語表達,一定意義上都是尋找和重新厘定文化價值體系的嘗試。扶貧話語也是如此。在每一次體制革新和社會變遷中。政治文化、社會文化和大眾文化都會發生—些細微或者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便是話語表達。就國家層面而言。扶貧不僅僅是一種共享發展理念下的戰略訴求,更是一種嘗試建設新文化的努力。
作為文化的載體,社會化過程和媒介化過程也是塑造和尋找新文化體系的過程。對于當代中國媒介組織和媒介從業人員而言。通過對精準扶貧的報道,也是在媒介化時代建設新的扶貧文化的契機。
新的扶貧文化應該包含這樣一種含義。即扶貧是平等理念下消除社會階層差異的—種文化嘗試。而不應該是主導文化向非主流文化傳輸的過程,也不應該是以社會地位相對高的階層向社會地位相對低的階層自上而下進行文化傳輸的過程。
筆者曾經做過幾年的農民培訓,在培訓中發現,一些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相對的農民群體,擁有很強的發現和創造文化的能力,農村的一些曲藝形式,在他們的手中被賦予很多日常化的內容。比如舞蹈、相聲、歌謠、散文等。此外還有一些鄉村文化的表達。他們主動記載了鄉村社會中一些文化傳統和習俗,這些都是媒介建設扶貧話語的重要資源。
四、建設新的媒介扶貧信息傳播話語需要培養“專職的扶貧報道”從業者
筆者做了十余年農民工與媒介關系的調研工作,曾經希望訪談一些專門從事三農報道的記者,發現人數寥寥,而對僅有的一些記者的采訪中。他們對農民工的看法基本來自于個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和媒介報道,專業性和職業性都比較缺乏。有的記者告訴筆者。這是媒介的組織結構決定的,媒介也不可能設立專門的三農部門。因此,就媒介自身的現狀而言,建設新的媒介扶貧信息的話語,也需要從媒介從業人員的職業化與專業化上入手。
扶貧報道與國家發展戰略結合。平面化的信息報道方式遠遠不夠,需要培育和發掘專業的“扶貧記者”。這些“扶貧記者”在滿足基本的專業素養的同時,要從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趨勢有基本的認知,對扶貧政策的前因后果,以及其與國家與社會發展戰略之間的關系有清晰的了解。對基層社會有長期的觀察和了解,在理論和實踐上有專業知識和職業素養。
假設媒介從業人員能夠在專業挾貧報道上更貼近現實、融入日常生活,同時又具備一定的專業矢口識和高度,滿足不同受眾群體和各種組織的信息訴求。那么媒介便成為彌合不同階層之間知識溝的一種有效工具。(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鄉村傳播研究所所長。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