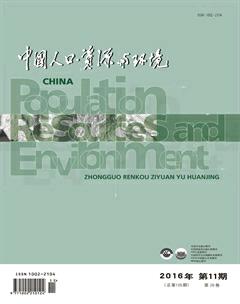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補(bǔ)償問(wèn)題研究
劉靈輝+鄭耀群
摘要 隨著未來(lái)家庭農(nóng)場(chǎng)數(shù)量的逐漸增加與經(jīng)營(yíng)土地面積的不斷擴(kuò)大,與快速城鎮(zhèn)化相伴隨的土地征收區(qū)域不可避免會(huì)與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范圍相交叉或重疊。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通過(guò)整合作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分得的承包地和市場(chǎng)化交易獲得的承包地實(shí)現(xiàn)土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因此,在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被征收時(shí),應(yīng)確保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獲得科學(xué)合理的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并妥善處理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與擁有不同類型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眾多相關(guān)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guān)系。本文采用文獻(xiàn)資料法和理論分析法,區(qū)分點(diǎn)狀征地、線狀征地和面狀征地三種不同情況,分析了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的后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影響,在土地承包關(guān)系“長(zhǎng)久不變”的政策框架下,深入剖析了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涉及的農(nóng)地權(quán)利類型。然后,構(gòu)建起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理論模型,以及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政府、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農(nóng)民等權(quán)利主體之間的收益分配理論模型。具體而言,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根據(jù)自有土地、通過(guò)土地流轉(zhuǎn)獲得的土地、通過(guò)土地退出獲得的土地所占的比重以及不同類型土地權(quán)利所對(duì)應(yīng)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分得相應(yīng)的征地補(bǔ)償收益;政府通過(guò)稅收參與征地補(bǔ)償收益分配;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憑借土地所有者身份依法分得相應(yīng)比例的補(bǔ)償收益;農(nóng)民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為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價(jià)值扣除其讓渡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的農(nóng)地權(quán)利價(jià)值后的剩余部分。最后,本文從四個(gè)方面提出了相應(yīng)的對(duì)策和建議:①做好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規(guī)劃;②提高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并將間接損失納入補(bǔ)償范圍;③建立家庭農(nóng)場(chǎng)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征收補(bǔ)償收益分配機(jī)制;④保障抵押權(quán)人(金融機(jī)構(gòu))對(duì)征地補(bǔ)償享有優(yōu)先受償權(quán)。
關(guān)鍵詞 土地制度;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收益分配
中圖分類號(hào) F2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2-2104(2016)11-007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10
“家庭農(nóng)場(chǎng)”是起源于歐美的舶來(lái)名詞,當(dāng)今世界,所有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農(nóng)業(yè),盡管各國(guó)的國(guó)情不同,采取的都是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經(jīng)營(yíng)方式。家庭農(nóng)場(chǎng)既把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要素融入到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農(nóng)戶家庭經(jīng)營(yíng)中,又避免了雇工農(nóng)場(chǎng)大規(guī)模流轉(zhuǎn)土地帶來(lái)的解放勞動(dòng)力過(guò)多、企業(yè)運(yùn)行風(fēng)險(xiǎn)累及農(nóng)民、農(nóng)作精細(xì)化程度不夠等問(wèn)題,是農(nóng)業(yè)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最佳路徑選擇[1],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最好組織形式[2]。2013年中央一號(hào)文件提出,鼓勵(lì)和支持承包土地向?qū)I(yè)大戶、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民合作社流轉(zhuǎn)。政府將家庭農(nóng)場(chǎng)寫(xiě)入國(guó)家促農(nóng)發(fā)展的最高文件,不僅表明了它已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政治生命力[3],而且也表明現(xiàn)階段我國(guó)發(fā)展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時(shí)機(jī)已經(jīng)成熟、條件初步具備[4]。目前,全國(guó)各地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方興未艾。根據(jù)2012年農(nóng)業(yè)部首次家庭農(nóng)場(chǎng)統(tǒng)計(jì)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全國(guó)30個(gè)省、區(qū)、市(不含西藏)共有符合統(tǒng)計(jì)標(biāo)準(zhǔn)的家庭農(nóng)場(chǎng)87.70萬(wàn)個(gè),平均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200.20畝,經(jīng)營(yíng)耕地面積達(dá)到1.76億畝,占全國(guó)承包耕地面積的13.40%。發(fā)展家庭農(nóng)場(chǎng)有賴于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zhǎng)下大量農(nóng)民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所帶動(dòng)的土地流轉(zhuǎn),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高速增長(zhǎng),主要依靠高速的工業(yè)化和快速的城市化兩個(gè)引擎拉動(dòng),土地更是成為這兩個(gè)引擎的發(fā)動(dòng)機(jī)。以征地制度為核心的獨(dú)特土地制度,是支撐這一經(jīng)濟(jì)高成長(zhǎng)的重要制度[5]。根據(jù)《中國(guó)城市建設(shè)統(tǒng)計(jì)年鑒》顯示,2001—2014年,全國(guó)累計(jì)征收土地面積為0.353 8億畝,其中,耕地面積0.157 3億畝,占全國(guó)承包耕地面積的1.19%。有關(guān)研究表明,我國(guó)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個(gè)百分點(diǎn),城市建成區(qū)面積將擴(kuò)大1 056 km2,耕地減少615萬(wàn)畝[6]。根據(jù)中國(guó)國(guó)務(wù)院公布的《國(guó)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和中國(guó)社科院發(fā)布的《城市藍(lán)皮書(shū):中國(guó)城市發(fā)展報(bào)告No.8》,2020年、2030年中國(guó)城鎮(zhèn)化率將分別達(dá)到60%和70%,意味著屆時(shí)耕地將分別減少0.321 6億畝和0.936 6億畝。隨著家庭農(nóng)場(chǎng)數(shù)量的逐漸增加與經(jīng)營(yíng)耕地面積的不斷擴(kuò)大,與快速城鎮(zhèn)化相伴隨的土地征收區(qū)域不可避免會(huì)和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范圍發(fā)生交叉或重疊。土地征收會(huì)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后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帶來(lái)或多或少的影響,甚至造成其消滅。另外,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成片土地是通過(guò)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作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分得的承包地和市場(chǎng)交易獲得的大量分散零碎承包地進(jìn)行歸并和整合實(shí)現(xiàn)的,具有涉及權(quán)利主體眾多、權(quán)利類型多樣的特征,故而,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被征收時(shí)將面臨著復(fù)雜的補(bǔ)償收益分配問(wèn)題。因此,研究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補(bǔ)償問(wèn)題有利于消除眾多權(quán)利主體之間的收益分配矛盾和沖突、打消有志于投身家庭農(nóng)場(chǎng)事業(yè)農(nóng)民的疑慮與擔(dān)心,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shí)意義。
1 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的影響
發(fā)展家庭農(nóng)場(chǎng)首先需要解決“地從哪里來(lái)”的問(wèn)題[7],家庭農(nóng)場(chǎng)所需的土地應(yīng)滿足三個(gè)基本條件:集中成片、規(guī)模適度、期限穩(wěn)定。因此,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在集中適度規(guī)模土地過(guò)程中面臨著大量的信息收集、眾多回合的談判協(xié)商、高額的資本投入等。然而,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歷經(jīng)千辛萬(wàn)苦集中起來(lái)的土地在生產(chǎn)運(yùn)營(yíng)過(guò)程中同樣存在著喪失的風(fēng)險(xiǎn),例如,因自然災(zāi)害土地毀損而喪失、因農(nóng)民中途違約索回土地而喪失、因國(guó)家強(qiáng)制性的土地征收而喪失等,其中,土地征收是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依法必須接受、可以獲得經(jīng)濟(jì)補(bǔ)償且未來(lái)發(fā)生頻率相對(duì)較高的一種土地喪失類型。根據(jù)征收地塊的形狀特征,土地征收可分為點(diǎn)狀征地、線狀征地和面狀征地,不同征地形狀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后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影響存在著較大差異。
在點(diǎn)狀征地情況下,征地項(xiàng)目主要包括移動(dòng)通訊基站、高壓電線桿、風(fēng)力發(fā)電桿等,具有單個(gè)點(diǎn)位征地面積小、波及農(nóng)戶少等特點(diǎn)。點(diǎn)狀征地看似在家庭農(nóng)場(chǎng)成片集中的土地上設(shè)置了一個(gè)小小的障礙物,一般而言,對(duì)家庭 農(nóng)場(chǎng)后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造成的影響甚微。但是,如果點(diǎn)狀征地的點(diǎn)位密度越大、分布越凌亂(如圖1-b、圖1-c),會(huì)使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土地變得愈來(lái)愈不適宜于機(jī)械化耕作,并導(dǎo)致其后期生產(chǎn)運(yùn)營(yíng)成本的增加。
在線狀征地情況下,征地項(xiàng)目主要包括公路、鐵路、輸水工程等,征收地塊具有均勻狹長(zhǎng)、沿線波及農(nóng)戶較多、單個(gè)農(nóng)戶被征地面積較少等特點(diǎn)。線狀征地像在家庭農(nóng)場(chǎng)成片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上畫(huà)了一條“分割線”,將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分割成兩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組成部分。如果線狀征地越靠近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一側(cè)邊緣(圖2-a),則家庭農(nóng)場(chǎng)另一側(cè)土地面積較大的組成部分可以繼續(xù)維持規(guī)模化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不變;如果線狀征地越靠近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中心位置(圖2-b、圖2-c),則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被均分程度會(huì)越高。由于公路、鐵路、輸水工程等項(xiàng)目建設(shè)往往對(duì)周邊環(huán)境帶來(lái)的負(fù)外部性影響較大,這會(huì)導(dǎo)致家庭農(nóng)場(chǎng)被分割的兩個(gè)組成部分繼續(xù)作為一個(gè)整體進(jìn)行生產(chǎn)運(yùn)營(yíng)的可能性基本不復(fù)存在,然而,相對(duì)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現(xiàn)有的資金數(shù)量、機(jī)械設(shè)備臺(tái)數(shù)、勞動(dòng)力人數(shù)等生產(chǎn)要素而言,被分割的單一組成部分所代表的土地規(guī)模又缺乏“適度性”。因此,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不得不放棄一個(gè)組成部分的土地,通過(guò)“兼并”周邊農(nóng)戶土地等手段擴(kuò)大另一組成部分的土地規(guī)模,以求再次達(dá)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的狀態(tài)。
在面狀征地情況下,征地項(xiàng)目主要包括工業(yè)廠房、城市住宅、綜合商場(chǎng)、水利水電工程等,征收地塊具有不同項(xiàng)目面積差異大、波及農(nóng)戶范圍廣、單個(gè)農(nóng)戶喪失土地?cái)?shù)量多等特點(diǎn)。如果面狀征地位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邊緣且面積較小(圖3-a),則相當(dāng)于在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角落“摳出”了一小塊,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影響僅僅表現(xiàn)在土地面積的細(xì)微變化上。如果面狀征地越靠近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中間且面積較大(圖3-b),則家庭農(nóng)場(chǎng)剩余地塊之形狀會(huì)淪為不規(guī)則的環(huán)狀,如果再將被征地塊用于工業(yè)、居住、商業(yè)等給周邊環(huán)境帶來(lái)的負(fù)外部性影響納入考慮范疇的話,則家庭農(nóng)場(chǎng)剩余土地適宜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程度將大幅降低。如果面狀征地的面積足夠大,征收地塊會(huì)局部超過(guò)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規(guī)模邊界,甚至將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全部覆蓋(圖3-c),如興修水利水電工程。此時(shí),家庭農(nóng)場(chǎng)被完全“吞并”,即使有部分剩余土地也淪為被征地塊的“邊角料”,家庭農(nóng)場(chǎng)會(huì)因土地征收而消滅。
2 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涉及的農(nóng)地權(quán)利類型
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作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享有通過(guò)土地發(fā)包獲得承包地(下稱“自有土地”)的權(quán)利。然而,自有土地往往呈現(xiàn)出地塊零碎分散、單個(gè)地塊規(guī)模“超小”的特征,因此,家庭農(nóng)場(chǎng)實(shí)現(xiàn)土地適度規(guī)模化集中有賴于農(nóng)民城鎮(zhèn)化轉(zhuǎn)移所帶動(dòng)的土地流轉(zhuǎn)和土地退出等農(nóng)地權(quán)利市場(chǎng)化交易行為。現(xiàn)階段,政府通過(guò)政策引導(dǎo)和激勵(lì)農(nóng)民流轉(zhuǎn)或退出土地,農(nóng)民通過(guò)市場(chǎng)渠道自愿讓渡農(nóng)地權(quán)利以賺取理想的經(jīng)濟(jì)收益,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以農(nóng)地轉(zhuǎn)入方身份介入市場(chǎng)接收土地對(duì)零散地塊進(jìn)行整合和歸并,這是目前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適度規(guī)模集中的重要實(shí)現(xiàn)途徑。一般而言,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成片土地是歸屬于眾多權(quán)利主體的分散零碎地塊拼接整合的結(jié)果,是通過(guò)農(nóng)地權(quán)利市場(chǎng)化交易形成的一種契約性合并。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內(nèi)部構(gòu)成具有多元性,根據(jù)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歸屬主體不同分為自有土地和轉(zhuǎn)入土地;轉(zhuǎn)入土地根據(jù)農(nóng)民處置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類型不同,分為流轉(zhuǎn)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的土地和退出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的土地;根據(jù)農(nóng)民選擇的流轉(zhuǎn)方式不同,流轉(zhuǎn)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的土地又可以分為出租、入股、轉(zhuǎn)包、互換、轉(zhuǎn)讓等。
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擁有土地所有權(quán),農(nóng)民擁有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隨著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物權(quán)屬性的依法確立、土地承包關(guān)系“長(zhǎng)久不變”政策的實(shí)施以及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流轉(zhuǎn)權(quán)、退出權(quán)、抵押與擔(dān)保權(quán)、 發(fā)展權(quán)、繼承權(quán)等內(nèi)在權(quán)能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與認(rèn)可,農(nóng)村土地實(shí)質(zhì)上形成了由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和農(nóng)民共享產(chǎn)權(quán)的格局。國(guó)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duì)土地實(shí)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bǔ)償。土地征收在直接導(dǎo)致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土地所有權(quán)向國(guó)家不可逆性轉(zhuǎn)移的同時(shí),征收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消滅土地上現(xiàn)存的權(quán)利,取得了完全沒(méi)有負(fù)擔(dān)的土地所有權(quán)[8]。目前理論界關(guān)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問(wèn)題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兩類問(wèn)題進(jìn)行:①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土地所有權(quán)和農(nóng)民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征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問(wèn)題;②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和農(nóng)民等權(quán)利主體圍繞土地征收產(chǎn)生的收益分配問(wèn)題。然而,對(duì)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等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通過(guò)與眾多農(nóng)戶進(jìn)行農(nóng)地權(quán)利交易集中起來(lái)的規(guī)模化土地被部分或全部納入征地范圍時(shí),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應(yīng)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問(wèn)題以及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與其他眾多農(nóng)地權(quán)利主體之間的征地補(bǔ)償收益分配問(wèn)題鮮有學(xué)者進(jìn)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
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實(shí)質(zhì)上是政府通過(guò)法律途徑對(duì)土地進(jìn)行的一種行政性壟斷定價(jià),Alchian[9]指出,所有定價(jià)問(wèn)題都是產(chǎn)權(quán)問(wèn)題。因此,研究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首先應(yīng)明確其內(nèi)部復(fù)雜的權(quán)利構(gòu)成(見(jiàn)表1)。對(duì)于自有土地,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擁有和普通農(nóng)民一樣的物權(quán)性質(zhì)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對(duì)于通過(guò)出租、轉(zhuǎn)包、入股、互換等方式獲得的土地,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僅擁有債權(quán)性質(zhì)的土地使用權(quán),需按年度支付給轉(zhuǎn)地農(nóng)民一定數(shù)額的流轉(zhuǎn)費(fèi),土地使用期限為合同載明的流轉(zhuǎn)年限,合同期限屆滿后土地使用權(quán)自動(dòng)重歸原土地承包者所有。同時(shí),農(nóng)地蘊(yùn)含的向非農(nóng)用途轉(zhuǎn)換之發(fā)展權(quán)并不隨土地流轉(zhuǎn)讓渡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所有。土地退出與土地流轉(zhuǎn)所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轉(zhuǎn)移結(jié)果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土地退出屬于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一次性完全讓渡,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一次性支付給農(nóng)民數(shù)額較大的退地補(bǔ)償收益[10],同時(shí)擁有退地農(nóng)民原承包地的一切權(quán)利,包括農(nóng)地的發(fā)展權(quán),相當(dāng)于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一次性“買賣”行為。
3 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征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及收益分配
3.1 土地所有權(quán)和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
目前,政府憑借征地權(quán)控制建設(shè)用地“增量”來(lái)源關(guān)口進(jìn)而壟斷土地一級(jí)市場(chǎng),依靠“低價(jià)征地、高價(jià)出讓”形成的價(jià)格剪刀差為政府攫取源源不斷的財(cái)政收入。由于這種征地補(bǔ)償方式缺乏對(duì)等的博弈議價(jià)機(jī)制,造成征地補(bǔ)償收益分配格局嚴(yán)重扭曲,農(nóng)民只能從土地用途轉(zhuǎn)換帶來(lái)的高額增值收益中分配到很小一部分。因此,現(xiàn)行征地補(bǔ)償制度難以為繼、亟待改革。未來(lái),應(yīng)充分發(fā)揮市場(chǎng)機(jī)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即通過(guò)對(duì)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放棄國(guó)家對(duì)城市用地的高度壟斷,使土地的供求關(guān)系主要由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11]。農(nóng)民能夠和地方政府一樣成為土地的供給者,土地交易價(jià)格由政府定價(jià)轉(zhuǎn)變?yōu)檗r(nóng)民與用地者之間的協(xié)商議價(jià)。此時(shí),每畝土地的所有權(quán)議定價(jià)格(M1)主要包括三部分:農(nóng)地農(nóng)用狀態(tài)下的權(quán)利價(jià)值(R1)、農(nóng)地轉(zhuǎn)用下的發(fā)展權(quán)價(jià)值(R2)和農(nóng)用轉(zhuǎn)用的各項(xiàng)成本投入(C),即M1=R1+R2-C[12]。其中,R1是每畝農(nóng)地未來(lái)年限純收益的資本化,即未來(lái)每畝農(nóng)地每年純收益的折現(xiàn)值之和;R2是每畝農(nóng)地轉(zhuǎn)為最佳狀態(tài)下建設(shè)用地后的未來(lái)每年純收益的資本化,即未來(lái)每畝農(nóng)地轉(zhuǎn)為最佳狀態(tài)下建設(shè)用地后每年純收益扣除機(jī)會(huì)成本(農(nóng)地農(nóng)用年純收益)后余額的折現(xiàn)值之和;C包括土地取得費(fèi)、土地開(kāi)發(fā)費(fèi)和稅費(fèi)等。
3.2 不同主體間圍繞征地補(bǔ)償?shù)氖找娣峙?/p>
(1)政府和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可以分配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我國(guó)現(xiàn)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產(chǎn)生有其特殊的時(shí)代背景,它在財(cái)力有限的情況下能有效解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財(cái)力不足的問(wèn)題,保證國(guó)家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需的土地[12]。目前,在土地征收中,用地單位所要支付的土地出讓金已經(jīng)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財(cái)政來(lái)源[13]。如果政府放棄土地一級(jí)供應(yīng)市場(chǎng)壟斷地位將意味著土地財(cái)政的終結(jié),如果沒(méi)有相應(yīng)的替代機(jī)制將導(dǎo)致政府債務(wù)償還和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資金來(lái)源面臨困境。為避免政府利益嚴(yán)重受損進(jìn)而影響其制度變革的積極性甚至施加阻力,可以通過(guò)適當(dāng)?shù)亩愂照甙才攀拐畢⑴c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來(lái),“土地財(cái)政”向“稅收財(cái)政”的轉(zhuǎn)變有利于地方政府改變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思路,把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源泉從以地生財(cái)?shù)墓秩χ欣鰜?lái),轉(zhuǎn)變到通過(guò)依靠科技進(jìn)步、科學(xué)管理等促進(jìn)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可持續(xù)軌道上來(lái)。
設(shè)政府的稅收比例為δ1,即政府通過(guò)稅收可以分配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為δ1×(R1+R2-C)。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對(duì)農(nóng)村土地的權(quán)利主要體現(xiàn)在土地發(fā)包、土地利用監(jiān)督等宏觀管理職能方面,同時(shí),在農(nóng)民選擇出租、入股、轉(zhuǎn)包等保留物權(quán)權(quán)利的市場(chǎng)化土地處置方式時(shí),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經(jīng)濟(jì)利益依法不能有所體現(xiàn)。然而,土地征收屬于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一次性完全讓渡,且直接導(dǎo)致農(nóng)地所有權(quán)由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所有不可逆地轉(zhuǎn)變?yōu)閲?guó)家所有,因此,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憑借土地所有者身份,按照法律政策規(guī)定獲得相應(yīng)比例的土地交易收益分配額。假設(shè)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收益分配比例為δ2,即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每畝農(nóng)地可以分配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為δ2×(R1+R2-C)。
(2)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可以分配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土地所有權(quán)的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在扣除政府稅收和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依法分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后,即為每畝承包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分配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M2,則M2=(1-δ1-δ2)×(R1+R2-C)。土地承包關(guān)系“長(zhǎng)久不變”即農(nóng)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期無(wú)限延長(zhǎng)、真正賦予農(nóng)民無(wú)限期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因此,M2代表的是無(wú)限年期下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價(jià)值。假設(shè)家庭農(nóng)場(chǎng)被征土地總面積為S畝,其中,自有土地面積為Z畝,通過(guò)土地流轉(zhuǎn)獲得的面積為L(zhǎng)畝,通過(guò)土地退出獲得的面積為T(mén)畝。由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對(duì)流轉(zhuǎn)獲得的土地不享有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因此,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對(duì)這類土地僅能分配獲得剩余合同使用期限下農(nóng)地農(nóng)用狀態(tài)下的權(quán)利價(jià)值。設(shè)N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與農(nóng)民在合同中約定的土地流轉(zhuǎn)年限、n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通過(guò)流轉(zhuǎn)獲得土地已使用的年限、r為折現(xiàn)率。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在征地補(bǔ)償時(shí)可以獲得的收益額為M3,則:
(3)與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有農(nóng)地權(quán)利交易關(guān)系的農(nóng)民可以分配獲得的征地補(bǔ)償收益。農(nóng)民選擇不同的農(nóng)地權(quán)利交易方式會(huì)產(chǎn)生差異化的權(quán)利轉(zhuǎn)移結(jié)果,進(jìn)而會(huì)在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與農(nóng)民之間形成不同的征地補(bǔ)償收益分配格局。①在農(nóng)民選擇出租、入股、轉(zhuǎn)包、互換等流轉(zhuǎn)方式時(shí),轉(zhuǎn)地農(nóng)民僅僅是將合同約定期限(N年)內(nèi)農(nóng)地農(nóng)用狀態(tài)下的承包地轉(zhuǎn)歸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使用,轉(zhuǎn)地農(nóng)民仍享有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和合同期限屆滿后的農(nóng)地使用權(quán)。因此,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M2)扣除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合同期限(N年)農(nóng)地農(nóng)用狀態(tài)下的權(quán)利價(jià)值,即為轉(zhuǎn)地農(nóng)民每畝承包地被征收時(shí)可以分配獲得的補(bǔ)償收益M4,則M4=(1-δ1-δ2)×(R1+R2-C)-R1×1-1(1+r)N。②在農(nóng)民選擇土地退出時(shí),退地農(nóng)民將農(nóng)地權(quán)利徹底讓渡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并獲得一筆數(shù)額較大的退地補(bǔ)償收益,相當(dāng)于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一次性買斷。此時(shí),退地農(nóng)民已與原承包土地之間無(wú)任何權(quán)利歸屬關(guān)系,因此,無(wú)權(quán)參與已退出農(nóng)地的征地補(bǔ)償收益分配。但是,如果退地農(nóng)民仍屬于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分得的補(bǔ)償收益S×δ2×(R1+R2-C)在征地范圍涉及的全體農(nóng)民內(nèi)再分配時(shí),退地農(nóng)民可以憑借“成員權(quán)”分得相應(yīng)數(shù)額的貨幣收益。
4 對(duì)策與建議
4.1 做好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規(guī)劃與相關(guān)規(guī)劃的銜接,降低征地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后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影響
各地結(jié)合實(shí)際編制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規(guī)劃,確定本區(qū)域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短期、中期和長(zhǎng)期發(fā)展目標(biāo)。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規(guī)劃不僅應(yīng)明確未來(lái)本地區(qū)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培育戶數(shù)、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面積、發(fā)展模式、特色亮點(diǎn)等,而且應(yīng)根據(jù)新農(nóng)村建設(shè)規(guī)劃和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引導(dǎo)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發(fā)展區(qū)域。同時(shí),使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規(guī)劃與城鎮(zhèn)規(guī)劃、土地利用規(guī)劃、環(huán)境保護(hù)計(jì)劃、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布局規(guī)劃相協(xié)調(diào),合理確定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適宜發(fā)展區(qū)、限制發(fā)展區(qū)、禁止發(fā)展區(qū),盡可能使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范圍位于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的規(guī)模邊界和擴(kuò)展邊界之外,盡量減少與港口碼頭、機(jī)場(chǎng)、鐵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電力、水利水電工程等重點(diǎn)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的征地范圍相重疊或相交叉。如若土地征收著實(shí)避不開(kāi)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范圍,則應(yīng)根據(jù)不同的征地類型,盡可能降低土地征收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后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造成的影響。對(duì)于點(diǎn)狀征地,應(yīng)盡量降低征地點(diǎn)位落入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范圍內(nèi)的密度;對(duì)于線狀征地,征地線路應(yīng)盡量位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邊緣;對(duì)于面狀征地,應(yīng)最大限度降低征地區(qū)域與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重疊范圍,并使重疊區(qū)域位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邊角”部位。
4.2 提高土地征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將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因征地的間接損失納入補(bǔ)償范圍
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綜合考慮農(nóng)地區(qū)位、土地等級(jí)、土地利用類型、供求關(guān)系、當(dāng)?shù)厣鐣?huì)經(jīng)濟(jì)狀況等因素,充分體現(xiàn)被征土地的市場(chǎng)價(jià)格,既要考慮土地的生產(chǎn)性收益,也要考慮土地的非生產(chǎn)性收益。同時(shí),應(yīng)將農(nóng)民納入土地發(fā)展權(quán)的權(quán)利主體范圍,讓被征地農(nóng)民充分分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帶來(lái)的土地增值收益。然而,“市場(chǎng)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僅限于合同法意義上的“一般損失”或“直接損失”,通常會(huì)忽略所有間接損失[14]。因此,土地征收不僅應(yīng)以市場(chǎng)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被征土地進(jìn)行充分補(bǔ)償,而且還應(yīng)充分考慮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因土地征收所遭受的間接損失補(bǔ)償。在中國(guó),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因土地征收遭受的間接損失至少包括如下五個(gè)方面:①家庭農(nóng)場(chǎng)因土地征收而破產(chǎn)消滅時(shí),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的離職失業(yè)損失;②家庭農(nóng)場(chǎng)因土地征收而破產(chǎn)消滅時(shí),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為土地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購(gòu)買的農(nóng)機(jī)具等折價(jià)出售而遭受損失;③與征地工程建設(shè)相伴隨的人流、車流增大,所帶來(lái)的噪聲、廢氣、水質(zhì)污染等給家庭農(nóng)場(chǎng)造成的負(fù)外部性損失;④征地工程建設(shè)造成家庭農(nóng)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的成片土地被分割、被設(shè)置障礙而造成的生產(chǎn)運(yùn)營(yíng)成本升高損失;⑤征地后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少量殘余土地不能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和利用而造成的損失。
4.3 建立家庭農(nóng)場(chǎng)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征收補(bǔ)償收益分配機(jī)制
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適度規(guī)模化集中過(guò)程中面臨著多元化的農(nóng)地權(quán)利市場(chǎng)化處置方式和多樣化的融資渠道。因此,在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被征收過(guò)程中,應(yīng)妥善處理眾多擁有不同類型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相關(guān)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guān)系。①在“土地財(cái)政”向“稅收財(cái)政”轉(zhuǎn)變過(guò)程中,應(yīng)科學(xué)確定政府以征地補(bǔ)償收益為稅基的稅率標(biāo)準(zhǔn),避免稅率過(guò)高而擠占其他農(nóng)地權(quán)利主體的收益分配額度。②應(yīng)依法確定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參與征地補(bǔ)償收益分配的比例和收益用途,避免村干部等主體的貪污、挪用和擠占。同時(shí),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提取收益的對(duì)象并非全部指向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對(duì)家庭農(nóng)場(chǎng)自有土地和通過(guò)土地退出獲得的土地,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提取收益的對(duì)象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對(duì)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通過(guò)流轉(zhuǎn)獲得的土地,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提取收益的對(duì)象為土地轉(zhuǎn)出方。③由于土地退出伴隨著發(fā)展權(quán)的轉(zhuǎn)移,因此,在有償退出之時(shí)考慮給予這種“土地發(fā)展權(quán)”補(bǔ)償[15],但是應(yīng)科學(xué)確定農(nóng)民退地價(jià)格標(biāo)準(zhǔn),既要確保農(nóng)民獲得充分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以調(diào)動(dòng)其退地積極性,又不至于讓主要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提前支付土地發(fā)展權(quán)價(jià)格而導(dǎo)致用地成本大幅攀升。④家庭農(nóng)場(chǎng)利用其經(jīng)營(yíng)的農(nóng)地進(jìn)行抵押貸款時(shí),抵押物價(jià)值不應(yīng)簡(jiǎn)單比照農(nóng)民享有的物權(quán)性質(zhì)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進(jìn)行評(píng)估確定,而應(yīng)按照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享有的物權(quán)農(nóng)地權(quán)利類型組合情況及相應(yīng)的面積綜合確定。避免家庭農(nóng)場(chǎng)獲得的貸款抵押額度偏高,金融機(jī)構(gòu)行使優(yōu)先受償權(quán)而損害其他供地農(nóng)民的利益,或造成金融機(jī)構(gòu)的不良貸款風(fēng)險(xiǎn)。
4.4 明確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地抵押權(quán)人(金融機(jī)構(gòu))的優(yōu)先受償權(quán)
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獲得成片集中且期限穩(wěn)定的土地需要支付大筆的用地成本,同時(shí),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土地整理、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機(jī)械設(shè)備購(gòu)置、生產(chǎn)資料采購(gòu)、日常管理運(yùn)營(yíng)、勞動(dòng)力雇用等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故而,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需要強(qiáng)大的財(cái)力支撐。然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風(fēng)險(xiǎn)大、保障低,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很難獲得企業(yè)和一般信貸機(jī)構(gòu)的資金支持,資金短缺是成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持續(xù)發(fā)展的掣肘。因此,創(chuàng)新家庭農(nóng)場(chǎng)貸款模式,允許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利用享有的物權(quán)農(nóng)地權(quán)利向金融機(jī)構(gòu)申請(qǐng)抵押貸款是破解其資金瓶頸的重要一環(huán)。此時(shí),金融機(jī)構(gòu)成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相應(yīng)土地份額的抵押權(quán)人。當(dāng)家庭農(nóng)場(chǎng)抵押出的土地被征收時(shí),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分配獲得的相應(yīng)征地補(bǔ)償費(fèi)在性質(zhì)上屬原抵押農(nóng)地權(quán)利的代位物,金融機(jī)構(gòu)作為抵押權(quán)人可在補(bǔ)償費(fèi)上代位行使其優(yōu)先受償權(quán)[16]。征地機(jī)關(guān)非經(jīng)金融機(jī)構(gòu)同意,不得將屬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所有的補(bǔ)償金交付與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或應(yīng)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主提存,并通知金融機(jī)構(gòu)。如果被擔(dān)保的債權(quán)已屆清償期,金融機(jī)構(gòu)可以直接向征地機(jī)關(guān)請(qǐng)求給付,未屆清償期,可以向法院請(qǐng)求將補(bǔ)償金予以保全。
(編輯:于 杰)
參考文獻(xiàn)(References)
[1]袁賽男.家庭農(nóng)場(chǎng):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進(jìn)路選擇——基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與傳統(tǒng)小農(nóng)戶、雇工制農(nóng)場(chǎng)的比較[J].長(zhǎng)白學(xué)刊,2013(4):92-97.[YUAN Sainan. Household farm is the best path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omparison of household farm, traditional peasant household and employment mode farm[J]. Changbai journal, 2013(4):92-97.]
[2]趙保海.我國(guó)農(nóng)地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問(wèn)題分析——基于農(nóng)村剩余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陷阱假說(shuō)[J].吉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36(3):20-24.[ZHAO Baohai. Analysis on the scale operation of farmland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trap[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36(3):20-24.]
[3]施國(guó)慶,伊慶山.現(xiàn)代家庭農(nóng)場(chǎng)的準(zhǔn)確認(rèn)識(shí)、實(shí)施困境及對(duì)策[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15(2):135-139.[SHI Guoqing, YI Qingsh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dern family farms[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15(2):135-139.]
[4]石言弟.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現(xiàn)實(shí)選擇[J].江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3(7):16-18.[SHI Yandi. Family farm: realistic choic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J]. Jiangsu rural economy, 2013(7):16-18.]
[5]劉守英.直面中國(guó)土地問(wèn)題[M].北京:中國(guó)發(fā)展出版社,2014:47.[LIU Shouying. Land issue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a[M].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ress,2014:47.]
[6]王筱明,吳泉源.城市化建設(shè)與土地集約利用[J].中國(guó)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01,11(S2):5-6.[WANG Xiaoming, WU Quanyua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land[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1,11(S2):5-6.]
[7]鄭風(fēng)田.中國(guó)式家庭農(nóng)場(chǎng),須精心謀劃[J].農(nóng)村工作通訊,2013(5):42.[ZHENG Fengtian. Chinese family farms need careful planning[J]. Newsletter about work in rural areas, 2013(5):42.]
[8]郭平.農(nóng)地征收制度的變革契機(jī)——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征收補(bǔ)償制度[J].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6(3):124-126.[GUO Ping. The chance for the change of the land expropriate policy[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6(3):124-126.]
[9]ALCHIAN A A.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J]. Il politico, 1965,30(4):816-829.
[10]劉靈輝.農(nóng)地自由流轉(zhuǎn)下家庭農(nóng)場(chǎng)土地適度規(guī)模化研究[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15(2):153-160.[LIU Linghui. Obstacles and breakthrough for family farms to get moderate scale of land in land free circulation[J].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15(2):153-160.]
[11]文貫中.吾民無(wú)地:城市化、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內(nèi)在邏輯[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137.[WEN Guanzhong. Our people have no l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urbanisation, land system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M].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2014:137.]
[12]劉靈輝.土地承包關(guān)系“長(zhǎng)久不變”對(duì)征地補(bǔ)償?shù)挠绊懪c制度改革[J].中州學(xué)刊,2015(7):37-42.[ LIU Linghui. System reform and impact of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aused by permanent stability of l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5(7):37-42.]
[13]張衛(wèi)東,譚家強(qiáng).農(nóng)村房屋征收中的博弈與沖突[J].吉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36(2):48-54.[ZHANG Weidong, TAN Jiaqiang. Games and conflicts in rural housing expropriation[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36(2):48-54.]
[14]黃東東.公平補(bǔ)償?shù)牧⒎ㄟx擇——農(nóng)地補(bǔ)償市價(jià)標(biāo)準(zhǔn)質(zhì)疑[J].中國(guó)土地科學(xué),2013,27(4):36-41.[HUANG Dongdong. Fair compensation and its legislation choice: discussion on the standard of marketbased land compensation[J].China land sciences, 2013,27(4):36-41.]
[15]韓立達(dá),韓冬.市場(chǎng)化視角下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有償退出研究——以成都市為例[J].中州學(xué)刊,2016(4):43-48.[HAN Lida, HAN Dong. Study on rural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s exit with compen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take Chengdu for example[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6(4):43-48.]
[16]房紹坤,王洪平.論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流轉(zhuǎn)后征地補(bǔ)償費(fèi)的歸屬與分配[J].吉林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52(3):140-146.[FANG Shaokun, WANG Hongping.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of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fees after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 transfers out[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52(3):14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