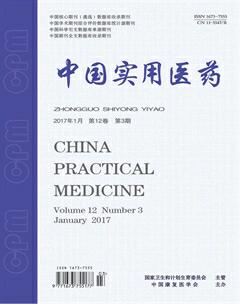肺癌終末期患者的臨床治療與關懷
韓麗娜 武晉 鄭建中
【摘要】 對于終末期肺癌患者的治療態度一直是業界的討論焦點, 究竟以抗癌治療為主還是以處理癥狀為主, 究竟是強調生的價值還是維護死的尊嚴。作者從治療策略的角度來論述終末期肺癌患者的治療意義, 認為終末期肺癌患者的治療并非沒有價值, 應該在控制疾病發展的基礎上, 以提高生存質量為目的, 以減輕疼痛和加強營養支持為重點, 同時兼顧人文心理關懷。
【關鍵詞】 癌癥;治療態度;生存質量;姑息治療;倫理思考;人文關懷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7.03.100
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了《全球癌癥報告2014》, 該研究稱全球癌癥患者及死亡病例都在急劇地增加[1], 其中肺癌是最普遍和最致命的癌癥:2012年約新增180萬患者并導致159萬人死亡, 其中中國約占此類病例的1/3以上。雖然近年來我國在肺癌的臨床治療方面有較大進展, 但由于大多數患者出現典型癥狀一段時間后才來醫院就診, 所以80%的肺癌患者在確診時已屬終末期, 遺憾的錯失了早診早治的機會。另外, 因為肺癌生物學特性十分復雜, 惡性程度較高, 預后較差, 對于中晚期且不適應手術切除者, 采用化療或放射治療, 其療效差于手術切除, 5年生存率不足15%。所以有些患者或家屬則更傾向于使終末期癌癥患者過早的進入臨終關懷或撤出生命支持, 而沒有意識到這些患者仍然還有選擇積極治療的權利和意義。
1 終末期肺癌概述
終末期肺癌患者指預計生存期不超過6個月的患者。對于錯失最佳手術治療手段的患者, 是應該繼續抗癌治療還是僅僅對癥處理臨床癥狀, WHO專家委員會認為, 當延長生命不能改變病情, 也不符合患者愿望時, 停止推遲死亡的一些治療措施在倫理上是可接受的。但是, 中國傳統習俗及情感需求, 使很多患者家屬要求醫生給這類患者繼續治療以延長其生命[2]。那些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家庭會選擇繼續治療使腫瘤縮小, 而另外一些家庭則會選擇處理癥狀或者直接將患者拉回家想吃吃, 想喝喝, 想玩玩。但事實上, 這類終末期階段的患者往往是“在家等死”。
2 終末期肺癌的治療
2. 1 確定治療目的 有研究表明, 分期影響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分期越晚, 患者生活質量越差[3]。對于不可治愈的腫瘤患者, 可以給予姑息治療, 在不增加患者痛苦和生命危險的前提下, 減少瘤負荷, 增進機體功能, 進一步提高終末期生活質量, 延長生存時間。即使是不能根治也無法延長生存的患者, 也應積極控制癌痛等嚴重影響生活質量的相關癥狀。
2. 2 可選擇的治療策略
2. 2. 1 姑息性放療 終末期肺癌患者常由于腫瘤侵襲、壓迫、壞死等導致局部癥狀嚴重, 采用低劑量、大分割放療模式, 可有效控制癥狀, 且副反應小、患者耐受良好。如放療可減輕骨轉移疼痛, 也可有效地減輕上腔靜脈梗阻綜合征、腦轉移等引起的各種癥狀。適度的姑息性放射治療在Ⅳ期非小細胞肺癌治療中不僅能有效地控制病情, 緩解癥狀, 減輕患者痛苦, 還能提高生存質量, 延長患者生命[4]。
立體定向放療(SBRT)是對晚期肺癌傳統姑息治療模式的一次突破。它是一種有效的低分割非侵入性消融治療, 通常治療1~5次, 每日1次或隔日1次。對不能手術切除的部分終末期肺癌患者的腫瘤控制率高、正常組織耐受性好, 有相當不錯的臨床效果。應用SBRT治療技術的速鋒刀(EDGE)腫瘤無創放射手術治療系統, 它具有常規手術和放療設備都難以實現的治療效果。自2014年4月全球第一套EDGE腫瘤無創放射治療系統在美國亨利福特醫院全系統運行以來, 已經治療400多例腫瘤患者, 腫瘤控制率>95%, 且均沒有出現不良反應。而在這些腫瘤患者當中, 肺癌患者就占29%。
2. 2. 2 姑息性化療 化療是晚期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療手段, 但終末期肺癌患者通常難以耐受標準的含鉑雙藥聯合方案, 培美曲塞或多西他賽等單藥化療常可達到有效控制率。
姑息化療或挽救性化療是終末期肺癌患者的一種治療手段, 在評估患者一般情況、各臟器功能、既往用藥情況、化療藥物毒副反應、患者受益分析等做出全面評估后, 在治療前充分尊重患者的選擇權和知情權, 特別強調醫患溝通與規避損傷, 如利大于弊, 可選擇化療。而對病情危重、一般情況極差或惡液質患者, 一般不冒然給予化療。
研究顯示[5], 姑息化療對終末期肺癌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 非化療組1年生存率41.8%, 化療組患者1年生存率76.6% (P<0.05), 兩組患者生存質量相比, 姑息化療組患者生存質量比非化療組高;生存時間超過1年組患者的整體生活質量量表(GOL)評分、KPS評分、血清白蛋白含量均高于1年內的患者(P<0.05)。
2. 2. 3 營養支持治療 腫瘤營養治療是計劃、實施并評價營養干預, 以治療腫瘤及其并發癥或身體狀況, 從而改善腫瘤患者預后的過程, 包括營養篩查或評估、營養干預、療效評價三個階段。當營養支持不僅僅是補充營養素, 而是被賦予調節代謝、調理免疫、治療營養不良等使命時, 營養支持則升華為營養治療以降低腫瘤發病率、延長生存時間、提高生存質量[6]。
但在實際生活中, 人們對營養和代謝不良對腫瘤患者帶來的負面效應認識有限, 大部分腫瘤患者確診即為晚期, 營養和代謝不良同時存在。“腫瘤開始發生時即應對營養狀況做相應干預”這是Prof. Maurizio Muscaritoli在“平行通路”概念中所提到的。
事實上, 絕大多數住院患者在終末期均接受了靜脈補液等營養支持治療。有研究證明, 實施營養支持療法后, 肺癌患者的軀體功能提高, 疲乏和惡心嘔吐有所緩解;對化療期間情緒、失眠癥狀、呼吸困難、口腔疼痛、脫發、胸痛等癥狀均有所改善[7]。
2. 2. 4 疼痛治療 軀體疼痛是終末期肺癌患者的主要癥狀之一, 表現為由癌癥直接引起的癌痛或因治療癌癥引起的疼痛或其他疾病引起的疼痛。越來越多的循證證據證實:癌癥患者生存期與癥狀控制相關, 并且疼痛管理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 因此疼痛治療是腫瘤治療中的重要環節。1995年美國疼痛學會主席James Gampbell提出將疼痛列為第五生命體征, 亦有學者提出疼痛是一種疾病。評估疼痛癥狀和生活質量, 根據NCCN成人癌痛指南給予恰當的治療, 提高舒適度和功能, 同時嚴密觀察不良反應并給與相應對癥措施。
藥物治療癌痛, 通常使用WHO倡導的三階梯療法, 可使85%~90%的癌痛獲得滿意緩解[8]。研究顯示[9], 使用藥物治療癌痛后, 患者中度疼痛緩解92.9%, 重度疼痛緩解85.7%, 總緩解率為88.6%;患者社會功能、情緒功能、軀體功能、失眠、整體質量均明顯改善, 整體健康狀況提高, 并有效減少了阿片類止痛藥的使用劑量(P<0.05)。
終末期肺癌患者置入自控性止痛泵, 是目前療效確切的治療方法, 達到相同止痛效果的同時, 攜帶使用方便, 相較皮下或靜脈用嗎啡或芬太尼, 泵入的劑量極低, 成癮性低、副反應小。
2. 2. 5 分子靶向治療 分子靶向治療是21世紀肺癌治療的重大突破, 針對可能導致細胞癌變的環節, 從分子水平遏制惡性生物學行為, 從而抑制腫瘤生長, 甚至使其完全消退, 達到與癌共存, 延長生存期。
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 分子靶向治療已逐步取代化療的一線地位, 顯示出依從性好、副反應小、生存期更長等優勢。如生長表皮因子受體絡氨酸激酶抑制劑(EGFR-TKI)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對EGFR突變的肺腺癌有非常好的療效;而克唑替尼對EML4-ALK 基因重排或ROS-1融合基因型的肺腺癌有良好效果。2017年非小細胞肺癌NCCN指南將EGFR、EML4-ALK、ROS-1、c-MET、RET、Herb-2等基因列為肺腺癌患者推薦檢測指標, 根據基因檢測指標選擇不同靶向藥物治療, 是晚期肺癌患者首選治療方案。而確定分子亞型、篩選靶向治療人群也是非小細胞肺癌個體化治療的關鍵[10, 11]。
2. 2. 6 介入治療 研究顯示[12], 將106例肺癌患者分為介入治療組, 與同期90例行吉西他濱聯合順鉑(GP)方案進行全身化療的患者(GP組)進行比較、評價治療后效果時發現, 介入組患者和完全緩解(CR)、部分緩解(PR)、疾病穩定(SD)及疾病進展(PD)均明顯優于GP組, 介入組和GP組的總有效率分別為80.2%和48.9%, 介入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發生率明顯低于GP組。由此證明血管介入在治療肺癌中的應用具有很好的前景, 可作為臨床治療肺癌的有效手段之一。
2. 2. 7 人文關懷 與其他癌癥的患者相比較, 肺癌患者有軀體癥狀的沉重負擔, 而且心理易激惹比例高。其臨床顯著激惹在40%的人群中已經被檢查到。由于肺癌患者的易激惹性, 其在軀體癥狀、死亡和生存擔憂、呼吸困難和焦慮、衰弱和抑郁癥、失眠和疲勞、戒煙以及藥物治療的選擇等方面均應給予適當的人文關懷[13]。可應用傾聽、鼓勵、暗示等心理干預手段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也可讓取得改善結果的患者傳授抗癌經驗, 消除其他患者顧慮, 增加信心;同時通過對患者的同情、關心、安慰等人文關懷完善患者心智, 提升患者的自我認知和尊嚴[8]。
2. 2. 8 其他 射頻消融:2000年, Dupuy首次報告了射頻消融在肺惡性腫瘤中的應用。因其微創、有效、可重復性, 現已廣泛應用于臨床無手術指征的肺惡性腫瘤的治療[14]。
熱消融術:有研究在對56例患者進行腫瘤熱消融術治療后, 臨床評價完全有效8例(14.3%), 部分有效27例(48.2%), 輕度有效21例(37.5%), 即時有效率為100.0%。術中、術后患者未出現嚴重并發癥。此結論證明熱消融術治療中央型晚期肺癌療效佳, 并發癥少, 麻醉風險低, 患者耐受好, 值得借鑒和臨床推廣[15]。
生物治療:以非特異性免疫刺激為主要手段的生物治療在腫瘤綜合治療中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 比如抗新生血管生成治療、溶瘤病毒治療、干細胞治療、誘導分化及凋亡、內分泌治療等。
免疫治療:腫瘤免疫治療主要包括特異性主動免疫治療、被動免疫治療及過繼免疫療法。在對腫瘤微環境的深入認識基礎上, 腫瘤免疫治療是一個進展迅速的研究領域, 是腫瘤治療的重要方法[16]。近三年ASCO會議最熱門的討論話題、最新的研究進展正是免疫治療, PD-1 (細胞程序性死亡-1) 和PD-L1 (程序性死亡配體1)抑制劑的研發和臨床應用, 對多種腫瘤顯示了良好療效。其中對肺癌患者的高敏感性、有效性、高控制率、低毒性, 更是曙光初現, 給肺癌治療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天地。未來研究方向如靶向聯合免疫治療、化療聯合免疫治療、新輔助或輔助免疫治療均是研究的契合點。
基因治療:以基因沉默治療、抑癌基因治療、免疫基因治療、自殺基因療法、抑制腫瘤血管生成基因治療、腫瘤多藥耐藥基因治療、抗端粒酶療法和多基因聯合療法等方面的腫瘤基因治療也已經成為腫瘤治療的研究熱點之一。
中醫輔助治療:中醫、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非小細胞肺癌在減輕化療毒副作用, 提高生活質量, 提高近期療效及無進展生存期, 總生存期, 預防復發轉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17]。
3 家屬的治療態度
痛苦地活著, 還是有尊嚴地死去, 這是個問題。醫院的患者離開這個世界時, 通常是兩種情況, 一種周身插滿管道, 一種身上沒有任何管道。當生命依賴無數管道來支撐時, 生命的意義是什么, 從容走向死亡似乎是更為解脫的抉擇。醫生是決策者和執行者, 但醫療決策不該只是醫生。拋開復雜的文化、宗教、社會資源等因素, 醫患雙方應達成共識:注重生命質量。維系沒有質量的生命是種無謂的治療, 不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親人的痛苦, 加重家庭負擔, 更是對人道主義精神的違背, 對社會醫療衛生資源的浪費。
醫生不僅僅需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精湛技術來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 更需要用自己的哲學學識、人文關懷讓患者從容面對死亡。患者家屬應當配合醫護人員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 有效延長親人生命, 使親人無痛苦、舒適、有質量地生活, 最終達到讓親人與癌共存甚至消滅癌癥, 或者平靜、安詳地接受癌癥或是死亡。從而使癌癥患者得到真正有意義、有質量的生命。
4 討論
終末期肺癌患者的積極治療是有一定價值的。針對這樣一個有高流失率和高癥狀負荷的惡性腫瘤患者群體來說, 其最佳治療不僅是疾病本身的治療, 還要對癥處理, 給予以緩解癥狀、改善生活質量為目標的 “個體化治療”, 為患者“量體裁衣”。這樣不僅能緩解患者的痛苦, 也避免了因過度治療所致的痛苦, 能合理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的同時也符合現在醫學倫理學的要求。
在對肺癌治療的研究進展中發現, 不斷有新的突破, 針對肺癌的基因突變或重排、分子受體、代謝調控、分子通路阻斷、免疫抑制點的抑制治療, 從基因、分子、受體、信號傳導等方面的基礎研究到臨床應用, 把病因、預防和治療很好地連貫了起來。同時應早期引入姑息治療, 提高生活質量, 緩解侵略性臨終治療, 合理促進生存期的延長[18]。
隨著國內首家“肺癌精準醫學研究中心”項目在全國多家醫院的啟動, “精準醫學”理念在終末期肺癌領域的實踐應用將成為人們討論與研究的焦點。而上述這些都將是醫務人員面對的機遇和挑戰。
參考文獻
[1] 張艷紅, 王珂, 潘戰和. 你患癌癥的概率有多大? 健康與營養, 2014(6):32-34.
[2] 曹培國, 鄭蘭香. 晚期惡性腫瘤的姑息治療與臨終關懷. 實用預防醫學, 2004, 11(1):25-27.
[3] 張凌云, 于萍, 劉云鵬, 等.腫瘤患者化療期間的生活質量調查與分析.現代腫瘤醫學, 2007, 15(6):860-862.
[4] 楊俊體, 蘭勝民, 曹建忠, 等. Ⅳ期非小細胞肺癌姑息性放療臨床價值回顧性分析. 中華腫瘤防治雜志, 2012, 19(18):1413-1416.
[5] 陳坤燕. 姑息性化療對晚期肺癌患者生活質量的干預作用. 醫學信息(旬刊), 2011, 24(7):2942-2943.
[6] 石漢平. 腫瘤營養療法. 中國腫瘤臨床, 2014(18):1141-1144.
[7] 蘇文利, 彭少華, 林海峰. 營養支持療法對老年原發性支氣管肺癌患者化療期間生活質量的影響. 中國醫藥導報, 2015, 12(6):44-47.
[8] 張純, 裴圣廣. 提高惡性腫瘤患者生存質量的倫理思考. 中國醫學倫理學, 2008, 21(4):116-117.
[9] 汪德明. 三階梯止痛治療加姑息性化療與晚期腫瘤患者生活質量的關系研究. 淮海醫藥, 2013, 31(1):46-47.
[10] 馬駿. ERCC1, BRCA1, β-tubulinⅢ, RRM1的表達與ⅢA-N2期非小細胞肺癌完全切除術后化療藥物選擇及預后相關性的臨床研究.廣州, 中山大學.
[11] Cheng L, Zhang DY, Eble JN. Molecular Genetic Pathology. 2nd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13:176-191.
[12] 顏景臣.血管介入治療肺癌的療效觀察.中國腫瘤臨床與康復, 2015(1):34-36.
[13] Key RG. Psychiatric care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Oncology, 2015, 29(3):732.
[14] 曾川, 張獻全.肺癌的射頻消融治療現狀及進展.中華肺部疾病雜志(電子版), 2015, 8(2):99-101
[15] 姚漢清, 王正東, 朱湘平, 等. 支氣管鏡介入熱消融術治療中央型晚期肺癌的臨床觀察. 中華肺部疾病雜志電子版, 2015, 8(1):43-46.
[16] 張立煌, 王青青.惡性腫瘤免疫治療的現狀及展望.浙江大學學報(醫學版), 2010, 39(4):339-344.
[17] 胡廣生, 王云啟. 非小細胞肺癌的中醫藥治療研究進展. 中醫藥導報, 2015(2):59-61.
[18] Temel JS, Greer JA, Muzikansky A, et al. Early palli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10, 363(9):733.
[收稿日期:2016-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