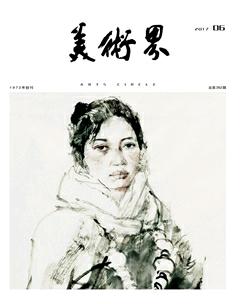維米爾與《繪畫藝術》
張熙
【摘要】維米爾的每一件作品都堪稱靜謐、優雅的典范,但其實畫中隱藏著諸多矛盾。這種矛盾既包括通過細節展現戰爭、暴力等社會問題,也包括對畫中事物不合常理的安排。本文從維米爾當做廣告的得意之作《繪畫藝術》出發,梳理了維米爾畫中的矛盾,提出維米爾對畫家身份的自我認知,維米爾認為畫家的目的不是復寫自然,而是要創造一個存在于畫室之中的全新秩序。
【關鍵詞】維米爾;繪畫藝術;圖像學;繪畫符號;圖像形式
提到維米爾的作品,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沉默的女人和靜謐的氛圍。把維米爾和顛覆性、破壞性這樣的詞聯系在一起,對大部分維米爾愛好者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勞倫斯·惠斯勒是極少數幾個注意到維米爾作品中那些不平靜瞬間的批評家之一,他梳理了維米爾所處的時代背景:與西班牙歷時彌久的三十年戰爭;信仰新教的聯合行省和信仰天主教的南部弗蘭德斯省之間殘酷的宗教爭斗;英荷、法荷之間糾纏不斷地摩擦;對維米爾一生都影響深遠的1654年德夫特軍火庫爆炸事件——他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良師摯友法布里斯。基于這一系列原因,惠斯勒提出維米爾畫中的平和是有意為之的、是制造出來的。
惠斯勒據此解讀那些畫中經常被忽略的細節,他認為:椅背上雕刻的怒吼的獅子,代表了一種暴力的入侵;老舊的地圖則記錄了國家邊界的變化;退役的或者醉酒的士兵是國家深陷戰爭泥沼的典型標志。而維米爾的畫室,作為超越時代背景的、沒有戰爭的、烏托邦的空間,用繪畫的力量將處于狂風暴雨中的世界拒之于門外。
惠斯勒對維米爾的看法打擊了大部分抱著某種“成見”去欣賞維米爾作品的觀者。但是結合維米爾的生活狀況不難發現,“暴力”作為形成他繪畫空間的重要因素是理所當然的。通過留存下來的政府文件和法庭記錄,米修·馬丁還原了維米爾的生活,他的生活狀態與畫中那個寧靜、優雅的資產階級生活圖景嚴重不符,由此我們更加確信繪畫對于維米爾來說是一個安全的、和平的、田園詩的存在。
《繪畫藝術》因創作時間之長,以及它自我介紹的廣告性質而成為一幅真正關于維米爾內心的作品。
維米爾習慣于將作品的視覺消失點設置在希望觀者注意的部分,在《繪畫藝術》中,它被放置在模特手部附近。畫中模特身著華服、頭戴桂冠、手持書本和喇叭。直到1950年,這身行頭的真正含義才被一位法國藝術評論家在無意中發現。解密的關鍵線索就在凱撒·里帕的《圣像學》中,這部書出版于16世紀,于1644年被翻譯成荷蘭文,并迅速成為當時畫家人手一本的象征符號辭典,它主要用于指導畫家繪制歷史人物。其中有一段描述歷史女神的文字“她頭戴桂冠,拿著一只小喇叭和一本書,桂冠象征榮耀和永生,喇叭象征名譽,書本代表對歷史的記錄”,于是,在此畫完成三百年后,畫中女子的身份終于得以確認,她就是歷史女神克莉歐,對《繪畫藝術》的解讀也進一步拓展到歷史領域。
像維米爾的其他作品一樣,《繪畫藝術》中也有幾個奇怪之處,這成為我們理解作品的重要起點。
第一,關于畫家的服裝。荷蘭服飾學家馬利凱·溫克在經過考證后提出,它們是早期服飾,但是在1620左右開始重新流行,并在1660年,也就是《繪畫藝術》誕生左右到達頂峰,此時它并不是作為日常生活著裝,而是作為出席重要場合的禮服而風靡一時。那么,畫中藝術家為什么要穿這么隆重的服飾進行創作呢?
第二,畫家的創作方法并不符合與維米爾同時代的畫家們的作畫習慣。經過專業學習的維米爾和其他北方畫派的畫家們,在作畫前要先用褐色顏料描繪出光線和基本構成,然后再層層上色。開始的黑白階段被稱為底色,這種方法被當時造型精準、畫技精湛的藝術家們運用得爐火純青。而畫中那位畫家卻像在畫數字油畫的孩子,他從上往下,先勾形,再上色,可以說是對意大利繪畫的拙略模仿。另外,維米爾作畫常用的調色板和帶抽屜的柜子也沒有出現。
第三,畫家頭上的吊燈并沒有與房頂相連,它是浮在空中的。燈頂上雙頭鷹的標志代表著哈布斯堡王朝,這個以天主教為信仰的西班牙王朝在1581年左右統治尼德蘭,在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合約》之后正式宣布統治結束。它為什么會以這種形式出現在畫中?
第四,墻上的地圖和吊燈一樣,屬于一個更早的時期。這幅地圖的原本留存至今,經過對比就會發現,維米爾無比精確的復制了這幅地圖。《繪畫藝術》甚至因此曾被用作圖像文獻來證明原地圖的誕生要比相關學界認定的早四年。這幅地圖的最初版本由克里茲·維斯特繪制,《繪畫藝術》中的這幅是他的兒子尼古拉斯的修訂版。它詳細地描繪了尼德蘭十七省分裂為新教七省聯邦和南部天主教十省的情況。
這些問題表現出《繪畫藝術》對傳統繪畫符號寓言功能的“祛魅”。阿爾帕斯注意到,畫中地圖右上角的標簽中荷蘭語的“描繪”。他認為這是一個雙關語,是對荷蘭“描述”美學的暗喻。他還認為這個詞是荷蘭繪畫藝術的精華所在:它忠誠于視網膜上反映的視覺影像,它拒絕意大利藝術符號和傳統敘事,它通過對細節的精確描繪來傳達知識,它嘗試挑戰程式化并試圖改變視覺在繪畫中的地位。阿爾帕斯相信,歷史的概念在17世紀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折,變為一種簡潔的、基于事實的、無需闡釋的描繪性科學,他認為《繪畫藝術》是這種轉變的有力證據:維米爾用它端莊的模特和宏偉的地圖來表達對新歷史的慶賀。
《繪畫藝術》的確是對符號慣性的挑戰。從觀者的角度出發,我們越過畫家肩膀看到的并非克莉歐,而是一個身著華服的年輕的荷蘭女孩。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繪畫藝術》去神秘化的用意。從這個角度來說,阿爾帕斯是對的,維米爾的確用荷蘭人的觀看方式重構了對歷史的接受態度。但是,阿爾帕斯沒有發現維米爾在作品中傾注的個人力量——不管是對傳統寓言和符號的“明顯的排斥”,還是對歷史的表述方式的革新,或是用普通鄰家女孩代替凱撒·里帕“圣像學”中信仰的締造者們——維米爾將這一切歸因于畫家的選擇,作為畫家自我意識的反射。
因此,重新審視畫中的地圖,我們真正應該注意的或許不是阿爾帕斯強調的寫實性的描述,而是那道看似自然實則刻意的龜裂——那道在視覺上增加了地圖的空間感和光影美感的裂縫正處于南北尼德蘭的分界線上(當時的地圖以右邊為北)——這條龜裂證明,這幅地圖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是對客觀世界一絲不茍的復寫,它提醒觀者維米爾已經將他的歷史認知和美學理念融入了維斯特的地圖中,融入到畫室內那些看似如實描摹的事物里。維米爾并非完全丟棄了那些圖像學符號的內涵,而是通過重新部署它們,通過上文中提到的幾個不同尋常的“疑點”,為繪畫符號賦予了新的個人化的意義。由此,繪畫成為一種異于客觀存在的、被主觀視角所重構的圖像形式。
至此,我們似乎能夠發現維米爾對畫家身份的自我認知,和傳統的、致力于提高社會地位的畫家不同(他們認為畫家要忠實描繪自然,并通過控制意義對社會加以引導),維米爾的確精確地描繪了畫室中的事物,但他有更大的野心,他的目標不是復寫自然,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自然——一個存在于畫室中的第二自然,一個關于社會和歷史而非模仿的空間。
參考文獻:
[1][法]邁克爾·蒙迪亞斯.維米爾和他的生平:社會歷史學的網絡[M].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9.
[2][美]斯維特拉娜·阿爾珀斯.描繪的藝術:17世紀的荷蘭繪畫[M].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