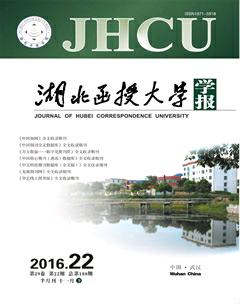傳統文化產業化面臨的陷阱與困境
沈瀅
[摘要]入世以來,為應對西方國家文化產品輸入可能帶來的意識形態入侵,同時也為積極融入全球化趨勢,國家將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作為重大發展戰略。伴隨我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壯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對于文化自覺和正當性的需求日漸突出,在追求“軟實力”為政策導向的背景下,傳統文化產業化策略應運而生。而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角度看,在當下更加復雜的全球化趨勢和背景下盲目對傳統文化文化進行產業化發展,會忽視產業化本身所蘊含的商業資本邏輯對文化本質的傷害,對于產業化本身不客觀、不全面的理解,在文化傳播實踐過程中遇到突發情況會讓自身更加被動。而且對“文化軟實力”的盲目崇拜本身就有將自身主動“他者化”的風險。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產業化;傳統文化
一、從批判的“文化工業”到力捧的“文化產業”:批判話語被悄然遮蔽
“文化工業”一詞最早出現于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于1947年出版的《啟蒙辯證法》,用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大眾文化的商品化及標準化。其核心觀點認為以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為基礎的大眾文化工業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是一種異化與虛假的文化,而且“文化工業”給資本家帶來豐厚利潤的同時也使人們在媒介文化產品的消費中不自覺的認同統治者的價值觀,喪失批判能力,從而達到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可見“文化工業”一詞的誕生是包含著濃濃的批判色彩。上世紀該概念被引入中國的大眾文化批判中,不過當時的中國大眾文化發展并沒有形成實質上的“文化工業”規模。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從原先的“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y)逐漸轉向“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ies)分析,將其視為具有內在結構和職業關系的完整產業體系。批判角度也從以前單一的宏大敘事的意識形態轉向“面對文化產業自身的邏輯關系和結構性質,注重考察技術創新、社會分化和趣味差異所形成信息傳播的離散趨勢”。但是不管批判的角度有何變化、概念翻譯有何區別,有一點是沒變的,那就是這個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批判性色彩。然而當文化工業概念演變到“文化產業”,又一次走進國內學術視野中時,它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已經被悄然消除了,不僅成為文化經濟新的增長點,更成為傳承發揚民族文化的有利工具。
這一有意無意地忽略或轉換,其實就已經無形中遮蔽了產業化發展中可能要遭遇的問題和困境。正如陳衛星陳衛星在其文章中指出,文化產業的發展中“交織著個人生活與社會議程、公共服務與消費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技術統治與技術解放等諸多相互參照的力量”,其中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但這些參照力量及復雜關系都被國家出面主導的“文化產業”政策所或多或少忽略了。在具體的文化傳播實踐中,各種復雜力量的角逐引發的文化現象或是問題凸顯出來,并引發相關輿論時,政府的應對就顯得那么不知所措力不從心。
二、從文化產業到傳統文化產業化:國家話語的一脈相承與國內外環境的今非昔比
(一)傳統文化產業化是繼續完成文化產業未竟之使命
傳統文化的產業化發展如同當初人世后開始大力提倡文化產業的發展一樣,更多的是源于國家文化戰略高度的考慮。倘若說政策給予了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是我國目前文化產業、尤其是大眾文化或更甚者就是娛樂文化的發展如日中天的最重要原因,那么今天的大眾文化發展中所出現的種種飽受詬病的現象弊端,如泛娛樂化、低俗化等也是文化產業化過程中的必然。
而傳統文化的發展與一般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又有所不同,它所承載的使命和功用更有所不同,如果說當初我們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目的是用以抵抗外來文化入侵和侵蝕、守住意識形態領域和陣地,那么今天派出“傳統文化”出征,無疑可以看做是承認出于政治因素考慮的政策帶來了經濟上的可觀成就,卻沒有完成本意上的政治使命。從人世至今,文化領域對外開放程度一次次被迫加大,然而留給國內文化產業迎頭趕上的時間看上去并不那么充足,比如我們的國內電影市場的確比開放之初繁榮的多,國產影片的票房也的確在用數據說話,但是進口影片對于國內影片的碾壓也是不言而喻的,從院線將國內影片與引進大片調開檔期就能看出來。更不用說青少年對于日美韓動漫以及其中透漏的價值觀的無形吸收與向往。在這種背景下,面對經濟上日漸崛起,文化上卻不能提供相匹配的大國地位的弱勢,十八大以來政策制定就將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崛起提上重要日程。繼承文化產業化尚未完成的使命,傳統文化走向產業化之路。
(二)舊的使命遇上新的環境
但是正如上文所說,傳統文化畢竟不同于一般的大眾文化。而且,當下的國內外環境與當時也不可同日而語。
全球化在今天對于文化傳播的政策指定、對于文化實踐的實際影響已經是全方位的,它對于政治、經濟、媒介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放松管制和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盛行使得民族國家的政策干預面臨著弱化的趨勢,從而威脅著公共服務/管理的職能。傳媒產業重組的潮流使得金融資本網絡對信息傳播產生越來越大的支配性和壟斷性。信息傳播技術的接近不平等依然存在,更需要探討如何以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社區傳播或另類傳播的發展來改變傳播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這不僅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今天繼續揭示新的社會結構和權力賭注的發展背景,也是對傳統文化產業化所必須面對的復雜環境的高度概括。
(三)商業化——資本邏輯下的傳統文化發展困境
據此看來,傳統文化產業化所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可能是產業化的資本邏輯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盛行的國際背景下終會跳脫政治手段的控制,無法達到利用資本為傳統文化價值升值的目的。按照資本的本性和邏輯,產業化運作首先尋求資本的鏈接和累積產出效應,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文化傳媒經濟實體本身在經歷各種兼并、重組,并與跨國文化傳播媒介在競爭中合作,其中利益紛爭復雜程度不言自明,在實際的文化投資生產過程中平衡政策的導向性和資本收益會成為傳統文化在傳播中遭遇的又一困境。由吳天明執導的《百鳥朝鳳》之所以上演出品人下跪的一幕,不僅僅是表面上所謂炒作要票房那么簡單,影片在豆瓣上評分超過8分,但是票房慘淡,雖然有影評人對導演的一跪以淚水博眼球換票房的行為嗤之以鼻,覺得市場最有說服力,但是實際上影片在院線的拍片少卻是不爭的事實。“與影片的爆棚口碑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其尷尬的排片數量。據統計,在同為5月6日新上映的五部影片中,《美國隊長3》首日上座率為34%,《百鳥朝鳳》緊隨其后,為14.6%。然而相比《美國隊長3》首日53.8%的排片占比,《百鳥朝鳳》的排片只有2%。到了5月8日,《美國隊長3》的排片為55.6%,上座率為31.0%,而《百鳥朝鳳》的上座率雖升至20.6%,排片卻降至1.2%。5月9日截至16:30,《百鳥朝鳳》當日上座率已經達到7.9%,超過了《美國隊長3》的6.9%,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但排片占比仍然極少。…‘更值得注意的是,《百鳥朝鳳》絕大部分場次被安排在上午或晚上十點以后,黃金場次排片極少,許多觀眾表示想看電影卻買不到合適場次。”
一部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良心制作,在面對產業化的文化市場、院線安排,高口碑低票房幾乎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三、文化軟實力——新的崛起突破口還是他者話語的“圈套”?
(一)文化軟實力追求與弱國心態
中國傳統文化產業化方向的提出是在官方政策導向前提下提出的對策,而出發點是為的實現所謂軟實力的增強,提升國家形象和民族自信心。有學者很生動的總結了我國近代以來在不同歷史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分別用了三十年通過革命和建設來解決“挨打”問題,又用了三十年解決挨餓的貧困難題,目前面臨的則是在國際上動輒“挨罵”的問題。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其實就是要解決文化自覺與文化正當性問題,說到底,我們大力發展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在“弱國”心態下提出的被動應對策略。這種背景和心態容易導致我們對于外來文化和價值觀念傳播的過度提防。
(二)過度防范導致對傳統文化發展的傷害
對外來文化過度的防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過度推崇而導致的復占傾向,二是對國外文化產品的過度抵制。這兩種趨向都不利于保護和發展我們的傳統文化。
前者常常導致文化生產實踐耽溺于民族傳統文化符號的堆砌或賣弄,而罔顧文本內容質量,生產不出真正有吸引力的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作品,甚至會在商業原則下被文化產品制作、生產、流通環節偷梁換柱形成對傳統文化符號的過度消費和傷害。比如曾紅極一時的央視文化節目《百家講壇》,在專業人士看來無非了借了傳統文化的外衣符號,實現了電視臺廣告商和部分文化學者的雙贏,而主講人以專業學者身份,為收視率博眼球,對經典故意進行曲解,不管是對傳統文化還是對廣大普通的受眾都是一種不尊重和傷害。還有部分影視作品為了刻意突出中國風,中國元素,強行在作品中嫁接傳統文化符號,不管是水墨丹青的特寫還是中國古代禮儀風俗的特意呈現,其實與劇情本身需要關系不大,在這些作品里傳統文化以不連貫的符號牽強其中,成為可有可無的點綴,與整部作品的思想內核關聯不大,使作品的整體性完整性大打折扣,所包含的傳統文化價值的吸引力也無從談起,其中所宣揚的中國符號、傳統文化元素在作品被宣傳之時已經被消費殆盡。如號稱“十年磨一片”的《大魚海棠》,從片頭設計到劇中作為背景的每個細節都經得起推敲,全劇的色彩畫面也的確如宣傳所言,充滿中國味道,但是在技術上如此用心的一部國產動漫,卻因為將民族文化符號當成最大賣點反而忽略了劇情劇本的設計,故事本身并沒有多大的吸引力,雖宣傳有效票房甚高,但卻沒有獲得預想中的口碑和褒揚。而對外來文化的過度抵制往往激起民間對外來文化向往的報復性反彈,引發民眾對本民族本國文化正當性的質疑和排斥。
(三)重新思考軟實力——走出他者話語的圈套
最早提出將權力資源二分為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是約瑟夫·奈,而他這個提法已經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在當今國際環境下離開軍事和經濟實力單純的靠文化軟實力就能打造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吸引力是不現實的,比如美國文化橫掃全球,其背后依仗的是美國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根據華人學者趙月枝的觀點,這種提法很有可能是西方在對華意識形態斗爭中所用的一種戰略。“軟實力”與“硬實力”好比蛋與雞孰先孰后一樣只能導致循環論證。而當下中國大力追求發展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種無奈的“應對之策”。為的是平衡國際輿論中對于中國政府的批評,同時也是為了塑造有利的國際形象。而“中國的改革轉型過程在意識形態上挑戰了‘資本主義同自由民主制必然緊密相關這一西方神話,使得西方媒體一直受困于自身的意識形態牢籠。”只要中國政權形式不變,就會被西方媒體當作意識形態的假想敵,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單純地追求所謂國家軟實力,以期改變對方對自己的想象與刻板印象根本就是徒勞。可見軟實力追求與國家形象的塑造背后仍然是我們以他者的眼光在審視自身,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塑造一個讓西方世界滿意的國際形象,然而正如趙月枝所分析的那樣,中國的獨特的改革與發展道路本身已經讓自己置身于西方國家所警惕的對立面,再一味按照他人的標準雕琢自己實質上就有可能是中了圈套。
所以按照趙月枝的說法,追求“軟實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響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得有一個大家都視之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文化一倫理格局,然后廣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樂。”以此為邏輯,傳統文化發展如果將著眼點依然放在“把我講給你聽”,對外講好中國故事,不停地向西方世界表白自己的優秀與無害,那么根本就是雞同鴨講,所以導致傳統文化產業化發展的具體文化實踐中總遭遇尷尬,挖掘傳統文化的魅力與吸引力不是不可以走產業化道路,但是著眼點也許更應該放在國內受眾,尤其是青年人身上,我們的文化對這個國家未來的主人有吸引力才能真正算得上是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