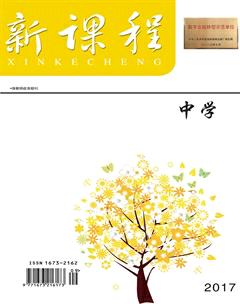徜徉田園詩海 提升審美趣味
張春霄
摘 要:語文是人類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語文活動是人形成審美體驗、發展審美能力的重要途徑。而中國古典詩歌是中學生學會審美、傳承文化的豐富源泉。主要通過山水田園詩歌經典作品鑒賞自然風光之美、田園生活之美、田園耕作之美、鄰友親善之美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從而讓學生在閱讀鑒賞優秀作品中體驗豐富情感、激發審美想象,并逐漸形成自覺的審美意識和審美能力,養成高雅的審美情趣和高尚的品位。
關鍵詞:核心素養;山水田園詩;審美;文化
美育是指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觀,發展學生鑒賞美和創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在人的全面發展教育中,美育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能陶冶情操,而且還有助于智力開發,進而提升德行品行,正如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言,“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也”。而語文核心素養中重要的學科期待,正是能夠讓學生在健康的、美的、具有正能量的廣泛閱讀中增加文化積淀,豐富精神世界,提升鑒賞和審美能力。
中學生正處于情緒敏感的青春期,他們內心開放,思想活躍,求知欲強,對美的人、事有異乎尋常的心理需求,這正是語文學科順利開展審美教育的重要條件。而放眼當下,這又是一個信息爆炸、全民娛樂、審美異化的時代,人們對快餐文化、碎片閱讀樂此不疲,八卦刷屏,韓流不斷,文化生態光怪陸離,亂象叢生。在這種情況下,中學生感知美、發現美、創造美的能力又將會如何?這是一個讓人憂心忡忡的問題。作為嶄新的一代,又必將承擔文化傳承的重任,他們的現在也在決定著民族的未來。
而語文尤其是古典詩歌,飽含國人深沉豐富的內心情感,體現了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是培養學生高雅趣味、充實學生高潔心靈、實現學生高尚精神的重要途徑。山水田園詩歌,是中國古典詩歌非常重要的題材之一,也是中國文人“士”文化主流價值觀之外的別一人生范式,他們寄情山水,走向田園,在日常與自然里實現著詩意和美的發掘,通過清淡悠遠的詩句勾連起你我穿越時空的審美家園。
一、自然風光之美
自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塵世如樊籠,自然才是家園。凡是詩人,總是要從大自然中取法的。風景的詩意之美,在山水田園詩中尤為明顯。“春游芳草地,夏賞綠荷池。秋飲黃花酒,冬吟白雪詩”(汪洙編《神童詩》),草長鶯飛木深蛙鳴,流云碧空落紅映雪,春夏秋冬流轉,四時之美各異。詩人們用簡練淡雅之筆,描畫田園清幽靜謐、靈動飄逸之美,表達返璞歸真、恬淡自適的詩意情懷。
古樸的村墟隱于山水間,炊煙裊裊之中夕陽西沉,綠意幽幽之下稚子愚頑,狗吠深巷雞鳴樹顛,柳絮迎風葵花向日,“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王維《渭川田家》)就是這樣一幅樸素雅致的鄉村日暮圖,意境悠遠,歸人愉悅。中國的傳統民居和園林藝術充分體現了自然山水啟迪之下的這種詩情畫意:門內有徑,徑轉有屏;階畔有花,花外有墻;石面有亭,亭后有竹;竹影婆娑,庭院深深。或許不過竹籬茅舍,亦須堂前羅桃李,檐后蔭榆柳,“屋中春鳩鳴,門前流水清”(王維《春中田園》);“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江畔獨步尋花·其六》),院中花開滿枝,戲蝶飛舞,嬌鶯鳴啼,繁華似錦;“晝永蟬聲庭院,人倦懶搖團扇。小景寫瀟湘,自生涼”(陸游《昭君怨·晝永蟬聲庭院》),夏木蔥蘢,蟬聲彌漫,天熱人倦,唯瀟湘之竹,送來清涼。
“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春”(盧照鄰的《春晚山莊率題二首》之二),人可在人外,但得在春中。“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陶淵明《歸園田居》),閑人徜徉野田山林,“晴明風日雨干時,草滿花堤水滿溪”(楊萬里《桑茶坑道中》),色彩清麗,景致錯落;“童子柳陰眠正著,一牛吃過柳陰西”(楊萬里《桑茶坑道中》),明媚和暖,趣意盎然;“獨出門外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白居易的《村夜》),朦朧的月光和隱約的麥田構成了夜的詩意背景,即使心思寥落時,也能悲而轉喜,幸甚樂甚!在自然的美妙畫卷里,清泉霧靄松濤隨風,蜻蜓繞籬白鷺跳波,黃梅野徑麥花如浪,沉浸其中,實在有“別有天地非人間”(李白《山中問答》)之感!
二、田園生活之美
林語堂說,中國有一種輕逸的、近乎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可以在他們那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里找到最好的論據。“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于明慧悟性上的達觀者。這種達觀產生寬宏的懷抱,能使人丟開功名利祿,樂天知命地過生活。”
的確,曠懷達觀、陶情遣興的中國人創造出的生活方式,必定展現出浪漫高雅的東方情調,所謂琴棋書畫詩酒茶,呈現的是精致優雅、風格獨具的日常生活美學。“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灑掃庭院栽種花木,自給自足中盡享點滴之中的生活趣味。這趣味是“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在折露葵”(王維《積雨輞川莊作》)的清雅閑淡,是“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陸游《臨安春雨初霽》)的生意疏懶,是“野童扶醉舞,山鳥助酣歌”(孟浩然《夏日浮舟過陳大水亭》)的豪邁爽朗……當然,松葉釀酒,臨泉撫琴,田園詩歌描繪的與其說是難以效仿的生活最高典型,不如說是文人們借詩歌來表達他們對智慧藝術的生活方式的詩化向往。“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白居易《問劉十九》),屋外清寂無人大雪紛飛,室內爐火溫暖內心安寧;“水滿有時觀下鷺,草深無處不蛙鳴”(陸游《幽居初夏》),夏木陰陰草叢茂密,水漲河塘鷺鳥翔舞,詩人在蛙鳴聲中憑欄臨風,悠然自適。
還有一些田園詩歌截取恬靜真淳的生活畫面,描繪鄉村生活的返璞歸真,抒寫古老大地頗具傳統的民風民俗,表達詩人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由衷贊嘆。許多詩人干脆以農夫自居,陸游曾說“我是識字耕田夫”。他在《晚秋農家》中云:“我年近七十,與世長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衰業耕桑。身雜老農間,何能避風霜。”詩人不僅“身雜老農間”,以一個純粹的農民形象體驗著農民的生活,而且“與世長相忘”,以遠離塵世的淡泊情趣貼近農民的生活。而王駕“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社日》),描繪鵝湖山下稻粱豐收,農人家畜成群。夕陽西下,樹影漸長,春社歡宴散去,醉人在家人攙扶下愉快歸去。詩歌截取紅紅火火的農家生活畫面,表達了熱熱鬧鬧的民風民俗,飽含著詩人對田園生活濃濃的贊美和熱愛之情。endprint
三、田園耕作之美
悠久的農耕文明讓文人對田園有天然的靠近和熱愛,當仕途失意,田園便是他們逃離現實的避難所:“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讓陶淵明如釋重負;“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表達著陸游與田夫的親密無間;“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蘇軾《赤壁賦》),躬耕田居就是他們的生活實現和生命理想。
對普通勞動者的頌揚,是山水田園詩歌常見的感情審美主題。詩人用深情之筆,歌頌農忙時節農夫傾家而出,“農月無閑人,傾家事南畝”(王維《新晴野望》);贊美紡織婦女的勤勞,“五月雖熱麥風清,檐間索索繰車鳴”(王建《田家行》);還有農家姑娘的美麗嬌俏,“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陸游《岳池農家》);贊頌漁夫的雄健身姿,“老翁短楫去若飛,我欲從之已天際”(陸游《漁夫》);也描畫采蓮女的生動活潑和漁夫歸家的歡悅,“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王維《山居秋暝》);田家多淳樸熱情,率真純粹,“老農能共語,真率會人心”(陸游《雨后至近村》)。詩人這種對鄉野的濃濃熱愛和對農人的熱情贊頌,也體現了他們胸懷天下的人文精神,充溢著飽滿的愛和美。
詩人對農民辛勞耕作和苦難生活的悲憫同情是山水田園詩作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谷自生”(顏仁郁《農家》),天未破曉就得下田勞作,牛累得田中艱難徐行,老農又何嘗不是如此辛勞呢?可惜大家并不都能體恤同情農家之苦,不仍有人覺得谷物不過是田中自生嗎?即使辛勤勞作糧食豐收,依然入不敷出,只得艱難度日,“年豐米賤身獨饑,今朝得米無薪炊”(陸游《貧甚作短歌排悶》)。更有甚者,“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張籍《野老歌》)。農民們終年勞苦,但勞動果實卻被官府榨取了,而農民自己卻在挨餓。詩人在這樣的嚴酷現實里,表達著無力的吶喊控訴,抒發著對底層勞動者最真摯的憂心和深情。或許只有親歷農民的苦難,才能寫就這淚濕衣襟的愴然悲哀吧!
四、鄰友親善之美
雅友相交,是居于山林田園的文人理想。他們在幽靜閑然乃至窮鄉陋巷隱居而處,心中仍懷有“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贈孟浩然》)的交友志趣,所謂“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在詩人的視界,“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民諺)是田園生活中饒有意味的美學體驗。君子往來,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自由自得適意閑雅,一封“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問劉十九》)的邀約充滿古樸典雅的詩意情懷:暮色蒼茫,天將雨雪,能有友人前往共賞雪景共飲美酒,豈不快哉?友人相聚更是簡單生活里的重要精神寄托,“嘆息老來交舊盡,睡來誰供午甌茶”(陸游《幽居初夏》),表達出詩人濃濃的孤單虛空。而當有約未至,難免寂寞無聊賴中寥落悵然,所以才有“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趙師秀《約客》)的淡淡落寞、輕輕訴說。
當然,更多時候,詩人能感知的多是村夫野老的熱情好客和鄉野世間的淳樸民風。在“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蘇軾《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中左鄰右舍和睦相處,紛爭幾無。“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陸游《游山西村》)充分描繪了農人的好客豪爽。“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王維《終南別業》)則道出了詩人與鄉民相處融洽,談笑風生。當蘇軾被貶至惠州,“父老相攜迎此翁”,可以說,在惠州短短的兩年零七個月時間里,蘇東坡充分感受到了當地百姓的熱情,他們和諧與共,融為一體,正如他的《新年五首》言:“萬戶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他亦自豪地聲稱“杖履所及,雞犬相識”(《別王子直》),這份親善之美也因此讓他能夠在艱難的貶謫歲月得到些許安慰,他甚至說“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表示愿同野老一起過這種怡然自得的田園生活。
五、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很重要的主體思想就是“天人合一”。《莊子·齊物論》中曾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當西方人總是企圖以高度發展的人力征服自然、掠奪自然時,古老的東方智慧卻告誡我們,人類不過是天地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體。因此,天人調諧、“與自然無所違”便成了中華民族人生理想的集中體現。《呂氏春秋·應同》曰:“山云草莽,水云魚鱗,旱云煙火,雨云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自然固然有其變幻莫測的形態,但其實不過是天地大道示人之形,而人無論何其聰慧機敏,亦不過是茫茫寰宇之一種可能而已。這種天人合一思想體現在古典田園詩歌之中,便是萬物有靈、物我相通甚至相融兩忘的美思妙境。
古代文人們善于用欣悅多情的詩句展現著萬物的盎然生機和伶俐趣意,“浮云在空碧,往來議陰晴”(王質《山行即事》),碧空如洗,浮云繾綣,且晴且雨,生生不息;“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張養浩《雁兒落兼得勝令·退隱》),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溫馴的小鹿在青青綠草間踱步臥眠,敏捷的山猿與野花嬉戲愚頑。徜徉曼妙山水間,詩人們因此仿佛重新回到童年,贊嘆“鵲聲喧日出,鷗性狎波平”(王質《山行即事》)的熱鬧紛繁,更有“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兒竹馬嬉”(陸游《園中作》)的爛漫天性和純真童趣。
在或靜謐或熱鬧的自然之間,詩人們發現讀懂山水多情固然可喜,山水亦通曉人類悲欣交集豈不更是你我本屬自然之佳證?所以辛棄疾說,“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所以李白亦曾言,“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李白《獨坐敬亭山》)。在這里,自然并不僅僅只是作為審美客體被人類觀照賞讀,換個角度來看,人類作為自然之一種,又何嘗不是在山山水水的四時節令里綻放凋零?金圣嘆《魚庭聞貫》云:“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花到人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來。”人花兩看,花心似人心,一切景從此皆有情:“山色不言語,喚醒三日酲”(王質《山行即事》),“始憐幽竹西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縱使不言不語,但心神交匯情意相通,何處是你,何處為我?江山有待,花柳無私,人與自然相望相融,構成了中國古典山水田園詩卷獨特的審美意蘊。
追求人與自然的合二為一,是中國人的精神傳統。耳目的聲色愉悅固然令人歡欣,觀自然造化而悟天地之本質,從而有精神的超越與詩美的創造,或許,這才更是田園詩人們的生命理想吧。詩人們在對自然山水與田園生活的審美觀照中,既體驗生命的淡然,也體驗生命的樸質真淳。在這個意義上,正是既充滿人的生趣又具有靈的意蘊的中國山水自然才能孕育出山水田園牧歌的千古絕唱。
回望現實,工業化發展如火如荼的當下,學生居于都會流連于消費與娛樂的大時代中,遠離土地和勞動,對山水田園詩文的隔離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而城市文明無孔不入,鋼筋水泥的叢林熱鬧卻也單調,快節奏的生活里人們面臨的困惑和壓抑越發凸顯,山水田園卻能以博大的胸懷容納和收留,自然的四季輪回所昭示的生命真相仍能帶給人最大的心靈撫慰。無論春花燦爛,還是夏陽高照;無論秋葉靜美,還是冬日雪飄,無不洋溢著生命的情趣,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生命哲思。當為師者在課堂之上,與學生一起回望從前,品味著穿越千山萬水而來的詩歌盛筵,自會唇齒留香,精神愉悅,在美的情境里感受美,從而欣賞美、熱愛美,并實現美的創造和美的人生。
參考文獻:
[1]張圣華.蔡元培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
[2]林語堂.生活的藝術[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
[3]蔣勛.蔣勛說文學之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4]余恕誠.唐音宋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5]陳君慧.唐詩名篇鑒賞[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
[6]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7]胡經之.中國古典美學叢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8]俞育滋,張援.中國近代美育論文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編輯 高 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