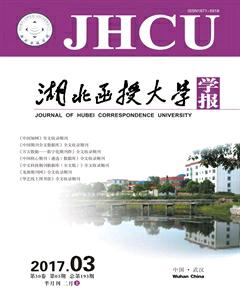文化之交融,譯者之創作
馬玉萍
[摘要]翻譯是語言再創造的過程也是文化傳播的一種方式。文化的異質性勢必會造成翻譯活動的不同。本文以《紅樓夢》的楊霍譯文為載體,比較分析二者在其翻譯中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力求從生態文化,宗教文化,文化意象以及譯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個角度探討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關鍵詞]《紅樓夢》;文化差異;翻譯;影響
一、引言
現如今,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呈現良好勢頭,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改革開放政策深入貫徹執行以來,文化的交流更是不斷加強,但是如何將中國文化走出去便成為了學術界人士日益關注的問題。作為軟實力的一種,名著翻譯成為弘揚本國文化的一種方式。但是,由于地域、歷史、思維方式的差異造成了文化的異質性,即文化差異。正是這種差異使翻譯活動出現了“文化缺失”“文化矛盾”等現象。基于這樣的現實情況,本文就以名著《紅樓夢》影響力最大的英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大衛·霍克斯所翻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楊憲益及其夫人的翻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為例,從中西文化差異為基點對譯文進行對比分析,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所采用的翻譯方法和策略,探究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二、文化差異與翻譯
所謂文化,不是民族在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氛圍,它是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內部共同特征,也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在生活與活動方式上的總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與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科技科學、宗教信仰以及法律體系都有密切的關聯。顧名思義,文化差異就是在文化方面所展現出的不同。具體而言就是由于不同地域人口生存環境的差異,而長期養成的習慣,處世態度、觀點信仰、宗教理念、思維方式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正因為如此,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在民族習慣和習俗上都表現出了較大的不同,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文化差異也就表現得非常明顯。
翻譯是一種最常見的文化傳播方式,也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傳遞行為,它主要是通過不同的行為規范,將語言進行轉換,利用不同的符號傳達相同的思想。翻譯的終極使命就是將文化從一種語境轉移到另一種語境,并保證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意思,不改變其中蘊含的道理,能夠讓別國的人們在自己的語境下進行全面的理解。所以,翻譯又可以被看作是連接兩種語言文化的橋梁,二者的關系密不可分。按照文化翻譯學的觀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管窺,翻譯則是文化與文化的對話,是譯者在不同規則的符號系統間進行信息傳遞的文化活動。歸根結底,翻譯就是從一種社會文化語境走出來再走進另一種社會文化語境的過程。表面上看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溝通,實質上則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融。故文化差異勢必對翻譯有一定的影響。
三、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具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史,在長期的積累和生活中保留著文化的精髓,語言特點非常鮮明,漢語也以婉約含蓄、簡潔明白為具體特征。《紅樓夢》作為我國四大名著之一,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更是有著濃郁的語體風格,再加上文化差異的影響,使得翻譯過程變得尤為復雜。直觀地了解了文化差異與翻譯的相關理論,有必要以《紅樓夢》的楊霍譯本為例,從中西文化差異的具體方面對翻譯的影響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加深文化差異對翻譯活動影響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欣賞作品內涵將原作的文化特征有效傳播。
(一)生態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地球之大,遍布各個國度甚至是同一國度的不同地域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各有特色,歸根究底是由人們所生存的環境所決定的。中英兩國生態環境的差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在翻譯活動中,這些差異也影響著譯文的表達。對比楊霍二人對中國名著《紅樓夢》的英譯文,明顯地看出中西生態文化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例:對立東風里,主人應解憐。(第十八回)
楊譯:Facing each other in the soft east wind!…
霍譯:Their mistress,standing in the soft summer breeze.…
原文中,“東風”一詞看似很普通的詞語,可是在中英兩位翻譯家的譯文中明顯看出,它的表達用語是不一樣的。楊譯文中,用了直譯法將其譯為“east wind”,而霍譯文中卻用了“summer breeze”。簡單的一個表示風向的詞語,中英兩位翻譯家的譯文差異競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只是中英兩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風向所代表的季節和風的特征就不同。中國位于北緯81度至南緯11度之間,北臨北冰洋、東臨太平洋、南臨印度洋,大陸性氣候特征顯著,季風氣候典型。所以,漢語中的“東風”代表春、夏季節從太平洋上吹來的溫暖而潮濕的氣流。然而,英國地處亞歐大陸的西端,西臨大西洋,東隔英吉利海峽,與歐洲大陸相望,因此源于墨西哥灣的熱帶暖流通過大西洋到達英國的西風溫暖宜人,而從西伯利亞刮過來的東風則比較寒冷。故在英國,“東風”卻指秋、冬季節從歐洲大陸吹來的寒風。在上面例句中,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因中國的生態環境特點忠實于原文采取直譯法,將“東風”譯為“east wind”,體現了譯者的主體性,對中國讀者來講,意義簡潔明了,可是對西方讀者來講會誤解其真正的意蘊。而霍克斯則考慮到讀者的感受把“東風”轉換成“slimmer breeze”。這種表達方式,即適合中國生態文化中東風代表春夏季節的意象,又表達了其的內涵特征“breeze”,不論是中國的讀者還是西方的讀者都會明白其內涵,沒有形成文化缺失與沖突。同時,地理位置的差異導致人們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的差異,這種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例: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第二十四回)
楊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 I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endprint
霍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can 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中英兩國地理位置的差異造成了兩國人民飲食習慣的不同。中華文明起源于中國古代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楊憲益先生祖籍是淮安盱眙(今屬江蘇省淮安市)屬于中國南方,人們以大米為主食,人們也經常用“魚米之鄉”來指物產豐富的地方,現代漢語中也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說。所以,對于土生土長在中國南方的楊憲益先生來說,大米是人們一日三餐中的主食,在他的譯文中“沒米的粥”當然就直譯為“a meal without rice”。相反,西方文明主要由游牧民族發展而來,游牧生活居無定所,自然就沒有固定的農耕收獲。所以,西方食物的來源主要來自于放牧的牛、馬以及獵物等,還有動物的奶類,即以肉、奶為食。英國是一個島國,海洋環境造就了人們不可能發展農業。所以,英國人食品的主食是牛奶、面包。生活在英國的霍克斯就是根據英國人的飲食習慣把“沒米的粥”轉換成“bread without flour”。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生態文化的差異影響著譯者的翻譯方法。
(二)宗教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語言與文化相輔相成,語言以文化為載體而文化又反映在語言的各個方面。從實質上來講,翻譯活動就是語言之間的一種轉換行為,也是不同文化問的轉換活動。《紅樓夢》是中國最有名的古典名著之一,其文化內涵博大精深,尤其涉及到的宗教文化耐人尋味。而宗教乃是社會文化和人類意識形態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是不同文化的表征。從某種意義上講,宗教文化貫穿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藝術、傳統習俗,又可稱為是一個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或行為準則,這種標準和準則影響著人們的意識形態。在對《紅樓夢》的翻譯中,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不同的譯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充分體現中西宗教文化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例:賈瑞一把抓住,連叫“菩薩救我”。(第十二回)
楊譯:…he seized hold of the Taoist and cried:“Save me,Bodhisattva!Save me!”
霍譯:“Holy one.Save me!”He cried out again and again.
“菩薩”全稱為“菩提薩倕”,梵語Bodhisattva,是典型的佛教用語。“菩提”本源于“菩提樹”因為佛祖就是在菩提樹下大徹大悟的,所以,“菩提”之意又為“覺”或“覺悟”;“薩倕”意為“有情”,有情是指有情愛與情性的生物。故菩薩便是覺而有情,顧名思義,就是要自覺地徹底覺悟并且要有情愛和情意,在佛教文化中國指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愚癡中解脫出來的人,也指信佛學佛之后發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這樣的人便叫做菩薩。在民間,人們通常把熱心腸的,能為眾人著想的,助人為樂的人成為“菩薩”。在上述的翻譯中,楊熟知中國宗教文化,使用直譯法,在譯文中運用“菩薩”的本源詞匯,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內涵,對于精通中國宗教文化的讀者來講,這種表達無疑是既遵循了“信”的翻譯標準有達到了“雅”的表達效果。可是霍譯中,卻將“菩薩”替換成基督教里指代的“上帝”將原文翻譯為“holy one”,“holy”意為神圣的;值得尊敬的;值得推崇的;圣潔的,圣徒般的;宗教的,霍譯文中,使用holy單詞完全是受其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故,不難看出,宗教文化差異影響著譯者的文化傾向和價值取向從而導致譯文表達的差異。
(三)文化意象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意象,顧名思義,是“意”和“象”的組合體。“象”者“物”也,“意”者“寓意”也,就是用物來表達語言的真正寓意。通俗地來講,就是用具體的東西來表現抽象的概念。其中,“象”是一種或多種能感觀感知的具體事物,而意則是一種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文化意象不斷出現在各民族的語言里,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符號,帶有豐富的寓意,深遠的聯想,以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向人們展示了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在翻譯過程中,如果對文化意象的差異處理不當,就會造成文化意象的錯位和丟失,產生誤譯。民族文化在意象上進行凝結,英語和漢語的適用人群不同,地域形成有別,文化意象的差異自然也就非常大。以《紅樓夢》楊霍譯本中譯文為例,即能明白這種差異之大,便能理解中西文化意象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作用。
例: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第三回)
楊譯:…“Dear heart!Flesh ofmy child!”she cried,…
霍譯:…“My pet!”and“My poor lamb!”burst into loud sobs.
漢語中,人們通常都說兒女是父母的心頭肉,也通常用“心肝寶貝”代指父母疼愛的子女。對原語中的“心肝兒肉”,楊氏采用直譯的方法完全忠實于原文將其譯為“Dear heat!Flesh of my child”,意在表達賈母對外孫女黛玉的疼愛之情,這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讀者來講,即可心領神會其中的奧妙,可以想象外祖母對外孫女的疼愛程度。而霍氏將之譯為“My pet”和“My poor lamb”。首先使用pet一詞,原意為寵物還指受寵的人,這里用它指代黛玉,表示黛玉就是賈母所寵愛的人。“lamb”本指羔羊,小羊,在圣經中是耶穌基督的象征,喻指溫順柔弱的人。霍克斯使用“poor”一詞來修飾lamb。首先,當時的林黛玉進賈府時母親已經去世,父親也離開了他,她是個孤女,顯得有些可憐,這符合poor的本意。但是,和lamb放在一起有表現出對其的疼愛,且說是意味深長,同時又體現出基督教文化對霍的影響,所以,使用lamb從多方面都體現出西方文化的特色,表達準確,意義深刻,便于西方讀者理解和接受原語的內涵與意蘊。
(四)文化背景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翻譯作為一種認知的再造過程,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偏差,翻譯者處于一個獨特的地位,當然會受到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的影響,楊霍二人的譯文之所以有差異,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中西文化差異的影響作用,而文化背景是造成中西文化差異最根本的因素。楊憲益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他的譯文作品則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多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運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希望將原著的意思完整的表達出來。戴衛·霍克斯雖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但英國的本土文化對他的影響根深蒂固,在《紅樓夢》翻譯上他受英國生態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社會文化的影響,多處運用意譯的翻譯方法,以讀者為翻譯的目標對象,以交際為主要目的,希望讀者與原作者產生共鳴,能夠實現同樣的讀書效果。
例: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第四回)
楊譯文:A confounded monk ends a confounded case.
霍譯文:And the bottle—gourd monk settles a protracted law suit.
“葫蘆”一詞看似很普通,但它的用意并非那么簡單,對其的理解決定著譯文的表達,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形成的譯文自然也就不同。霍譯文中,將“葫蘆僧”翻譯為“the bottle-gourd monk”這只是形象地描述了一下主體,而沒有將“葫蘆僧”的真正用意表達出來,也沒有將“葫蘆”之意體現出來,對原文內涵的表達出現了很大的缺失,信息傳遞有誤且使原語文化意蘊淡然無從。對不懂中國文化的讀者來講,對其的理解充其量也就是云里霧里直指其一而不知其二,沒有辦法領會原文的精髓。反之,楊譯文中,正是由于結合了中國文化的背景下,用到了“confounded(糊涂的)”一詞,意味深長,既說明了僧人的特點又說明了案件的實質,凸顯了原文內涵,結構簡潔明了,意義言簡意賅,便于讀者理解原文的真正意義和作者的目的。由此可見,譯者的文化背景差異同樣影響著翻譯活動。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依《紅樓夢》楊霍譯本為載體,從四個方面分析研究中西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我們不難看出翻譯活動受譯者所生活的生態環境,生活習俗,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制約。在翻譯過程中,翻譯者的文化傾向和價值取向還是有別的,譯者常常會發揮主觀能動性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深入研究兩種文化差異對翻譯活動的影響有助于彌補翻譯過程中的文化缺失,避免其差異造成的文化沖突,能最大程度的將原語信息傳達給讀者,更有助于中國文化有效走出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