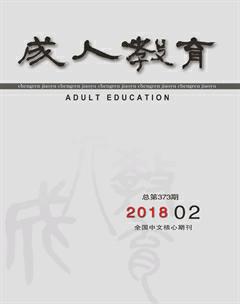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政策困境與政策選擇
【摘要】新生代農民工素質成為制約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障礙,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是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因素。我國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存在戶籍壁壘導致教育機會缺失,供求脫節導致職業教育市場結構性失衡,政策單一導致投入不足等政策困境。基于此,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應該建立以“稅籍與社保”為依據的教育權利分配政策;以“開源與增效”為核心的經費投入政策;以“針對性與實效性”為旨歸的教學治理政策。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政策優化
【中圖分類號】G7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794(2018)02006304
【收稿日期】20170413
【作者簡介】胡文燕(1981—),女,江蘇丹陽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在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及生產方式變革對勞動力提出了多樣化的新需求,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逐漸成為中國生產制造業一線工人,但是,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職業素質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2008年以來,我國先后出臺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等系列文件,要求多部門聯動采取針對性措施,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學歷層次、技術技能及文化素質,暢通其發展上升通道,而如何利用政策工具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的機會與質量是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加強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緊迫性
我國制造業正從“數量”向“質量”轉變,從“產品”向“品牌”跨越,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傳統產業結構向現代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即“迅速淘汰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向從事技術與知識密集型行業”。[1]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具有很強的緊迫性。同時,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一環,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可以實現農業、農村和農民協調發展。基于此,通過職業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的職業素質:一方面可以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技能,在市場導向的競爭就業機制中,增加自主擇業的籌碼,為以后立足城市奠定基礎;另一方面,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專業技能,既可以為城市創造財富,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發達地區帶動落后地區的橋梁。另外,《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引領城鎮化,用創新和改革促進農業和工業綠色、協調、統籌發展,實現工農共享發展成果。全面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激發農業、農村、農民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其中,農民是最具潛力的動能,且“農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2]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教育可以提升未來的市民素質與城鎮文明程度,為農民真正融入城市創造條件。
二、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政策的困境
由于歷史與制度原因,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問題長期被社會政策所限制或排斥。新世紀以后,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問題才被政策所關照,《2003—2010年全國農民培訓規劃》首次將農民工職業教育納入國家政策;2008年后進入政策密集期,國家投入力度以及各部委助力農民工職業教育的聯動機制得到加強;2011年后,新生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職業教育政策的重點,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在政策設計與政策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1戶籍壁壘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的機會不足
“分級辦學,屬地管理”是我國教育管理體制的基本特點,目前農民工職業教育政策也是在此基礎上構建的。“屬地”意味著制度設計是以戶籍和生源地為基礎,戶籍是教育資源的分配基本依據。這就使得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投入與教育需求發生錯位,相對于農村地區,城市的教育投入與教育質量更具有優勢,然而受戶籍限制,城市對農民工實際上是“經濟吸納,社會排斥”。以務工地政府財政支持的職業院校,多數拒絕為“外來人口”身份的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教育服務,盡管本地城市人口對職業院校存在偏見,而更加傾向于本科層次的高等教育,但“屬地化”的辦學體制導致城市不愿意將富余的職業教育資源與戶籍地以外的受教育者分享,大量有教育需求的新型職業農民被拒之門外。
新生代農民工是最具定居意愿的城市流動人口群體,但以戶籍制度和生源地為根據的教育制度設計,將新生代農民工置于城市的“邊緣”。他們試圖突破戶籍限制而融入城市,但是城市對他們設置了學歷、技能、經濟與房產等多種門檻;他們試圖通過教育來實現向城市流動,而戶籍制度又剝奪了他們接受城市職業教育的機會。他們只能徘徊在城市主流以外,從事技術含量低的體力勞動,社會地位低下,無法平等地享受社會文明的成果,在經濟分配中處于劣勢。因此,當前的農民工職業教育支持政策亟需突破戶籍制度的限制,特別要使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更加便捷地享受到職業教育的優惠資助政策。
2供求脫節導致農民工職業教育市場的結構性失衡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供求脫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我國教育體制造成的區域性供求失衡。由于職業教育權利被戶籍所限制,造成新生代農民工在務工的城市不能享受到職業教育優惠政策,而又因為外出務工在時間和空間上無法享受戶籍地的職業教育優惠政策,農民工也只能“望學興嘆”。如勞動力輸出大省湖南的職業院校招生數和在校生數分別從2010年的41.8萬與128.1萬,下降到2016年的36.7萬與104.6萬,而農村職業教育規模萎縮與生源困境更加明顯。[3]相反,深圳市工會的調查發現,2013年全市有新生代農民工51.2萬人左右,其中74.2%有學習專業技能知識的需求,而該市率先推行的“求學圓夢計劃”從2012—2016年的5年間,也僅僅幫助4 500名左右的農民工接受大專層次教育,9 300多名免費接受職業中專教育或職業技能培訓,供求矛盾十分突出。[4]endprint
二是職業教育內容與形式的供求失衡,這是指教育系統提供的職業教育或培訓在內容與形式上缺乏針對性,造成職業教育缺乏實效,農民工的參與積極性不高。如無錫市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中希望學習職業技能類課程的占87.5%,希望學習現代生活與休閑文化類課程的占50%左右,90%以上的人希望參加3—6個月的短期職業培訓,54.4%的人認為上班時間沖突與學校太遠影響了學習意愿。[5]但是,我國職業教育的專業課程過分偏重于學科取向,忽略了工作知識與技能,很難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需求。[6]
3政策單一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投入不足
充足的經費是農民工職業教育得以順利實施的基本條件,也是教育效益得以顯現的重要保障。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指導意見》中規定農民工培訓資金要列入省區、市財政預算,并鼓勵行業、企業積極參與新生代農民工培訓。國家建立了農民工培訓獎勵基金,由中央財政將培訓資金直接補貼用人單位;而納入省、市財政預算的資金是通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農村勞動力技能就業計劃”、“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星火科技培訓”、“全國貧困農民培訓轉移雨露計劃”等系列農民工培訓項目來落實的。
這種“項目式投入”方式是按培訓項目的不同類別分門別類設定投入資金額度,存在規模與資金投入偏小、區域投入差異大、區域選擇彈性大、個體投入剛性大等特點。但是,隨著新生代農民工人數的增多以及經濟轉型對技能要求的提升,中央和地方最初確定每年用于勞動力轉移培訓7億人民幣的金額早已難以為繼,加上項目管理過程中的“跑、冒、滴、漏”現象影響了培訓經費的使用效率。截止到2016年底,貴州省三都縣登記在冊的新生代農民工約2.9萬人,80%左右為初中文化程度,2016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安排培訓600名技工,但是,該縣獲得的上級和本縣財政費只有95萬元,人均約1 500元。[7]
企業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的重要承載者,本可以通過內部職業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價值而提升經濟效益,但農民工流動性較大,而政府又缺少相應的補貼政策,導致企業收益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參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積極性不高。2014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要求一般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1.5%—2.5%提取職工教育培訓經費,其中用于一線職工教育培訓的比例不低于60%;并鼓勵社會力量捐資、出資興辦職業教育,可是,這些政策都是鼓勵性政策而非強制性措施,沒有操作細則,政策效果難以顯現。
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政策的優化
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是新世紀出現的新問題,但根源卻在舊體制。該問題具有很強的復雜性,單一政策很難使問題得到持久而徹底的解決。因此,我們必須針對問題的根源形成有針對性的“政策組合拳”,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進行綜合改革。
1以“稅籍與社保”為依據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權利
目前,戶籍制度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的最大障礙,但是,戶籍制度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管理制度的核心之一,諸多的社會利益都依附戶籍而生,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想在短時期內完全消除既有的戶籍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化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入學障礙就必須在不改變既有戶籍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將相關利益從戶籍制度中剝離出來。近十年來,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等政策之所以沒有解決農民工的教育機會缺失問題,主要是政策立意更多地還停留在既有的戶籍制度框架內,以戶籍制度為紐帶的各項教育福利政策沒有得到修正或消弭。
在新形勢下,政府應該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貢獻程度或者納稅(社會保險)記錄頒發居住證,根據居住證讓其享有與城市戶口公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待遇。可以建立農民工“工作年限與職業教育資助”掛鉤政策,以納稅或社保記錄為識別依據,可以“先以工作年限換取教育資助”,也可以“先自費培訓,后用工作年限逐年返還”;也可以“用父母工作年限換取教育資助”,這樣不但可以充分釋放與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需求,還可以調動新生代農民工“流入地”舉辦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有利于形成靈活多樣的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體系,有效提升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
2以“開源與增效”為核心創新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投入政策
經費短缺是新型農民工培訓的瓶頸。盡管職業教育具有“公益性”與“私益性”雙重屬性,但是,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更具有“平民教育”或“窮人教育學”的性質,新生代農民工處于社會底層,很難獨立承擔相應的教育費用。因此,國家應該從教育公平與社會經濟發展角度擔當起農民工職業教育投入的主要責任,并在此前提下,按照“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建立政、工、校、企聯動工作機制,形成政府撥款、工會補貼、企業捐贈、金融機構捐資以及個人適當承擔等社會各界參與的多渠道、多元化共同分擔與投資機制。
各級政府應該根據人口測算數據與教育開支規模,將進城務工人員及其隨遷子女的職業技術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一種基本類型(而不是項目)進行財政預算與決算,并靈活調整財政支付方式。中央財政經費的撥付可以通過發放全國通用的“農民工職業教育券”的方式進行,以實名制按人頭等額發放,不允許轉讓或買賣,但是可以自主選擇教育消費地點與內容;地方政府的財政資助按照“工作年限”進行補助,既可以化解教育資助的戶籍壁壘,也可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投資積極性;可以將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總額提取的職工教育培訓經費中的一部分上繳財政,一部分也按照工作年限或工作表現直接發放給員工,自主選擇培訓;企業要保障工人帶薪參加職業教育的時間;政府可以通過稅收減免、低息或無息專項貸款等方式鼓勵個人或企業積極參與職業培訓;同時,應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endprint
3以“針對性與實效性”為旨歸加強我國職業學校的教學治理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主要價值體現在職業能力與文化素質的提升。但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屬于特殊群體,在參加職業教育過程中存在工學矛盾突出、專業與課程針對性差、教學模式不適應等問題,造成職業教育的實效性差強人意。因此,國家應該借助于一定的政策工具強化我國職業學校的教學治理,提升教育效益。
首先,政府要通過政策引導普通高校、職業院校、社會培訓機構、行業企業等開展校內外合作辦學,“把社會資源轉化為育人資源,使院校的單兵作戰轉為校內外多部門的聯動,理論與實踐、培養與需求對接,實現資源共享,合作共贏”。[8]“因校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在經費、師資、場地等方面予以專項支持,以此作為評價學校參與社會服務的一個維度;鼓勵學校差異化發展,可以根據周邊需求人才類型,發揮自身優勢自主開設新型專業、開展短期培訓或繼續教育;減少教育行政部門對職業學校辦學績效的直接評估,而是以“教育券”為主要中介進行“市場化”評估。
其次,政府要加強對職業院校教學模式的治理。在“指令性計劃”的招生模式下,一些職業院校對教學改革持消極無為的態度,不顧社會信息傳播環境的變化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學習特點,采用陳舊的教學模式,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政府可以通過實行“指令性計劃與市場性計劃”相結合的招生方式促使職業院校參與生源的市場競爭,倒逼教學改革;政府要對職業院校的信息化教學實行“競爭性的專項補助”政策,提高職業院校參與教學信息化改造的積極性。
第三,政府打造統一的農民工信息化學習平臺。在信息時代,職業教育應該乘互聯網的風口,建立新型網絡教學模式。政府要通過政策牽引職業院校利用互聯網的知識無限性和跨時空性,建立“送教進企業”和“學習不脫崗”的培訓模式,搭建面向農民工的優質網絡學習資源的公共服務平臺,如建設MOOC學習平臺等;建立基于智能手機的線上、線下教育相結合的學習模式;實行“網授與面授相結合、自主與協作相補充、理論與實踐相交替”的教學方式;實行學分累計制度,緩解農民工工學矛盾,達到“互聯網+職業教育培訓=工學不誤”的效果。
第四,政府要建立職業學校課程開發的支持政策。隨著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職業種類與職業要求的變化十分迅速,根據行業需要及時開發相應的課程成為職業教育與時俱進的客觀要求。但是,很多課程的開發是職業學校難以單獨完成的,需要通過政府整合資源,多個學校、多個部門及行業共同開發。因此,政府要擔當起相應責任,利用經濟杠桿或行政手段促進多部門的合作,共同開發滿足新生代農民工需求的課程資源,解決農民工學非所用、用無所學的技術困境。如2014—2015年,深圳市整合深圳市教科院、深圳市心理健康中心、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多個單位參與深圳市繼續教育學院的課程系列化開發與建設工作,開發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素質教育課程近60門、企業班組培訓模塊課程10門、心理健康教育課程8門、家政服務員系列課程12門,取得了良好效果。
【參考文獻】
[1]吳崇伯.論東盟國家的產業升級[J].亞太經濟,1988(1):26—30.
[2]張亞杭,李慧民.重慶高等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現狀及對策分析[J].重慶高教研究,2014(4):68—72.
[3]湖南中華職業教育社.湖南省職業教育發展簡況[EB/OL].http://zcc.gov.hnedu.cn/zyjyxchdz/.
[4]徐璐.問題與對策:對新生代農民工學歷繼續教育的思考[J].中國成人教育,2017(5):157—160.
[5]喬維德.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需求狀況的實證調查:以江蘇省無錫市為個案[J].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6):27—32.
[6]湯百智,湯棣華.基于工作過程取向的職業教育專業課程組織研究[J].職教論壇,2015(9):15—21.
[7]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2016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實施情況[EB/OL].http://www.sdx.gov.cn /html/article/323/ 14130.shtml.
[8]洪林,郭雷振.我國高校協同創新中心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構建探析[J].重慶高教研究,2016(1):72—75.
The Policy Dilemma and Cho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U Wenyan
(College of Media and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stacle for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ccup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work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also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new urbanization. At presen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exist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rriers lead to lack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in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arket, a single policy led to inadequate investment and other policy dilemmas. Therefo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tax registr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education rights allocation policy basis; set “broaden source and promote efficiency” policy input as the core budget and set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as the purpose of the government teaching policy.
【Key words】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ptimization
(編輯/徐楓)2018第2期(總第373期)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No.2 2018Total No.373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8.02.0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