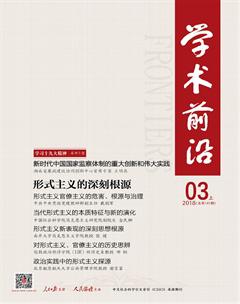新時代中國國家監察體制的重大創新和偉大實踐
王明高
【摘要】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傳承和發展,是對國外監察制度和反腐敗立法經驗教訓的總結,有利于破解自我監督難題,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形成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體制,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監察體制的建立,實現了黨的自我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黨內監督和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相結合,使黨內監督與國家監督、黨的紀律檢查與國家監察有機統一,是推進反腐敗斗爭法治化、制度化的治本之策,必將走出一條新時代中國國家監察體制之路。
【關鍵詞】國家監察體制 反腐倡廉 改革創新
【中圖分類號】 D6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5.010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把黨內監督同國家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貫通起來,增強監督合力。
3月11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專門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確立了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位。3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家監察法。這是新時代中國國家監察體制的一次重大創新和偉大實踐。
世界各國監察體制經驗和我國反腐倡廉歷程反復證明,科學的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是必然選擇。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推進反腐敗斗爭法治化、制度化的治本之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大舉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敗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意義重大而深遠。
對古今中外監察體制有益經驗的借鑒和總結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傳承和發展。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發軔于西周,確立于秦漢時期,至隋唐時期趨于完備,歷經多次變革延續至晚清,可謂源遠流長。秦朝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為了監督官員,秦始皇在中央設立監察機關,以御史大夫為首,下設御史中丞、侍御史或柱下御史,御史大夫負責監察文武百官,并輔佐丞相處理政務。西漢時期,御史大夫作為御史府的最高長官,領導機構成員監察中央官員,在地方設置刺史,負責監督地方官員。隋朝初年,為提升御史臺的地位,又重新設置了御史大夫一職,專掌糾察。到唐朝,御史臺從行政體系中獨立出來,作為獨立的監察機構,其下分別有臺院、殿院和察院,三者管轄范圍分明,形成了一個系統型、網絡型的監察體系。唐朝還制定了專門的監察法規《六察》和《風俗廉察四十八條》等,使我國的監察制度向著規范化、專門化的方向發展。宋代在唐朝監察制度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由御史臺和諫院共同組成監察機構,實行“臺諫合一”。到元朝,不再設置專門的諫官,而是由御史行使納諫的職責,真正實施了“臺諫合一”制度。明清時期,我國的監察制度達到鼎盛。明朝改御史臺為都察院,機構人數也空前增多,在中央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檢都御史,在地方設“六科給事中”,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還創造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類似今天的中央巡視。清朝為集中皇權,將“六科給事中”的相應職權歸附于都察院負責。作為“科道之官”的“六科給事中”和十五道監察御史,分別對內外官員進行糾察。《欽定臺規》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監察法規的優秀典范,標志著我國古代監察制度達到了鼎盛時期。
監察制度是我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對整肅綱紀、維護吏治、滌蕩政治污弊有著重要作用。自秦朝到清朝,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實行小官監督大官、以低品級官員監督高品級官員的法則,這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一大特點。
孫中山通過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經驗總結和西方監察體制的研究,提出了獨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的五權之一的監察權,由“監察院”行使對百官彈劾糾舉、監督的權力。歷史上的監察制度分言諫官和監察御史兩大系統,監察、獻納、封駁,涉及百官、政事,朝廷禮儀亦為其重要內容。而孫中山的監察思想重心在吏治和法律,出發點是人民,重點是監督人事和監督法律,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進步,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監察思想走向現代監察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對國外監察制度和反腐敗立法經驗教訓的總結。國際上公認的近代西方的監察制度誕生于1809年的瑞典王國,并逐步擴展到北歐地區,20世紀六七十年代迅速傳播至整個歐洲國家。1810年瑞典的《監察專員法》規定,監察的對象包括法官、檢察官、公立學校教師、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及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瑞典議會為增強監督力量,創設了議會監督專員的職務,并選擇“具有杰出法律才能和秉性正直的人士”擔任該職,負責監督中央行政機關,受理民眾的控訴。
英國是議會監察制度的代表國家,有著一套比較完整、靈活的監察制度。1967年,英國議會通過了《議會監察專員法例》,并正式成立了英國議會監察專員署。議會監察專員署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其職責是:受理公民投訴,監督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保證他們依法、合理地履行公務,防止其不當活動侵害公民的正當權益,保護因政府不當活動而受到侵害的公民。英國議會監察專員本身沒有獨立決定的權力,只限于調查下議院議員轉來的投訴案件。但是,它所監察的范圍卻很寬泛,包括對政府施政的監督,財政的監督、外交的監督,以及政府人事問題的監督等。
在美國,1978年《監察長法案》規定,監察長辦公室不干涉政府部門日常工作,主要工作是開展監督。監察長辦公室實行監審合一,既有審計職能,又有案件調查職能。審計依據國會審計辦公室制定的標準進行,主要包括財務審計、績效審計和對信息系統的審計,監控所在部門資金流向、防止浪費和內部網絡安全情況,發現苗頭性問題及時整改糾正,發現重大線索就與調查部門合作開展深入調查。
英國的行政監察專員履行公務時擁有調查、批評、建議、公開調查結果等權力。瑞士賦予了監察機關拘捕權、搜查權和公訴權。20世紀80年代,南美洲和亞太地區許多新興國家和地區在取得經濟發展奇跡和謀取政治轉型過程中,也建立了專門的監察制度。
世界各國監察制度的確立,既受到本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制約,也受到各國政治制度和施政理念的影響。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建立監察制度的初衷,往往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限制政府權力過度擴張;而新興發展中國家往往特別突出監察制度在反貪腐瀆職和保護人權中發揮的作用。國外監察制度的實踐經驗表明,無論是采取議會監察專員制,還是在行政系統設立監察機關,大凡要通過立法保障監察權的獨立行使,以全覆蓋監察對象,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在國外實行監察制度的國家,有一個顯著的成果就是:在操作公開和透明基礎上,通過制度建設鏟除滋生腐敗的體制性土壤,消除孕育腐敗的溫床,是反腐敗工作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瑞典、瑞士、新加坡等清廉國家的經驗無不說明了這點。這些科學的反腐制度主要包括:家庭財產申報制度、金融實名制度、遺產稅和贈與稅制度、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反腐敗國際合作制度五種。
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的規定在對公職人員行為進行規定與監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實名制度是家庭財產申報制的孿生兄弟,要求每一個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機構開設任何賬戶時都必須使用實名,所有的金融交易也必須使用實名并記錄在案。要發揮好前兩項制度的威力,還須有三項配套制度:即遺產稅和贈與稅制度、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反腐敗國際合作制度。
隨著腐敗犯罪越來越呈現出的組織化、跨國化的態勢,反腐敗國際合作成為世界各國反腐敗的必然選擇。為了加強國際合作,2003年10月,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目前,包括我國在內,全世界已有近百個國家批準了這個《公約》。《公約》是一項專門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件,在腐敗資產追回機制、外逃貪官刑事缺席審判機制、外逃貪官引渡機制、司法協助與執法合作機制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這對我國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對中央蘇區時期、延安時期和建國初期監察歷史的經驗總結。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決定了黨與腐敗水火不容。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監察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時期,隨著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央蘇區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工農民主政權的監察制度。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工農檢查處問題的決議案》;1933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蘇維埃政府的監察機構包括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農檢察部、控告局和各級檢舉委員會。中央政府設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省、縣、區三級設工農檢察部,城市設工農檢察科。1933年底,各級工農檢察部(或科)改設為工農檢察委員會,同時在鄉蘇維埃和市區蘇維埃也設置了這一機構。
延安時期實行的是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主要表現在陜甘寧邊區設立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以及縣區公署。當時的行政督察專員肩負著邊區政府監察、指導地方政府的職責。這種行政監察專員制度對于完善政府組織體系,提高行政效能,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
建國初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設立了人民檢察委員會,統一負責全國的監察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在縣、市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內,設立人民監察機關。”據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先后建立了監察機關。
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的重要探索
1945年7月15日,黃炎培先生在與毛澤東主席會談時,提出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問題。毛主席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正是關于跳出歷史周期率根本途徑的探索,對破解自我監督難題,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走長期執政之路,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方案時指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是國家監督制度的頂層設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戰略舉措,是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通過設立監察委員會,健全反腐敗體制機制,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另一方面通過加強反腐敗立法,包括修改憲法并制定國家監察法,確保監察權的獨立行使。
監察體制改革是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深刻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政治權力、政治體制、政治關系的重大調整。改革后,監察機構從行政系統中獨立出來,專司國家監察職責。從政治體制上看,監察委員會和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監察委員會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必將加強黨對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強化國家公權力機關的監督職能,拓寬人民行使監督權利的路徑。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實現監察體系全覆蓋的現實需要。在我們國家,80%的公務員,95%以上的領導干部都是共產黨員,在這樣的國情下,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既具有高度內在一致性,又具有高度互補性。在強化黨內監督,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同時,必須健全國家監察體系,不留任何監督空白,對黨內監督達不到的地方,或者不宜執行黨的紀律的公職人員,依法實施監察,才能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監察委員會實現了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監察法規定:監察對象包括各級公務員及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管理的人員;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受國家機關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集體事務管理的人員;其他依法履行公職的人員。中央紀委認為,試點確定的6類監察對象,目標清晰明確、全面具體,涵蓋了我國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操作性、權威性和震懾性。
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一體兩面,具有高度內在一致性。目前,黨內監督已實現全覆蓋,而現行的行政監察主要限于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二者不相匹配。國家監察是對公權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監督,國家監察體制全覆蓋和監督能力提高,直接關系到黨執政能力和治國理政的科學化水平。
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各級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中貪污賄賂、權力尋租、利益輸送等腐敗問題仍然大量存在,“小官大貪”、侵吞挪用、克扣搶占等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仍然禁而不止,嚴重離間黨群關系、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必須通過健全國家監督體制,把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納入監察范圍,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制約,才能實現標本兼治,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最大的現實意義在于,創造了一套適合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與黨長期執政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我監督模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是中國特色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既要加強自我監督,又要加強對國家機關的監督,不斷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
我們黨是一個有著8900多萬名黨員、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大黨,是一個領導著13億多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執政黨。要承擔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抵御各種風險挑戰,必須破解自我監督這一難題。國家監察本質上屬于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外部監督。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既是監察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式方法的與時俱進,又是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豐富發展,有利于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體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必將有效提升運用法律治理國家的能力,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進黨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走中國國家監察體制的治本之路
形成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體制。監察委員會是全新的反腐倡廉工作機構,它有效整合了檢察機關的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以及預防職務犯罪部門的職能,避免了國家反腐倡廉資源力量過于分散的問題,強化了黨對反腐斗爭的統一領導,形成了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倡廉體制。
在以往的反腐倡廉監督體系中,黨政系統設有紀檢機關,行政系統設有監察部門和預防腐敗部門,檢察系統設有反貪、反瀆職、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另外還有審計部門等專業性的監督機構,雖然紀檢機關和監察部門合署辦公,但反腐倡廉的各方力量和資源分散在不同領域、不同系統,且各部門各系統之間機構職能存在重合,職能銜接等方面難以達到統一指揮、有效配合,反腐倡廉工作效能大打折扣。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及預防職務犯罪等現有的反腐倡廉工作力量,收攏五指,攥緊拳頭,將從根本上改變過去多頭負責、資源分散、“九龍治水”的問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監察體制。
建立與司法執法部門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分析判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任務,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作出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使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使改革成果固化為法律制度,實現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強的制度保障。
修改后的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國家監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也就是說,一方面,為保證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同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在領導體制上與紀委的雙重領導體制高度一致。監察委員會在行使權限時,重要事項需經同級黨委批準;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領導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要對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另一方面,監察委員會由人大產生,就必然要對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并接受其監督。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把黨內監督同國家機關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貫通起來,增強了監督合力。
國家監察法賦予監察委員會監督、調查、處置的職責和談話、詢問、搜查、留置等12項調查手段。用留置代替“兩規”措施,將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法治難題,彰顯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和自信。在國家監察法中,對監察權行使的方式方法、審批程序、時限要求等作出嚴格限制,使監察權的運行更加公開透明。
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監察委員會成立后,對涉嫌職務犯罪的行為,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后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法院負責審判;對監察機關移送的案件,檢察機關經審查后認為需要補充核實的,應退回監察機關進行補充調查,必要時還可自行補充偵查。在憲法中對這種關系作出明確規定,是將客觀存在的工作關系制度化法律化,可確保監察權依法正確行使,并受到嚴格監督。在實際工作中,紀檢監察機關同執法部門也形成互相配合、制約的工作聯系。審計部門發現領導干部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線索,要按規定移送相關紀檢監察機關調查處置;紀檢監察機關提出采取技術調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的請求后,公安機關與相關部門要對適用對象、種類、期限、程序等進行嚴格審核并批準;在對生產安全責任事故的調查中,由安監、質檢、食藥監等部門同監察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實地調查取證,共同研究分析事故的性質和責任,確定責任追究的范圍和形式。
這樣,形成了監察機關與司法執法機關之間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有利于加強對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的監督,把監察權關進制度的籠子。
構建賦予憲法地位、法治化的國家監督體制。只有把制度變為法律,上升為國家意志,才能強化制度的權威性。在憲法中專門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確立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位,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使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于憲有據、監察法于憲有源,體現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必將為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奠定堅實憲法基礎,產生重大深遠影響。
國家監察法就是反腐敗國家立法,通過制定全新的《國家監察法》,取代《行政監察法》,對有關反腐敗的法律法規進行相應修改和有效整合,對監察制度進行徹底重構,以法律的形式將改革成果和反腐敗中取得的經驗固化,形成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根據憲法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必將進一步推進反腐敗工作規范化法治化。監察委員會并非政府職能部門,也非司法機關,而是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準確的法律定位應是監督機關。在國家機關序列中,監察委員會處于與一級政府和司法機關平行的地位,形成“一府一委兩院”的權力格局。在這一定位下,監察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獨立行使監察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以充分的權威性和獨立性保障監察效能的實現。
總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最大意義在于,實現了黨的自我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黨內監督和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相結合,使黨內監督與國家監督、黨的紀律檢查與國家監察有機統一,以黨內監督帶動和促進其他監督,建立更加科學、更加嚴密、更加有效的中國特色監督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倡廉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黨長期執政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就是權力腐蝕、脫離人民群眾,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在黨內監督已經實現全覆蓋的情況下,通過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把監察對象擴大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構建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使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有機統一,必將進一步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走出一條新時代中國國家監察體制的反腐倡廉之路。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形成反腐倡廉治本之策、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長效機制的思路與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6WTA11)
參考文獻
馬懷德,2016,《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和主要任務》,《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
肖培,2018,《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人民日報》,1月16日。
紀軒聞,2018,《以確立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為契機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3月12日。
蔡雅蕓,2017,《從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看現代監察》,《知與行》,第4期。
郭哲、王丹,2017,《司法體制改革下中歐監察制度之比較——以瑞典、法國、英國為樣本》,《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第11期。
紀亞光,2017,《我國國家行政監察制度的歷史演進》,《中國黨政干部論壇》,第2期。
責 編/鄭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