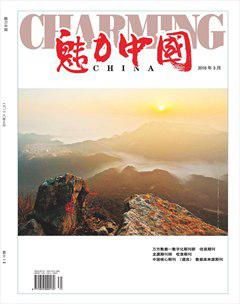藏族習慣法的傳承概況略談
摘要:藏族法文化肇始于久遠的原始時代,歷經上千年的歷史變遷仍然在藏區(qū)生機勃勃,其持續(xù)性和發(fā)展性可見一斑。在對在藏族習慣法的傳承過程中,四川藏區(qū)復雜的地理環(huán)境、獨特的經濟狀況、藏傳佛教教義以及藏民的文化傳統都為其提供了助力。由于特殊的經濟文化環(huán)境和藏族習慣法自身的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藏族傳統法文化生生不息的傳承下來。
關鍵詞:藏族;習慣法;傳承;藏傳佛教;載體
引言
藏區(qū)地處雪域高原,地形險峻,氣候復雜,自然災害頻發(fā)。藏民對大自然力量的不可探測逐漸轉變成為對大自然的臣服,這就形成了最初的“敬畏神山神水”的規(guī)則;藏傳佛教的傳播又掀起了藏民全民信教的熱潮,其“和諧”、“不殺生”的教義促使藏族糾紛和解制度的發(fā)展;歷朝的政治格局均未使習慣法湮滅,寬松的政策反而促進了習慣的傳承和更新,促使藏族習慣法有效傳承,歷久彌新。
一、藏族習慣法的萌芽:原始先民對自然的敬畏
藏區(qū)地處雪域高原,地形險峻,氣候復雜,惡劣的自然條件讓藏民的生存受到挑戰(zhàn),為應對自然的威脅,藏民必須團結起來共同生活和勞動,部落首領應運而生。藏族部落首領往往由德高望重、身份顯貴、博聞強識的長者擔任,是部落共同意志的體現。部落成員信服于部落首領的權威,遵循部落首領的自治管理指令,于是形成了藏族“遵守部落規(guī)則”的內部組織法則。同時對崇拜神靈、尊重自然的法則也開始萌芽,藏民在面對自然界無法探知的魔力時,其相對落后的認知水平讓藏民對自然界“敬而遠之”,并且創(chuàng)造一個“神靈世界”來解釋自然現象,原始藏民認為一切自然現象都是由“神靈”造成,神靈不可褻瀆,如果褻瀆神靈就受到懲罰,懲罰的方式則是受到自然的威脅。于是藏民選擇順從神諭,選擇崇拜自然,形成被動形成遵守“自然規(guī)則”的法則。
二、藏族習慣法的發(fā)展:藏傳佛教的盛行
進入封建農奴社會后,藏傳佛教教義豐富了藏族法文化中“平等”、“互助”、“互不侵犯”的內涵,全面信教為藏族法文化的傳承建立廣大的群眾基礎。
在吐蕃王朝政教合一、印度佛教興盛的社會背景下,藏傳佛教漸漸地成為了藏區(qū)民眾的信仰,藏傳佛教“不殺生”、“靈魂不滅”的教義對藏族刑事習慣法“賠命價”的形成功不可沒,“十善”、“五戒”、“因果循環(huán)”等教義促使藏民形成平等、自察、互助的處事理念和互不侵犯的法治規(guī)則,在豐富藏族習慣法內涵的同時,也促進藏族法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
三、歷史的見證:朝代更迭下藏族習慣法的傳承
元朝時期,政教合一的國家體制促進藏族“遵守規(guī)則”、“互不侵犯”等法制意識的強化。在政教合一的農奴制下,藏族民眾分為三個等級,藏民的地位因等級不同而不同,地位高的階層負責制定規(guī)則,發(fā)號施令,監(jiān)督規(guī)則的實施;地位低的階層負責遵守規(guī)則,踏實勞動。藏民違背規(guī)則會被買賣和殺戮,從而保障規(guī)則的運行,形成以“階層”為軸心的“金字塔”社會治理結構。同時同一階層間的數個部落由各自的部落首領統領,對內遵守首領的統率,共同生活和勞作,對外與其他部落友善互助、互不侵擾,形成以“首領”為中心的“同心圓”治理結構。藏區(qū)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治理模式和中國古代儒家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國家治理模式不謀而合,二者都起到了增強民眾“規(guī)則意識”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功用,安分守己、友鄰和諧、互不侵擾等習慣法規(guī)則的得以強化。
明清時期寬松的國家政策給了藏族習慣法生存空間。其一,中央政府允許土司按照舊制管理部落,不對藏族習慣法進行改革,這項舉措使得藏族法文化得以延續(xù)和傳承。其二,“改土歸流”政策未致力改革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給了藏族習慣法生存空間。“改土歸流”是指中央根據藏區(qū)各地殊異的具體情況派駐不同的官員來管轄藏區(qū)的措施,由于中央統治者的視角在如何集權、如何分配中央和藏區(qū)的權力上,所以“改土歸流”制度對于藏區(qū)生活、生產及解決民事糾紛的法則影響甚微,藏族習慣法依舊按照自己的路徑調整著部落間、部落內部的社會關系,“遵守規(guī)則”、“友鄰相助”、“崇拜自然”和“信仰神靈”等法則在寬松的政策下能夠找到生存空間,并且在改朝換代的動蕩中相對穩(wěn)定地傳承下去。
新中國成立后民主、科學的國家法律為藏族習慣法提供了傳承的可能性。新中國成立伊始,四川藏區(qū)與時俱進參與到了民主改革的浪潮中,首先,在管理民族事務上面,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為藏族習慣法提供了生存空間。國家法律明確賦予少數民族“當家做主”的權力,藏族可以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自覺管理藏族民族事務。國家法居于高屋建瓴的指導地位,藏族習慣法則嵌入單行條例和自治條例中蓬勃生長。
四、藏族習慣法能夠傳承還要依靠它自身根深蒂固的影響力
1950年國家頒布了《婚姻法》,《婚姻法》總則第二條規(guī)定:“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法》已經實行了68年,絕大多數家庭也已經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但有學者在對阿壩甘孜藏區(qū)的1000份走訪調研中,發(fā)現仍有大約39%的藏民認為“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婚姻形式“仍然存在”,18.7%的藏民認為“大量存在”,藏族“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觀念在藏民心中根深蒂固的程度可見一斑。藏族“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原本建立在匱乏的物質基礎上,而如今藏區(qū)經濟得以發(fā)展,農牧業(yè)產量大幅提高,藏區(qū)“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婚姻形式卻仍然大量存在,足以說明藏族習慣法文化在婚姻法和繼承法方面的生命力非常頑強,在藏民思想觀念的影響力根深蒂固。
結語
四川藏族習慣法是藏區(qū)的獨特文化符號,在歷史的流變中,這個符號沒有湮滅反而更加頑強,這不僅有賴于獨特的文化環(huán)境,還依靠其自身的合理性和藏民對它的使用和傳承。在國家法治建設大步邁進的今天,傳承藏族習慣法的腳步將會走的更加沉穩(wěn)。相信在現代法治的指引下,優(yōu)秀的藏族習慣法將會在四川藏區(qū)鮮活地傳承下去。
參考文獻:
[1]高其才:《當代中國民事習慣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吳大華、潘志成、王飛:《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通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版。
[3]隆英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藏族法律文化的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4]王堯.《走進藏傳佛教》.中華書局.2013年版。
作者簡介:彭清昀(1997年--),女,四川瀘州人,西華大學,本科在讀,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