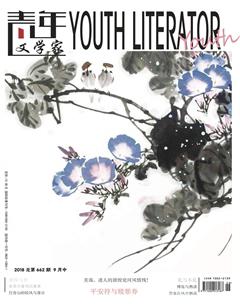莫言諾獎作品《蛙》的鄉土特色與世界氣派
摘 要:文化作品外譯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向世界,輸出中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方法和途徑。這項偉業,需要考慮四個問題:我們有什么樣的作品值得輸出;選擇誰作為譯者以搭建作者和讀者,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之間的挑梁;通過什么樣的渠道來出版發行;以及受眾的接受度和認可度如何。莫言的《蛙》深具鄉土特色與世界氣派,完全符合輸出的要求,因此我們以其為例,從文學作品翻譯的視角,進行前述問題的討論和研究。
關鍵詞:中國文化;外譯;《蛙》;文化輸出
作者簡介:曹娟(1978-),女,河南內鄉人,漢族,碩士,湖南工程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英語筆譯研究。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6-0-02
1、引言
2011年3月,日本文學名家諾獎獲得者在大江健三郎在莫言《蛙》日譯本封面上題詞:亞洲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人[1]。2012年10月,莫言身著燕尾服,一臉平和地登上了諾獎領獎臺,拿下了中國乃至儒學核心文化圈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成功,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界、文學研究與評論界特別是中國作品外譯研究領域的一件大事。有人將莫言的成功主要歸功于外譯,認為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不遺余力的譯介才是莫言通向諾獎之門的最主要原因,這顯然是本末倒置的皮相之說。然而,這種聲音卻從側面提出一個深刻的文學創作和文學作品的外譯命題暨:中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外譯工作如何才能夠取得成功?更進一步地,就是要反思:什么樣的中國文學經典才能為異域讀者所認可和接受?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文學作品的原創問題,翻譯問題,傳播問題和受眾問題。這四個問題構成了優秀文學作品外譯工作的四個關鍵環節,實際上也是支撐莫言成功登上諾獎舞臺的四梁八柱。應該說,莫言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在講的中國故事,也就是費孝通和矛盾所言的“鄉土特色”,這是中國作家特有的文化自覺:希望把中國的好故事講給世界上其他民族聽;但與此同時,莫言的作品里邊還充滿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式的魔幻主義色彩,有人把這種風格歸根到早莫言生四百年的中國民間學文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上——該書擅長以民間鬼怪志異為題材,骨子里普及的還是儒家“三綱五常”世俗化后的真善美品行——這顯然不符合實際:莫言絕大多數的文學作品是毫無顧忌、絲毫不見外地植根于中國現實土壤的,因為更多地以旁觀者的眼光來著筆,就未免顯得像某些文學批評家所質疑的“遺世而獨立”[2],但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有了更多的客觀性,并敢于關照現實。跳出了自身所屬的文化圈層和血肉相連母國故土,冷靜地講一個個發生在自己家鄉似乎與自己毫不相干而情節萬分離奇的故事,這向來是莫言的一貫風格。其氣度和格局也因此愈發的宏大起來,才具有了讓世界其他文化圈層的讀者都能夠認可和接受的世界氣派。
2、《蛙》的鄉土特色與世界氣派:暨原創問題與讀者問題
2.1鄉土特色與世界氣派:沖突與共生
《蛙》以中國計劃生育時代巨幅背景下鄉村醫生“姑姑”一生作為題材,講述了姑姑“萬心”從破除舊制用現代醫學方法接生的“送子觀音”到嚴格執行計劃生育千方百計讓不少孕婦終止妊娠和墮胎的“殺人惡魔”的轉變。成功塑造了一個現代科學的忠實信徒和體制政策的貫徹者的矛盾綜合體“姑姑”,是一個具有雙面人格的小說人物。在中國的語義中國,蛙通“娃”,也有“哇”(嬰兒啼哭)之意。有不少外國評論家以此認為莫寒是在抨擊中國計劃生育制度。但實際上,莫言在小說中是沒有出現過的,也就是價值中立,而隱藏在深處的并非是對計劃生育這一化解人口爆炸式增長給經濟社會造成的危險的中國制度,而是對生命繁殖和平等地生活的敬畏和由衷的佩服,因為“蛙”還有一層生物學意思,就是精子-蝌蚪-蛙的生長秩序,它是一種自然法則,莫言希望所有的發育成蝌蚪的精子都能夠有機會發育和成長為獨立的個體生命:蛙[3]。這就是他的鄉土特色,也是他包含心酸下對國人靈魂的痛擊,已經具備了人類命運通過體的思想境界:世界氣派。應該說,自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就開始了系統地對人權問題的反思和追求;而資產階級革命正式將宣言書變為行動派。如果說《獨立宣言》還僅僅是基于民族這樣一個人類的集合體來談論平權問題的話,那么《人權宣言》、《1787憲法》和《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以及國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真正地把人權的問題落實到生命個體的單個人身上。然而,正當全世界都在向著人權平權和個體選擇自由的康莊大道穩步前進的時候,中國卻一反常態以國家意識并具化為政治制度和社會風俗的方式來限制人口的增長,這雖然確有人口學家馬爾薩斯“兩個級數”的現實根基,但是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確然是以“公權干預(甚至是侵犯)私權”的事實。但莫言并未以此為切入點,像普通文人那樣地展開對現實制度的批判,而是站在更高的層次,在同情這一政策牢籠下的國人的無奈和心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莫言是從文學角度,給人口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提過醒,希冀他們能夠尋找到更好的“道”,來化解中國乃至世界人口增長給物質資料造成的巨大壓力[4]。
2.2莫言的鄉土特色與世界氣派提供了一種新寫作范式:中國的更是世界的
圈內流行的一句話是:文學家有國籍,但文學藝術沒有國際。中華文化曾經輝煌燦爛光照四鄰過,那時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圈層內,流行一種文化傳播的形式叫:東學西漸。那個時候,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中,我們立足文化高位,兼收并蓄,吐故納新,華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輻射世界。但近代以來,固守封建舊制的傳統文化的忠實擁鼎者們抱殘守缺,最終連帶政治、經濟全面落后世界潮流,文化自信全面喪失殆盡。短短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就敗光了古代中國的文化精英們苦心精英起來的強勢文化地位,與此同時,國人開始喪失文化自信,全方位,大幅度地引進和吸收西方世界文學,連同其價值標準也不加區別和斟酌地全盤翻譯、吸收進來,這個過程始于林魏時期,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停止,期間經歷大約一百七八十年的時間[5]。因此,直到現在我們討論翻譯的思維都還是基于“譯入”的,這就出現了認識論上的誤區,連帶翻譯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也必然會被禍及。經過一百多年的積累,在翻譯領域已經出現了“目的語讀者對中國文學的了解遠遠不如我們對他們的了解那么深刻”的現狀。因此,調整對外交流的文化勢位,轉變翻譯工作的理論根基,著手系統而全面地從“譯出”的視角來思考文化作品的翻譯問題。譯著必然要綜合考慮作者的寫作風格和本土特質,以及目的語也就是譯入地國家讀者所處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時代語境、民族審美等諸多因素。這便是要做到:文學作品是中國的,但更是世界的,講中國的故事,但是要讓全世界的人都讀得懂,這便是要有普世價值層面的東西。作者要有這樣的覺悟,譯者也必須要有這樣的功力,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討論譯者的問題[6]。
3、譯者的視角:誰來譯,兼論傳播渠道的構建
3.1外譯工作的“時間差”和“語言差”
這就是要討論和研究一個“時間差”和“語言差”的問題。毋庸置疑,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世界先進文化的譯介、吸收和采納是主動的、全面的、系統的、深刻的。而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認知還是從近十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繁榮、政治話語權的日益強大,國家軟實力爆炸式增長的背景下才被動開始的。而且他們主要是對了解和研究中國古文學,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接受就要少得多。我們花近一百八十年的時間去系統全面了解他們,而人家對我們的認識才剛剛開始,這就有了一個時間差的問題,時間差的出現,也必然有一個語言差的問題。不少應語言文化的國家的語言學家甚至感嘆: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對英語語法掌握的程度,都要遠遠地高于他們本國碩士研究生了[7]。換句話說,中國文化作品的世界化,可能要從語言關入手。但語言及其附著其上的文化的學習和掌握,非一日之功,因此短期內,我們還必須找到方法來搭建起中國經典作品和異域文化讀者之間的橋梁,這就是譯者的選擇問題。
3.2譯者的選擇及出版渠道的優化選擇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在“從莫言獲獎看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作家、譯家和評論家三家談”學術峰會(2012年,杭州)中國發表題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三點思考》一文中指出,“莫言的作品(如《蛙》)都是由外國著名的漢學家來譯的,如葛浩文和陳安娜等,因而其作品更加符合西方審美習慣;我國譯者雖然外語水平很高,但在把握語言的細微變化和整體審美方面與外國譯者還是有差距的” [8],其贊成以目的語所在國漢學家來譯的觀點不言而喻。雖則其立論有事后諸葛亮的學術投機的嫌疑,但是其邏輯理路是沒有問題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外國的軟件引入到中國來,必須要經歷過“漢化”的環節,而主要的操刀者必然是中國人一樣,聯結中國經典文化作品和外國讀者之間的最佳橋梁,也必須是最了解他們的人。從這里延展開區,我們實際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在華裔圈層中培育翻譯人才,其次中國國內的翻譯家強化對外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接受思維進行深入系統全面的了解后,也并非就不能進行本國作品的外譯工作,如費孝通和費正清就是中國通,他將美國的東西接受過來,我們就比較易于接受[9]。有了好的譯者,還必須要有優質的出版資源。事實證明,那些選擇了國內具有一定權威、地位和實力的出版社出版的《蛙》外譯本,其銷售情況和由此而應發的學術討論和學術評介的效果就要好得多。
4、結論
實際上,作者對譯者的態度、外譯的環境以及翻譯的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莫言成功。同其他作者和文學批評家相比,莫言對他的翻譯家的態度是友好的,如葛浩文就以“規化”的手法來對《蛙》做了語言風格、表達方式甚至內容架構的增刪改寫,而莫言對此表示,“自己不懂外語,譯者可以自主發揮”[10],這就大大地發揮了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因此直譯和雅譯之間,恐怕壓抑更能將《蛙》的鄉土特色展現到異國讀者的眼中。另外,中國文化走出國門,可能要作者立足自身文化場域,堅定不移的創造出具有本土特色和世界氣派的文學座屏來,同時建立外譯獎勵機制,鼓勵外國人來翻譯中國的經典文學作品。但要冷靜反思的問題是:當下中國,究竟有什么道德觀和文化價值觀值得我們不遺余力的輸出?若以昏昏使人昭昭,則不輸出也罷。
參考文獻:
[1]尹鈺瑩,韓笑,張琴.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研究綜述[J].濰坊學院學報,2018,18(01):12-17.
[2]劉文藝. 目的論視角下《蛙》日譯本文化負載詞翻譯研究[D].廣西大學,2017.
[3]苑亞楠. 翻譯補償策略下的《蛙》日文譯本研究[D].長春工業大學,2016.
[4]祝東江.從莫言獲獎看中國文學翻譯[J].文學教育(上),2015(01):101-103.
[5]于曉歡,黃周.莫言作品《蛙》日譯翻譯方法研究[J].華北科技學院學報,2014,11(11):108-112.
[6]鮑曉英. 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模式研究[D].上海外國語大學,2014.
[7]史成周.莫言獲諾獎對中華文化對外翻譯的啟示[J].海外英語,2013(21):180-181.
[8]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 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陳思和 教授. 從莫言獲獎看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N].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11-04(B02).
[9]綦亮.從翻譯到創作和評論都應多些文化自覺——“從莫言獲獎看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學術峰會述記[J].中國比較文學,2013(01):151-152.
[10]潘玥舟.從莫言獲獎看國家形象公關[J].國際公關,2012(06):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