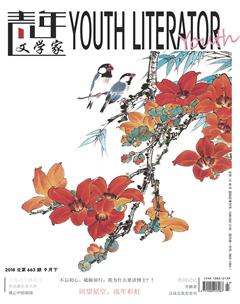回歸“吟詠情性”
摘 要:《詩辯》圍繞詩歌“吟詠情性”的本質特征,提出學詩應“以識為主”,要求學詩者通過熟讀前人佳作培養詩歌鑒賞力。同時希望學詩者在對歷代佳作的認真參讀中,把握古人的審美經驗和創作思路,從而建立起以“興趣”為最高目標的詩歌理想,創作出不著痕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優秀詩作。“識”(前提)、“妙悟”(方法)、“興趣”(理想)三者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學詩方略,嚴羽希望以此來扭轉江西詩派的不良詩風。
關鍵詞:識;妙悟;興趣;滄浪詩話;詩辯;嚴羽
作者簡介:張晟源(1994-),女,甘肅蘭州人,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方向:中國文化與文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7-0-02
《滄浪詩話·詩辯》中提出的學詩“以識為主”、“詩道亦在妙悟”和“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的說法,是理解嚴羽詩學觀的關鍵所在。本文試圖通過對《詩辨》文本的細讀,剖析“識”、“妙悟”和“興趣”,進一步探尋三者之間的潛在聯系,實現對嚴羽詩學觀的再認識。
一、“識”的內涵探析
“以識論詩”在古代典籍中是有蹤可循的。孔子要求弟子在學《詩》過程中要“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錢穆認為這里“識”的內涵有兩層:第一指積累關于自然的知識;第二指涵養性情:“孔子教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廣大其心,導達其仁。詩教本于性情,不徒務于多識。”[1]325換言之,“識”指的是在大自然中觀察和感受事物,為的是拓展胸懷、陶冶情操、揣摩天地之道,培養緣情寫物的詩性思維。嚴羽提出學詩“以識為主”,是對傳統詩論的重申,他還將養“識”的方法做了調整,認為學詩者只有以優秀詩篇為范本進行參讀,才能培養出高超的詩歌鑒賞力。
《詩辯》開篇以“入門須正,立志須高”[2]1規定了對“識”的要求,還列舉了與之相符的作品:《楚辭》、《古詩十九首》、樂府詩以及漢魏五言詩皆為古體詩,以韻律自然,感情古樸真淳見勝;盛唐時期李白、杜甫的詩歌,技巧漸漸成熟,但二人之作勝在情真意切,技法運用靈活自然。由此可知,嚴羽認為“高”“正”的作品,其共同特點是適情率意、自然淳樸。所謂“入門須正”即將抒情確立為詩歌的本質屬性,學詩者熟讀這些情感充沛、作法自然的作品,久之就能養成較高的詩歌素養和鑒賞力。嚴羽對詩歌資源的揀擇與他對詩歌本質的理解息息相關。“識”既是揀擇學詩資源必備的判斷力,有了好的判斷力,才能在豐富的歷代詩歌中選出真正的佳作進行學習;也是學詩者所要達到的學習目標,通過對優秀詩歌的反復參讀,進一步提升詩歌品味。
通過前人的優秀詩篇來培養“識”在嚴羽的時代是有共識的。嚴羽極力批評的江西詩派諸人也有相似的主張,黃庭堅在《大雅堂記》中說:“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3]927時人對“識”的重視也相當普遍,范溫在《潛溪詩眼》中明確提出:“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故學者要先以識為主,如禪家所謂正法眼者,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4]317 在這些相似主張中,嚴羽之論的特別處在于,他將抒情看作詩歌的唯一本質,并以此為出發點對前代的詩作進行了篩選,指出只有學習表情達意為主旨的典范作品,才能在個人的詩歌創作中走上正途。
二、“悟”的內涵探析
“悟”的本義指內心的感覺、知覺:“悟,覺也。……從心,吾聲。”[5]506后來逐漸延伸,指稱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主要見于道家思想中,指對難以言喻的“道”的把握和領會方法。“妙悟”兩字連用最早出現在僧肇《涅槃無名論》中:“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齊觀則彼之無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6]209這里“妙悟”指聰穎敏慧,善于感受和領會天地之道、成佛之方。
《詩辯》篇中,“悟”有“悟入”、“妙悟”等不同說法,它們的具體意義都不盡相同,根據具體語境對其進行梳理辨析,有助于從總體上把握“悟”的豐富含義。“悟入”本是佛家術語,指的是“領會并證入實相之理”。[7]243《詩辯》中則指學詩者熟讀古人佳作,有了相當積淀后,能夠把握古人作詩的要領和思路,達到開悟的境界。黃保真認為,“悟入”是“‘妙悟這種純審美的把握方式在‘學詩階段的表現形態。它是以純審美的態度去體悟前人佳作中的審美規律、思維方式,進而把它變為自己的審美方式,思維方式的過程。”[7]246佛家所謂“妙悟”是指“對禪道即本有的佛性的覺悟。”[8]28在論詩時,“妙悟”便是領會詩歌本質的最高法門。“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2]12他舉出韓愈、孟浩然的例子對“妙悟”之重要性加以解釋,劉辰翁點評此處說:“浩然不刻畫、只似乘興,滄浪謂浩然一味妙悟,皆得之矣”[2]15,可知“妙悟”是指詩人興之所至,感情流露自然的詩歌創作方式,這要求詩人有較強的審美感受力和高超的語言文字技巧,能夠將內心獨特的審美感受以自然、恰當的語言表達出來,完滿地實現創作對象、內心感受、語言文字之間的融會貫通,最后呈現出自然流出、不著痕跡的詩歌作品。
嚴羽認為最上乘的是漢魏詩歌“不假悟”的境界,自然感發而作,對技巧的雕琢少,最契合詩歌的抒情本質。“悟”則分為“透徹之悟”、“分限之悟”、“一知半解之悟”。最高者為,達到“透徹之悟”的是從謝靈運到盛唐時期的詩歌。許學夷說:“領會神情,不仿形跡,故忽然而來,渾然而就,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弈,公孫之劍舞,此方是透徹之悟也。”[2]16可見,“透徹之悟”也是指詩歌不著痕跡,渾然天成。“妙悟”指詩歌的創作方法,“透徹之悟”是對詩歌作品的鑒賞評價之語。陳伯海認為:“‘不假悟指的是直寫胸臆,發自天然,‘透徹之悟則是指有意識地追求藝術上的高妙,由人工而進入化境”[9]241,將“不假悟”與“透徹之悟”進行了到位的區分。而“分限之悟”、“一知半解之悟”則是尚未達到理想境界的不同階段的“悟”。
“悟”是針對詩歌創作方法而言的,指詩人能根據不同的審美體驗,找到與之契合的表達方式,用恰當的語言文字將其呈現出來,達到一種言意合一的狀態。漢魏詩不依托技巧而渾然天成,盛唐詩有法可循卻不露痕跡,正是“悟”的極致。“妙悟”說仍然圍繞著詩歌是性情所至的產物展開。
三、“興趣”的內涵探析
對“興趣”之“興”的解釋學界有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興趣”之“興”即指比興的表現手法,東漢鄭玄將其解釋為“托事于物也”。 [10]796也有學者認為,“興”是指感興,即“創作過程中情感的興起及創作沖動的產生。”[8]158二者都是圍繞著詩人主觀情感與客觀世界之間的聯系解釋“興”的內涵,分歧在于,到底是詩人先有了某種情志,然后借恰當的物象興寄成詩;還是詩人先看到了某種物象,由此觸發情感而成詩。這引起了“興趣”的兩層不同含義:一是指詩歌具有含蓄蘊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二是指詩人在外物感觸下產生的審美體驗在詩歌中的表現。二者都是對詩人主觀情感與客觀世界之間的關聯的描述。這說明,詩歌的產生與詩人和客觀世界的交流是密切相關的,好的詩歌能夠呈現出詩人內心感受與客觀物象之間的溝通聯系,也就是“興趣”的體現。
嚴羽對何為“興趣”也做了解釋:“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2]26“興趣”就是讀者在詩歌中看不到詩人對意境的刻意營造、對詞句的精心雕琢,仿佛渾然天成之作。嚴羽用幾個佛家典故進一步解釋“無跡可求”那種似實而虛、似虛而實的特點,這種特點為讀者提供更多自由想象的空間,讓詩歌達到了回味無窮的表達效果。可見,“興趣”就是指詩人將自己對世界的感受或體悟,通過創設情境的方式呈現出來,不著痕跡地表達內心情思。同時觸發讀者,使讀者在詩人營造的意境中產生屬于自己的情感意緒。于是,詩歌就不僅限于傳達作者的所感所想,而且還是一個觸發讀者的契機,使讀者也能參與到對客觀世界的體悟中。在這個過程中詩歌也因不同讀者的個性化解讀,具有了無限豐富的旨趣和意味。無論作者有意識地選擇物象運用比興手法,還是無意間受到感觸而產生的審美體驗。只要詩作含蓄蘊藉,具備“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都可以納進“興趣”的范疇。
嚴羽對“興趣”的闡述仍是以詩歌的抒情本質為中心的,如果說“識”和“妙悟”是學詩方法,那么“興趣”就是學詩者詩歌創作的目標和最高理想,也可以說是衡量詩歌價值的尺度。
有學者認為,《詩辯》中“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2]26的觀點,與前文強調“識”、“悟”,要求學詩者熟讀前人佳作是矛盾的。其實,強調學識積累和審美判斷力的提高是為了培養學詩者的詩歌品味,建立以抒情為本質的詩歌觀念,并不是說學詩與不需要讀書學習。嚴羽如此重視學詩者在入門階段的詩學觀之確立,是為了矯正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2]26的詩歌風氣。自《詩》《騷》以來,詩歌一直都是表現詩人情感意志的文學體裁,如果將文字、議論和才學引入詩歌,難免使詩歌緣情的本質遭到侵蝕和破壞,甚至會混淆詩歌與其他體裁間的界限。江西詩派注重師承前人用意和技法的風氣不僅削弱了詩歌的創造力,而且忽視了詩歌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嚴羽是為了維護詩歌“言志”“緣情”的本質,而在此重申強調“吟詠情性”[2]26的詩學主張。
四、結語
《詩辨》圍繞著“吟詠情性”的詩歌本質觀,主張學詩者首先要以良好的詩歌鑒賞力——“識”為前提和基礎,揀擇前代以情志為本質的詩歌進行參讀,從而領會古人在詩歌創作中獲得審美經驗的方式及其創作思路,學詩者還要能樹立起以“興趣”為最高價值的詩歌理想,創作出“無跡可求”、意味深長的優秀詩篇。嚴羽希望通過學詩路徑的調整,對江西詩派刻板因襲傳統、脫離現實的詩風進行糾偏,最終使詩歌言志緣情的本質回歸。
參考文獻:
[1]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三聯書店,2002.
[2]嚴羽著,郭紹虞校釋. 滄浪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3]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4]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卷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僧肇著,張春波校釋.肇論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0.
[7]成復旺.中國美學范疇辭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7]
[8]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陳伯海.“妙悟”探源——讀<滄浪詩話>札記之二[J].社會科學戰線,1985(1):235-244.
[10]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