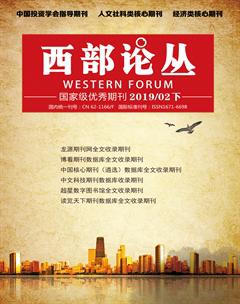城市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問(wèn)題探究
何泳璇
摘 要:居民作為社區(qū)治理參與的主體,在社區(qū)治理活動(dòng)中能夠發(fā)揮重要作用,本文從社區(qū)治理中居民參與概念的起源和發(fā)展出發(fā),以瀘州市江陽(yáng)區(qū)為樣本從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狀、意愿、動(dòng)機(jī)、內(nèi)容進(jìn)行調(diào)查,結(jié)合調(diào)查結(jié)果分析,發(fā)現(xiàn)現(xiàn)階段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存在自治意識(shí)薄弱、利益認(rèn)同缺失、人力資源匱乏三個(gè)主要問(wèn)題,本文針對(duì)性地提出解決對(duì)策,認(rèn)為需通過(guò)增強(qiáng)社區(qū)自治意識(shí)、提升社區(qū)治理能力、拓寬居民參與渠道以提升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積極性。
關(guān)鍵詞:居民參與 社區(qū)治理 調(diào)查分析
1、居民參與的起源與發(fā)展
“居民參與”源自于“公民參與”社會(huì)事務(wù)這一概念,是“公民參與”社會(huì)事務(wù)最微觀的表現(xiàn)形式。古希臘時(shí)期,雅典民主的理論與實(shí)踐被視為近現(xiàn)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從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末期開(kāi)始,公民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治理理論的產(chǎn)生與盛行共同推動(dòng)了全球性公民參與運(yùn)動(dòng)的不斷發(fā)展,民主和參與成為世界人民一致的呼聲,現(xiàn)代民主理論也演變成不同的觀點(diǎn)和流派。一是直接參與式民主,即公民應(yīng)該直接管理或者協(xié)商治理國(guó)家和社會(huì)事務(wù)。公民參與的理論先驅(qū)安斯坦(Sherry R.Arnstein)提出,“公民參與是一種公民權(quán)力的運(yùn)用,是一種權(quán)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經(jīng)濟(jì)等活動(dòng)中,無(wú)法掌握權(quán)力的民眾,其意見(jiàn)在未來(lái)能有計(jì)劃地被列入考慮。”[1]本杰明·巴伯提出的“公民是管理者,也是自治者、共治者與自己命運(yùn)的主宰者。”[2]二是間接參與式民主,即公民只需行使自己的投票權(quán)將管理的權(quán)力賦予代表他們的意愿人,讓更有能力的人管理社會(huì)事務(wù)。如密爾提出的代議制政府觀點(diǎn),“除公共事務(wù)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由所有的人來(lái)親自參與公共事務(wù)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就可得出結(jié)論說(shuō),一個(gè)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3]
從我國(guó)國(guó)情來(lái)看,居民直接參與社會(huì)事務(wù)的管理,更多體現(xiàn)在城市社區(qū)和農(nóng)村村社一級(jí)。2000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轉(zhuǎn)發(fā)了民政部《關(guān)于在全國(guó)推進(jìn)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的意見(jiàn)》,標(biāo)志著城市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有了上層綱領(lǐng),居民廣泛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和治理進(jìn)入新階段。當(dāng)前,我國(guó)對(duì)于城市社區(qū)治理的推動(dòng)近20年,政府仍然處于主導(dǎo)地位,許多社區(qū)的建設(shè)依舊沿襲著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時(shí)期的方式,尋求政府在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強(qiáng)調(diào)社區(qū)居委會(huì)為居民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務(wù)和社會(huì)保障,卻忽視了現(xiàn)代社區(qū)治理中的其他主體,尤其是居民對(duì)于社區(qū)事務(wù)的參與較為匱乏。因此,深入研究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治理中居民參與的實(shí)踐過(guò)程,客觀剖析在此進(jìn)程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wèn)題及原因,對(duì)激發(fā)社區(qū)居民參與熱情和提高其自治能力,推進(jìn)社區(qū)建設(shè)的和諧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2、以瀘州市江陽(yáng)區(qū)為樣本的調(diào)查情況
2.1調(diào)查方法及過(guò)程
本次調(diào)查的問(wèn)卷是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通過(guò)深度訪談社區(qū)居民和社區(qū)工作者,結(jié)合訪談過(guò)程中所發(fā)現(xiàn)的有效實(shí)現(xiàn)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衡量要素進(jìn)行整理,并對(duì)這些要素進(jìn)行剔除、篩選、整合、歸類,最終確定出能影響社區(qū)居民有效參與社區(qū)治理的衡量要素。
從以下三個(gè)方面內(nèi)容設(shè)計(jì)調(diào)查問(wèn)卷:第一,被調(diào)查居民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yè)、居住時(shí)間及月收入狀況等7個(gè)結(jié)構(gòu)性調(diào)查項(xiàng)目。第二,居民對(duì)當(dāng)前社區(qū)治理狀況的滿意度,主要從居住意愿、對(duì)當(dāng)前社區(qū)治安、鄰里、公共文化服務(wù)工作的評(píng)價(jià)來(lái)考察。第三,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狀,主要從居民的參與意愿、參與次數(shù)、參與內(nèi)容三個(gè)方面來(lái)考察。
調(diào)查采取問(wèn)卷調(diào)查和實(shí)地訪談結(jié)合的方式進(jìn)行,主要探訪地點(diǎn)在各社區(qū)的公共文化活動(dòng)中心、轄區(qū)內(nèi)商業(yè)區(qū)、小區(qū)物業(yè)辦公室。問(wèn)卷調(diào)查采用結(jié)構(gòu)化問(wèn)卷的形式,以四川省瀘州市江陽(yáng)區(qū)的所有城市居民為總樣本,從社區(qū)的所有社區(qū)居民中隨機(jī)選取一部分社區(qū)居民進(jìn)行問(wèn)卷調(diào)查,由被調(diào)查者自主填寫(xiě)。本次共發(fā)放調(diào)查問(wèn)卷180份,除去無(wú)效問(wèn)卷17份,最終獲得有效問(wèn)卷163份,回收率為90.6%。
2.2調(diào)查結(jié)果及分析:
2.2.1被調(diào)查居民的基本情況
被調(diào)查居民的基本信息表明,受訪者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居住時(shí)間、戶籍類型、收入情況等多個(gè)維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被調(diào)查對(duì)象與實(shí)際居民構(gòu)成較為一致。此外,因受訪者在社區(qū)居住年限3年以上的比例較高,此類人群對(duì)社區(qū)治理有更為深入和廣泛的了解,能夠保證本次調(diào)查的客觀性和有效性。
2.2.1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狀
本文通過(guò)對(duì)受訪者過(guò)去一年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次數(shù)進(jìn)行調(diào)查,進(jìn)而表征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實(shí)際參與度。
163名受訪者在過(guò)去一年參與社區(qū)治理事務(wù)0次的有102名,占樣本總數(shù)的62.58%,一年參與社區(qū)治理事務(wù)1-3次共有46名,占樣本總數(shù)的28.22%,超過(guò)90%的受訪者在過(guò)去一年參與社區(qū)治理事務(wù)的次數(shù)在3次以下。樣本數(shù)據(jù)表明,目前社區(qū)居民參加社區(qū)治理的參與頻率較低。
2.2.2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意愿
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意愿是指:居民參與社區(qū)相關(guān)事務(wù)及活動(dòng)的主動(dòng)性或能動(dòng)性。在一定程度上居民的參與意愿表達(dá)了其對(duì)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態(tài)度,它與居民的參與行為具有一致性,是居民主觀性參與的重要表現(xiàn)。
數(shù)據(jù)表明,占比74.24%的受訪者表示不同程度地贊同“社區(qū)居民應(yīng)該參與到社區(qū)治理”這一說(shuō)法;占比75.47%的受訪者表示認(rèn)為“參與社區(qū)治理可以營(yíng)造和諧共建的良好社區(qū)氛圍”;占比66.25%的受訪者認(rèn)同“社區(qū)組織很好的體現(xiàn)了居民自治”的觀點(diǎn)。結(jié)合訪談了解到,社區(qū)居民,特別是空閑時(shí)間較多的居民,大多有意愿參與到社區(qū)治理當(dāng)中去。因此,營(yíng)造和諧共建的良好社區(qū)氛圍可以通過(guò)居民參與的路徑實(shí)現(xiàn),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是現(xiàn)代公民自治的有效載體,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具備廣泛的自主意愿。
經(jīng)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個(gè)人事務(wù)繁多是影響居民積極參與社區(qū)治理的一個(gè)重要因素,科學(xué)規(guī)劃社區(qū)事務(wù)日程不失為增強(qiáng)居民參與的重要途徑;此外,如何廣泛激發(fā)居民積極參與社區(qū)共治也是一項(xiàng)重要課題。
2.2.3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內(nèi)容
依據(jù)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事務(wù)的內(nèi)容不同,將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分為社區(qū)政治事務(wù)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wù)參與、社區(qū)文化活動(dòng)參與。
社區(qū)中的政治事務(wù)參與是指社區(qū)居民關(guān)注和參與社區(qū)的政治事務(wù),譬如社區(qū)黨組、人大代表、居委換屆選舉、業(yè)主委員會(huì)代表的選舉、居民議事會(huì)等政治事務(wù)。居民參與的社區(qū)政治事務(wù)不僅決定了居民的社區(qū)地位,也深刻地影響著居民參與其他社區(qū)治理事務(wù)的動(dòng)機(jī)。一般認(rèn)為,參與社區(qū)政治事務(wù)是參與社區(qū)治理的高階表現(xiàn),是表征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深度的重要因素。34.97%的受訪者表示參與過(guò)社區(qū)議事會(huì)等會(huì)議;24.54%的受訪者表示參與過(guò)居委換屆、業(yè)主推選等選舉活動(dòng);此外,64.73%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不知道居民委員會(huì)的職能職責(zé),因此總體上講居民參與社區(qū)政治事務(wù)的比例相對(duì)較低,且居民對(duì)社區(qū)組織建設(shè)了解不多。
社區(qū)公共事務(wù)的參與主要表現(xiàn)為社區(qū)環(huán)境治理、治安維護(hù)等。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wù)是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中級(jí)階段,也是社區(qū)和諧穩(wěn)定的基礎(chǔ)。39.88%的受訪者表示曾參與過(guò)社區(qū)環(huán)境治理和治安維護(hù)等社區(qū)公共事務(wù)活動(dòng),通過(guò)與社區(qū)工作者訪談,我們了解到目前社區(qū)的環(huán)境治理和治安維護(hù)更多依賴于專業(yè)的隊(duì)伍,如新建商住社區(qū)的小區(qū)環(huán)境和治安管理主要依托專業(yè)物業(yè)管理團(tuán)隊(duì)進(jìn)行,社區(qū)居民參與率并不高。
社區(qū)文化活動(dòng)包括開(kāi)展文化娛樂(lè)活動(dòng)、營(yíng)造良好的公序良俗氛圍等,是增強(qiáng)社區(qū)凝聚力、提高居民歸屬感的最有效途徑之一。此類形式是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較為常見(jiàn)的形式,也可認(rèn)為是居民參與的低階形式。52.76%的受訪者參加過(guò)社區(qū)公共文化服務(wù),還有44.17%的受訪者表示參加過(guò)社區(qū)志愿者服務(wù),從樣本數(shù)據(jù)看,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文化活動(dòng)的參與度相對(duì)較高。
2.2.4研究結(jié)論
通過(guò)問(wèn)卷調(diào)查及實(shí)地訪談,我們可以看出,現(xiàn)階段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存在以下三個(gè)方面的問(wèn)題:
(一)自治意識(shí)薄弱。行為動(dòng)機(jī)社區(qū)居民對(duì)于自身應(yīng)積極參與社區(qū)共治這一理念較為認(rèn)同,總體參與意愿較高,但仍有部分居民持否定態(tài)度;特別是行為動(dòng)機(jī)上,相當(dāng)部分表現(xiàn)為從眾心理、被動(dòng)參與、“搭便車(chē)”心理等,居民的公共參與意識(shí)相對(duì)薄弱,歸屬感和認(rèn)同感缺乏。因而增強(qiáng)社區(qū)居民的集體行動(dòng)意識(shí),激發(fā)其社區(qū)共治的意愿顯得尤為重要。
(二)利益認(rèn)同缺失。社區(qū)居民在實(shí)際參與社區(qū)治理事務(wù)的行動(dòng)力較差,參與頻率較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與其自身利益關(guān)聯(lián)度較低。“沒(méi)有利益支撐的行為是不可能長(zhǎng)久的、穩(wěn)定的、持續(xù)的、理性的和有節(jié)制的。”[4]只有當(dāng)參與社區(qū)治理的行為與居民自身利益一致時(shí),參與行為才可能是持續(xù)的、自發(fā)的。因而可以引入一定的激勵(lì)機(jī)制、完善科學(xué)的組織方式、加大信息公開(kāi)力度有助于解決提升居民治理參與度。
(三)人力資源匱乏。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等級(jí)相對(duì)較低,居民的參與多集中于社區(qū)公共文化活動(dòng)、社區(qū)志愿者服務(wù)等較低等級(jí)的社區(qū)事務(wù),而參與政治事務(wù)、環(huán)境、治安等事務(wù)意愿較低。一方面,由于薪酬偏低、時(shí)間有限、沒(méi)有實(shí)質(zhì)決定權(quán)等因素,專業(yè)人員和管理人員參與社區(qū)治理的驅(qū)動(dòng)力不足,在對(duì)社會(huì)管理能力要求較高的組織建設(shè)、治安管理、環(huán)境維護(hù)等領(lǐng)域人力資源不足。另一方面,許多居民參與愿望強(qiáng)烈,但由于其能力有限,致使參與效率不甚理想。
3.提升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對(duì)策
3.1增強(qiáng)社區(qū)自治意識(shí)
政府應(yīng)合理界定自身職能與社區(qū)自治權(quán),探索完善社區(qū)組織制度,對(duì)于不屬于政府權(quán)限范圍內(nèi)的社區(qū)日常性事務(wù)交還給社區(qū),擴(kuò)展社區(qū)自治服務(wù)內(nèi)容,鼓勵(lì)居民參與社區(qū)管理并提供機(jī)會(huì),增強(qiáng)居民與社區(qū)之間的利益依存度。組織開(kāi)展多種多樣的宣傳活動(dòng),通過(guò)廣泛的宣傳從而凝聚共識(shí),形成共治共享的價(jià)值觀念,營(yíng)造良好的社區(qū)文化氛圍,激發(fā)居民自我服務(wù)、自我管理的創(chuàng)造力,從而增強(qiáng)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自治理念。
3.2 提升社區(qū)治理能力
加大社區(qū)教育和宣傳力度、通過(guò)普遍性、針對(duì)性的社區(qū)治理領(lǐng)域培訓(xùn),引導(dǎo)居民理解社區(qū)、支持社區(qū),提升居民個(gè)人素養(yǎng)和治理能力,為社區(qū)各項(xiàng)事業(yè)的完善發(fā)展提供人力支撐。同時(shí),加大社區(qū)組織人事制度改革,創(chuàng)新管理機(jī)制,健全激勵(lì)機(jī)制,通過(guò)科學(xué)設(shè)崗、按崗擇人,以崗定薪等方式,引進(jìn)專業(yè)化管理人才,增強(qiáng)社區(qū)治理隊(duì)伍的生機(jī)與活力。
3.3拓寬居民參與渠道
建立完善社區(qū)重大決策的預(yù)告制度和重大事項(xiàng)公示制度,通過(guò)各類渠道、各類方式向社區(qū)居民提供及時(shí)有效的信息,為居民廣泛參與社區(qū)治理打下基礎(chǔ)。在社區(qū)居民會(huì)議和居民協(xié)商議事會(huì)議制度的基礎(chǔ)上,探索健全民情懇談機(jī)制、社區(qū)聽(tīng)證、社區(qū)評(píng)議、樓長(zhǎng)議事制度等對(duì)話協(xié)商機(jī)制,對(duì)居民直接利益的重大問(wèn)題,應(yīng)廣泛征求意見(jiàn)、深入分析權(quán)衡,提升居民參與意愿和重大決策的科學(xué)性,從而推動(dòng)社區(qū)民主協(xié)商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5]
參考文獻(xiàn)
[1] Arnstein,Sherry R.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IP,Vol.35,No.4,July 1969,pp.216-224
[2] 本杰明·巴伯:《強(qiáng)勢(shì)民主》,彭斌、吳潤(rùn)洲譯,長(zhǎng)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990年版序言”,第7頁(yè)
[3] 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2年版,第三章第55頁(yè)
[4] 〔美〕戴維·波譜諾,《社會(huì)學(xué)》,李強(qiáng)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
[5] 李立國(guó). 在推進(jìn)社區(qū)治理中維護(hù)基層社會(huì)和諧穩(wěn)定[J]. 中國(guó)民政, 2014(2):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