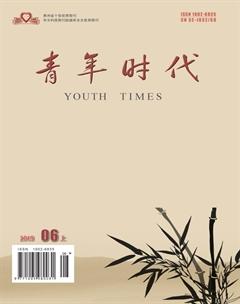淺析魯迅筆下的先驅(qū)者形象
陳悅
摘 要:過客是魯迅在《野草》中塑造的多個(gè)先驅(qū)者形象之一,從中可以看到先驅(qū)者面臨的世界和群眾,看到先驅(qū)者的形象和精神內(nèi)核,包括其生存狀態(tài)和心靈常態(tài)、復(fù)雜矛盾的情感、苦痛與執(zhí)著以及超強(qiáng)的行動(dòng)力。
關(guān)鍵詞:魯迅;先驅(qū)者;形象;《野草·過客》
一、先驅(qū)者面臨的世界
過客說:“回到那里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qū)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過客強(qiáng)烈的要向前走的意念以及對(duì)“回到那里去”的抗拒,折射出先驅(qū)者面臨的這個(gè)世界的面目。
過客所不愿去的世界,是一個(gè)“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的世界,是一個(gè)人們已失去了充分表達(dá)自我的意識(shí)和能力、被麻木和“中庸”所充斥的世界;是一個(gè)讓猛士“無所用其力”、遍布著“殺人不見血的武器”的世界。
過客所描述的世界是充滿壓迫、束縛、虛偽的,這種描述并非抽象,而是建立于先驅(qū)者和敵人、先驅(qū)者和群眾、先驅(qū)者和愛人這三種關(guān)系之上的。在這樣一個(gè)世界中,先驅(qū)者要迎接敵人的攻擊;要面對(duì)和啟蒙中庸麻木的群眾卻又常被群眾無視和傷害;彷徨孤寂、渴望溫情卻要冷靜對(duì)待愛。
二、先驅(qū)者面臨的群眾和孩子
《過客》中人物形象有三,分別是代表先驅(qū)者的過客、代表群眾的老翁和代表孩子的女孩。
一直呼喚著過客往前走的聲音也呼喚過老翁,但老翁卻是“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對(duì)此,過客表現(xiàn)出極大的驚異“哎哎,不理他……。(沉思,忽然吃驚,傾聽者)”。面對(duì)同樣的召喚,過客在思想掙扎后仍不畏艱苦往前走,老翁卻止步不前。面對(duì)通往墳的路途和艱難的過程,他們表現(xiàn)出不同的態(tài)度和行動(dòng)力,這是先驅(qū)者和群眾最大的區(qū)別。
《過客》全文沉重,但女孩這一形象給人清麗之感,表現(xiàn)出對(duì)孩子的熱愛。老翁說前面是墳,女孩卻說那有許多野百合;當(dāng)老翁讓過客把布掛在野薔薇上,女孩表現(xiàn)出極大的歡喜。女孩特有的審美行為體現(xiàn)出了其心靈與自然高度合一的境界。錢理群先生在《心靈的探尋》中也談到類似的問題:“魯迅博大的感情世界不僅超越了‘自我的狹窄范圍,甚至超越了國家、民族的狹窄范圍,升華到了自我心靈與宇宙萬物(生物,非生物)的契合。這樣的境界是兒童所有的,于是魯迅一再地為兒童的心靈世界辯護(hù)。”
群眾和孩子構(gòu)成了先驅(qū)者所面臨的世界的主體:于孩子,寄寓希望;于群眾,以合理的姿態(tài)面對(duì)。所謂合理的姿態(tài),即先驅(qū)者必須要深入群眾,并以一種真誠、平視的態(tài)度來啟蒙群眾。首先,先驅(qū)者要深入群眾而非脫離群眾。其次,先驅(qū)者不應(yīng)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來面對(duì)群眾,而應(yīng)真正與群眾站在同一戰(zhàn)線,不卑不亢地做群眾的事業(yè)。其間也包含著魯迅對(duì)待群眾的思想的一個(gè)重要轉(zhuǎn)變。魯迅在日本受到進(jìn)化論的洗禮之后,曾萌發(fā)出濃厚的啟蒙群眾的意識(shí),以一種啟蒙者高傲的姿態(tài)寫下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啟蒙情感強(qiáng)烈的文章,但經(jīng)過多次低谷后和打擊后,他說:“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dāng)作自己的嘍啰。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gè)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yè)。”如此,魯迅才真正將先驅(qū)者和群眾合二為一,協(xié)調(diào)了二者的關(guān)系。
三、先驅(qū)者
(一)先驅(qū)者的形象
在魯迅筆下,先驅(qū)者的外表往往是精瘦困頓而非肥頭大耳的,衣著往往是破舊而非光鮮亮麗的,正如過客狼狽、滄桑、疲憊、衰弱。其中或許包含了魯迅對(duì)先驅(qū)者形象的設(shè)想:真正憂國憂民、“橫眉冷對(duì)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與敵人戰(zhàn)斗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先驅(qū)者,必然是過客這樣的形象。《故事新編·理水》中禹的形象大致也是如此滄桑破敗,“一群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黝黑,衣服破舊”、“頭一個(gè)雖然面貌黑瘦,但從神情上,也就認(rèn)識(shí)他正是禹”。而在《彷徨·傷逝》中,子君在婚后的形象竟是“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此處用一個(gè)“胖”字表現(xiàn)出逐漸被生活侵蝕的感情的變化。由此可見魯迅對(duì)過客這一類先驅(qū)者形象設(shè)定的偏愛。
(二)先驅(qū)者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靈常態(tài)
《過客》一文展現(xiàn)出了先驅(qū)者的生存狀態(tài),即一直向前走。在這個(gè)過程中,先驅(qū)者心靈的常態(tài)是孤獨(dú)。
過客的狀態(tài)是“要走到一個(gè)地方去,接著就要走向那邊去,前面!”。這種一直向前走的狀態(tài),實(shí)際上是追求希望的過程。魯迅曾指出:“希望是附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這里的“存在”,我理解成一種實(shí)踐的狀態(tài),即過客一直在進(jìn)行著的“走”的狀態(tài)。亦如 “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shí)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走,是可以在無所希望中得救的有效途徑。
作為一名覺醒的知識(shí)分子,處于新舊社會(huì)的強(qiáng)烈變革中,魯迅得以汲取中華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優(yōu)秀文化的精華、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diǎn)上看這個(gè)世界。他超前于一般民眾和整個(gè)社會(huì)。因此,魯迅和同時(shí)代其他人的關(guān)系可以理解為先驅(qū)者和群眾的關(guān)系。
在這樣一種關(guān)系中,孤獨(dú)是魯迅心靈的常態(tài),正如過客所說:“從我還能記得的時(shí)候起,我就只一個(gè)人”。魯迅在《墳·文化偏至論》中更是引用了尼采《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話,直接點(diǎn)明孤獨(dú)狀態(tài),“吾行太遠(yuǎn),孑然失其侶,吾見放于父母之邦也。”但這并不說明魯迅就是一個(gè)向往孤獨(dú)、排斥喧鬧歡愉的人。他那絕大多數(shù)冷峻、犀利的文字中也不乏溫情的氣息。但孤獨(dú)與冰冷始終是魯迅的主觀選擇。錢理群在《心靈的探尋》中亦有相關(guān)論述:“盡管在魯迅的感情世界中,存在著‘熱與‘冷的矛盾對(duì)立;但是,魯迅的主觀選擇、歸趨,則無疑是‘冷。”
從《過客》和魯迅的其它文章中,可以看到“走”的生存狀態(tài)和始終站在群眾中間是導(dǎo)致魯迅孤獨(dú)的心靈常態(tài)的兩個(gè)重要條件。先驅(qū)者以“走”作為生存狀態(tài),但先驅(qū)者和群眾在向前走的意念和行動(dòng)力等方面又存在極大的裂隙和差異,因此先驅(qū)者會(huì)越走越遠(yuǎn),群眾卻停滯不前。先驅(qū)者是秉持一種要“打破鐵屋子”、啟蒙群眾的信念將“走”作為生存狀態(tài)的,但這種狀況下,當(dāng)感受到群眾的停滯不前甚至受到群眾的傷害時(shí),便會(huì)感到想?yún)群皡s不能的孤獨(dú)。這種孤獨(dú),便成了與其“走”的生存狀態(tài)相對(duì)應(yīng)的心靈常態(tài)。
(三)先驅(qū)者的情感
面對(duì)女孩的好意,過客是感激的,但最終還是“竭力站起”去拒絕。不敢接受布施之因,魯迅在此處竟用了“像兀鷹看見死尸”這樣夸張的比喻,可見其內(nèi)心情感的矛盾。
魯迅思想中的情感是復(fù)雜矛盾的:冷與熱、愛與憎、向往溫情與不愿被束縛……這與魯迅的人生經(jīng)歷有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少年時(shí)期家庭沒落,年幼的魯迅第一次嘗到世態(tài)炎涼,正是在生養(yǎng)他的故鄉(xiāng)。魯迅由于對(duì)母親的愛與順從而接受了一樁束縛自己多年的婚姻,這讓他對(duì)愛有所遲疑。魯迅盡力維持的家庭關(guān)系最后仍免不了破裂,對(duì)家庭的向往被重重潑了涼水,冷與熱再次在他心中激烈地斗爭(zhēng)。魯迅對(duì)青年寄寓極大的希望并且盡力啟蒙青年,但卻經(jīng)常受到傷害與背叛:他在紹興教書時(shí),就有學(xué)生借談學(xué)業(yè)到他房中騙煙抽,還回宿舍傳授經(jīng)驗(yàn),以至一些學(xué)生群起效尤;1928年,一位自稱姓黃的青年向他求詩,他認(rèn)真寫了四句寄去,不料過了一段時(shí)間,卻見一份官方色彩的雜志上登出這首詩,而且是用手跡制成封面,這才知道受了騙……魯迅曾全心全意、嘔心瀝血地去做啟蒙群眾的事業(yè),但卻遭到了《域外小說集》滯銷、袁世凱政府恐怖統(tǒng)治下不得已抄碑文、他人的文字討伐等等挫折。
這些“冷”逐漸消磨著他的“熱”,以致他在《野草·希望》中說:“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fù)和報(bào)仇。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shí)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由此,可以明晰魯迅情感的矛盾,明晰魯迅為何用夸張的筆墨來描寫過客面對(duì)好意的踟躕了。
(四)先驅(qū)者的苦痛與執(zhí)著
過客執(zhí)著地朝著墳的方向走,但這整個(gè)路途,都無疑是苦的,“我的腳早已經(jīng)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關(guān)于魯迅對(duì)苦的態(tài)度,錢理群曾在《心靈的探尋》中這樣談到:“‘人生苦的命題所表現(xiàn)的,是對(duì)于人性,人生,社會(huì)……不健全和痛苦的一種敏感(這不僅是魯迅?jìng)€(gè)人的心理素質(zhì)所致,更是近百年來中國民族多災(zāi)多難的歷史造成的),更是毫不退讓的徹底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過客無畏苦痛,執(zhí)著地向墳走去,正是先驅(qū)者專與苦痛搗亂的真實(shí)寫照。
(五)先驅(qū)者的行動(dòng)力
《過客》一文中,先驅(qū)者強(qiáng)大的行動(dòng)力體現(xiàn)在過客只知道前路是墳的情況下,仍然一直堅(jiān)持著往前走。這樣的一種行動(dòng)力,讓人仿佛看到了魯迅毫不停歇地工作著,仿佛聽到了他在《兩地書·二四》中對(duì)許廣平所說的“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而這種強(qiáng)大的行動(dòng)力,與先驅(qū)者啟蒙群眾、脫離“吃人、喝血”的世界的強(qiáng)烈意念息息相關(guān)。
先驅(qū)者強(qiáng)大的行動(dòng)力還體現(xiàn)在其即使是在最困頓的時(shí)候,也絕對(duì)不會(huì)以犧牲人民群眾為代價(jià)去追求任何東西。過客如是說:“可是我也不愿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bǔ)充我的血。”在當(dāng)時(shí)那個(gè)“吃人、喝血”的世界,即使免不了如《吶喊·狂人日記》所寫在“其中混了多年”,但是先驅(qū)者總是憑借著脫離這樣的世界的強(qiáng)大意念,勉勵(lì)催促著自我不斷前行。
強(qiáng)大的行動(dòng)力,貫穿著魯迅一生。魯迅在日本接受進(jìn)化論思想后,便懷著啟蒙青年的抱負(fù),做出了大量努力,正如王曉明在《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jìng)鳌分兴f:“他是自居為一個(gè)救國救民的啟蒙者,對(duì)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滿懷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嗇自己的嗓門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義情緒激越飛揚(yáng)。”。魯迅將進(jìn)化論當(dāng)作精神動(dòng)力,但他所看到的中國卻是退步的、與宣稱歷史必然進(jìn)步的進(jìn)化論不一致的,這讓他的精神支柱有所動(dòng)搖,加之經(jīng)歷了多次人生低谷,魯迅對(duì)自己的行動(dòng)也不免有所懷疑。但在這種情況下,魯迅仍然能以一種“中間物”的心態(tài)面對(duì)一切,他說:“當(dāng)開始改革文章的時(shí)候,有幾個(gè)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dāng)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也因此能夠重拾行動(dòng)的信心與動(dòng)力。此時(shí)的魯迅不再像年輕時(shí)空有一股熱情,對(duì)將來傾注所有的熱情和行動(dòng)力,而是在堅(jiān)持進(jìn)化論這一原則的基礎(chǔ)上,以一種“在天上看見深淵”的哲學(xué)視角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即看到將來的希望的同時(shí),也能洞悉將來的黑暗,能看到道路的艱辛。
強(qiáng)大的行動(dòng)力,正是《野草》精神的精髓所在:“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dāng)生存時(shí),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反抗只為了與黑暗搗亂,向前走只為了體現(xiàn)人追逐希望的狀態(tài),如此,即使前路茫茫,也都值得坦然,欣然,大笑,歌唱!
四、結(jié)語
雖然荊棘遍布路途,雖有老翁般將號(hào)召置之不理的絕大多數(shù)普通群眾,雖要在溫情與決絕中掙扎,雖每一步都消耗先驅(qū)者的血肉,但世界必須要有過客這樣的先驅(qū)者,才會(huì)有希望,正如野草“在旱干的沙漠中間,拼命伸長(zhǎng)他的根,戲曲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自然是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枯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shí)息肩之所。”這是野草精神中最動(dòng)人的地方,《過客》一文將其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參考文獻(xiàn):
[1]魯迅:《野草》[M],譯林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2]錢理群:《心靈的探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
[3]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jìng)鳌穂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4]魯迅:《吶喊》,《魯迅全集》第1卷[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版.
[5]魯迅:《而已集》,《魯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6]魯迅:《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7]魯迅:《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8]魯迅:《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10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9]魯迅:《故事新編》,《魯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10]魯迅:《彷徨》,《魯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11]魯迅:《墳》[M],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 2014年11月第1版.
[12]魯迅:《書信》,《魯迅全集》第11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13]魯迅:《兩地書·二四》,《魯迅全集》第11卷[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14][美]托馬斯·福斯特:《如何閱讀一本小說》[M],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