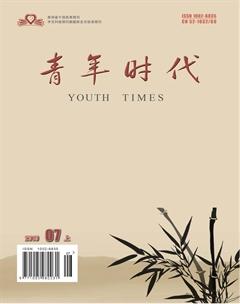精準扶貧視角下涼山彝族自發移民探析
崔玲 黎鵬
摘 要:涼山彝族自發移民呈現“鄉-鄉”鏈式遷移的特征,在城鄉融合背景下,其遷移具有必然性。相比于精準扶貧中的易地扶貧搬遷,彝族自發移民具有內在自主性和自謀生路的優勢。與第一書記稀釋基層治理自主權不同,經過遷移中不斷調試,建立移民社區共同體,具備更多自主權和治理能力。文章認為彝族自發移民行為對移民性扶貧具有借鑒意義,既有利于補足遷出地空心化、開拓市場和刺激產業發展,也有利于彝民的社會融入,建議遷入地政府做好公共服務,積極接納彝民。
關鍵詞:精準扶貧;彝族;自發移民
一、引言
習近平“我一直牽掛大涼山,牽掛彝族群眾”。四川涼山州是深度貧困區,僅涼山州有11個國家級貧困縣。根據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2014~2017年大小涼山彝區已完成8.5萬戶36.2萬人的減貧,但截止2017年底仍有11.2萬戶50.2萬人未脫貧,貧困發生率高達18.1%。有學者從涼山自然地理環境出發,提出移民扶貧的必然性,區別于“救濟式”扶貧與“開發式”扶貧。
馬戎在《人口遷移與族群交往:內蒙古赤峰調查》中,闡述“鄉-鄉”作為人口遷移的四種類型之一,是從農村向其他農村的遷移;不同于政策性移民,自發移民大多具有“鏈式遷移”(chain migration)的特征。涼山彝區自發移民呈現規模搬遷、集聚居住、自成村落的特點,與“浙江村人”相比,彝族自發移民較為關注在遷入地能否落戶。自歷朝以來,涼山彝區形同化外之邦,稱為“獨立倮倮”。受其影響,族際身份的差異在彝族遷移過程中彼此互動而得到再生產,如東莞彝族工頭及其社會功能以及家支的社會影響力。彝族自發移民與漢族農民工“鄉-城”遷移都屬于自發移民范疇,但也有不同:遷移方向不同,彝民主要是鄉-鄉遷移為主;遷移類型不同,彝民多以戶為單位、家支為紐帶的遷移;生計方式不同,彝民在遷入地以種植業與外出務工兩種生計方式交叉進行。本文將彝族自發移民的社會與精準扶貧的政策相結合,希望能探討自發移民對扶貧的積極意義,以期為民族地區的精準扶貧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文獻回顧
精準扶貧作為一項社會政策,事關國計民生而備受關注。學者們從政策研究上,分析我國貧困治理政策的歷史演進,總結扶貧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幫扶資源供給與需求的最優匹配問題,希望探討當前扶貧的創新路徑,如建構復合型扶貧治理體系、創新可持續發展支撐機制和實施“六個精準”。從精準扶貧對職業教育改革和農村貧困家庭人口結構的影響,與基層治理的理性關系、大數據的耦合性和公益組織的生態網絡構建。從主觀測量維度來看扶貧效果,李濤基于廣西民族地區的實證分析,提出政府承諾與政府信任對精準扶貧的人民獲得感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沈建勇等從實證檢驗海南精準扶貧提出生態保護和教育扶貧成效顯著;但黃強等認為生活水平對總體精準扶貧績效的貢獻最大。從扶貧方式出發,如產業精準扶貧作用機制、創新考評機制和旅游扶貧效益;從精準扶貧場域的現實困境中,提出政策瞄準偏差,出現精英捕獲現象,希望通過購買第三方服務來協助監督貧困識別中的惡意排斥和過失排斥。以往學者均從精準扶貧的不同視角進行研究,但都忽略了扶貧政策以外的移民性貧困。本文從精準扶貧背景下,深入分析涼山彝區自發移民對自主脫貧路徑的選擇及對策建議。
三、精準扶貧背景下彝族自發移民脫貧路徑
從長期性來看,精裝扶貧作為國家政策,代表國家力量的駐村第一書記深入到基層,短期內高規格高效率的調動基層資源,使扶貧能夠在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相反精準扶貧在基層的權力運作以第一書記為核心,從而也削弱了鄉村原來的基層治理能力,使基層治理的自主性進一步被稀釋,一旦第一書記完成精準扶貧任務離開鄉村之后,鄉村基層治理將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其扶貧成效從長遠看也難以得到鞏固。與“易地扶貧搬遷”不同,彝民不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具備自發性、自主性和自謀生路的特點,以脫離貧困為初衷,自愿選擇遠離家鄉尋求“小康”,帶有內在的積極性和開創性,值得鼓勵和推廣的。
彝民成規模卻不成體系的遷移,多向低壩河谷的小城鎮和大城市遷移,在遷入地原本存在人口密度過高、人均資源少、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的情況下,會不會加劇這樣的問題呢?孫立平分析了20世紀 90年代以后的中國社會,經歷了從資源擴散性到重新積聚的趨勢。隨著城鄉戶口制度的壁壘逐漸消失,人口的遷移多以自愿流動為主,資源在市場調節中逐漸趨利避害,彝民有選擇流動的權利,政府應做好公共服務,妥善接納彝民融入遷入地生活,使其逐步“文化化”,也利于民族融合。其次,城鄉差距逐步擴大和城市對鄉村資源的吸附效應,使邊遠地區進一步衰敗,迫使同胞們在農村經濟停滯中受害,為尋求出路而不得不搬遷,其行為不需要扶貧而是“自主脫貧”。再者,中國城市現代化較西方相比還遠遠不夠,彝民在遷移中超生現象普遍,以及“彝族老人抱怨自己長壽,最大的心愿是在不連累家庭的尊嚴中死去”,使人口結構年輕化和強大的家庭支持,對遷入地出現錯位替補的優勢。最后,一個國度的文明程度體現在人文關懷上,馬戎認為“在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良性發展的社會中,所有族群將分享經濟發展和國家強大所帶來的成果,盡管在各種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達到絕對均等,但在一定意義上,所有族群都將是這個博弈過程中的‘贏家”。
四、對策建議
彝族青年勞動力補足“空心化”的農村。大量彝族青年人在外出務工中接觸了新事物、體會了高品質的生活,產生了對相對發達地區生活的強烈向往,且比50-60歲的人群更有能力實現時空轉換,人口遷移對年齡的選擇規律依然會發揮作用,可見未來涼山彝族自發遷移仍以青壯年為主,很可能更加年輕化。隨著涼山彝族自發移民的主要遷入地(安寧河谷)越來越擁擠,同時,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空心化”問題突出的漢族農村地區也急需勞動力和利用閑置資源;并且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等政策的創新,也為自發移民進入更大范圍的漢族地區提供便利。
刺激遷入地經濟發展。彝族自發移民在定居前期,因生活不穩定和收入不高,對二手產品的需求會維持一段時間,促進遷入地二手物品市場的擴大和規范也使資源循環利用,如桌椅板凳、舊電瓶車等。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彝族自發移民通過網購,以避免面對面的漢語交流障礙,獲得生活必需品。自發移民的生活方式逐漸受遷入地居民的影響,刺激了對更多生活用品的需求,如受過教育的小孩帶動彝族家庭講衛生,購買廚具、餐具、洗漱用品等;自發移民邀請漢族工人修建、裝修房屋,配備廁所和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等。彝族自發移民通過購買生活用品和外出務工等方式刺激了遷入地經濟發展。
吸納彝民梯度發展生態養殖產業。自發移民具有高山環境的適應能力,加之擁有高山畜牧業的經驗,若能與本地漢族居民達成協議,承包山林,在低壩河谷地帶飼養家禽,半山或高山地帶畜牧牛羊等,可形成梯度發展生態養殖業。此外,還可發展生態養殖,將果業與養殖業結合,一方面牲畜糞便可以作為肥料養護桃林等,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山區山林資源,提高土地利用率。
參考文獻:
[1]Macdonald,J.S.and L.D.Macdonald,1964,”Chain Migration,Ethnic Neigh-borhood Form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XLII(1):82-97.
[2]項飆著.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444.
[3]李列著.民族想象與學術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
[4]劉東旭.中間人——東莞彝族工頭及其社會功能[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9(06):24-30.
[5]李鵾,葉興建.農村精準扶貧:理論基礎與實踐情勢探析——兼論復合型扶貧治理體系的建構[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5(02):26-33+54.
[6]何仁偉,李光勤,劉運偉,李立娜,方方.基于可持續生計的精準扶貧分析方法及應用研究——以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J].地理科學進展,2017,36(02):182-192.
[7]徐頑強,李敏.公益組織嵌入精準扶貧行動的生態網絡構建[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3):43-53.
[8]李濤,陶明浩,張競.精準扶貧中的人民獲得感:基于廣西民族地區的實證研究[J].管理學刊,2019,32(01):8-19.
[9]王嘉毅,封清云,張金.教育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J].教育研究,2016,37(07):12-21.
[10]黃強,劉濱,劉順伯.江西省精準扶貧績效評價體系構建及實證研究——基于AHP法[J].調研世界,2019(04):45-50.
[11]鄧維杰.精準扶貧的難點、對策與路徑選擇[J].農村經濟,2014(06):78-81.
[12]孫立平著.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13]馬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6):122-133.
[14]嘉日姆幾.試析涼山彝族傳統臨終關懷行為實踐[J].社會科學,2007(09):12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