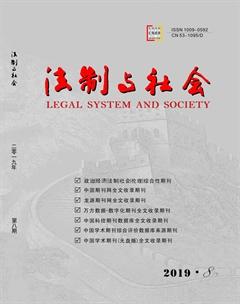《擔保法》若干問題分析
摘 要 《擔保法》是我國法律體系的核心構成,自施行以來在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面起到了較大作用。但《擔保法》于1995年開始實施,距今已有20余年,在此過程中,雖然推出了《擔保法司法解釋》等,但仍無法掩蓋《擔保法》自身暴露出的諸多不足。這些不足之處對《擔保法》在司法實踐中的效力造成較大影響。基于此,本文主要就《擔保法》存在的若干問題進行研究,旨在為找出其在新時代司法中的實踐方向及完善策略盡一份綿薄之力。
關鍵詞 《擔保法》 問題分析 法律體系
作者簡介:應朝陽,浙江六和(湖州)律師事務所,中級職稱,專職律師,研究方向:金融擔保、公司法。
中圖分類號:D923.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255
我國現行《擔保法》推行于1995年,距今已有20余年。在這20余年中,我國社會經濟、國民文化及整體國情均有不同,故《擔保法》出現問題是歷史必然。任何法律都具備時代性,不同時代對法律有著不同需求,而法律的制定又必然以當時國情為主,故在20余年后的今天,《擔保法》亟需完善。這既是時代發展的歷史必然,同樣也是司法實踐對現代法律的需求。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針對《擔保法》中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進行分析,并根據問題提出針對性完善建議。
一、現行《擔保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保證期間是否可以中斷
《擔保法》第25條對保證期間是否允許中斷作出明確規定,即“允許中斷”,但《擔保法解釋》第31條卻又提出保證期間不允許中斷。《擔保法》與《解釋》的自相矛盾與沖突使筆者產生了較大困惑,同時也造成了司法實踐過程中的分歧。對于這一問題,有國外學者提出保證期間只有在債權人提出訴訟或仲裁時才可以轉化為訴訟時效,該情形適用《擔保法》第25條規定保證期間允許中斷。但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這部分學者認為只有在一般保證的保證期間內,債權人對債務人采取法定的行使權利的措施時才會發生訴訟時效中斷的法律效果,訴訟時間在該情形下才能重新開始計算,因此中斷只能發生于一般保證期間,這與連帶責任保證存在較大差異。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持肯定態度,認為《擔保法》第25條規定的保證期間允許中斷具有法律效果,但要求保證期間本身處于特殊情況,只有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發生訴訟時效中斷。同時,這部分學者的關注重點在于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這同樣是一個問題。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保證期間是否能夠被中斷這一問題亟需解決。
(二)違反《公司法》規定的擔保合同效力認定
《公司法》第16條明確規定,企業向其他企業及投資者提供擔保時,必須嚴格按照公司章程規定進行,同時也明確規定擔保金額不得超過要求。有較多學者對該問題提出異議,這也促成了該規定在理論上與實踐上的不同解釋。對統一規定的不同解釋直接導致相同案件或相同性質的案件在對外擔保合同的認定效率上存在差異,這既是對司法裁判統一性的破壞,同時也是對司法權威的挑釁。因此,唯有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該規定才能真正適用于司法實踐之中。
目前,學界對于“對外擔保”的解釋主要有兩點:其一,公司進行對外擔保的必然前提是在法律上具備擔保資質。若公司不具備擔保資質,那么其無法為其他企業或投資者提供任何擔保服務。若公司具備擔保資質,在提供擔保服務之前也必須經過股東大會及董事會認可;其二,公司進行對外擔保必須具備一定資質,且同樣需要經過股東大會或董事會的認可才能決定擔保金額。目前學界的兩種觀點看似相似,但在本質上存在較大不同。在前者看來,擔保資質、股東大會及董事會是實施對外擔保的強制性規定,而后者則是強調對擔保的理性判斷。正是由于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故企業對于對外擔保合同的認定始終存在不一致現象。
(三)未得授權的分支機構是否具有擔保效力
《擔保法》明確規定:“分支機構在未獲得企業法人授權的情況下向他人提供擔保服務,則該服務合同無效。”具體而言,即指當分支機構在未得到企業法人授權之前并不具備提供擔保的資質,因此其無權以擔保人的身份作出任何決定,即便與其他債權人簽訂了擔保合同,法律也會判斷合同全部無效或超出權力之外部分無效。也就是說,唯有企業法人授權的機構才能進行擔保活動,否則一切行為均屬無效。
但在實踐中,經常發生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將名下房產用于抵押擔保。而《擔保法》并未就該現象作出明確解釋,導致司法實踐過程中難以對擔保合同的效力及房產處分權等內容進行有效認定。再加之《物權法》明確提出不承認無因性的房產變動行為,而抵押擔保合同的效力認定與當事人的利益有直接影響,對司法實踐造成較大困擾。在此情形下,若認定合同有效,則承認分支機構在未獲得企業法人授權的情況下也有權力對企業物資進行處理;若認定合同無效,則意味著分支機構需要承擔過失責任。
(四)《擔保法》是否適用于勞動合同
《擔保法》明確規定締約過失之債、契約之債、不當得利之債、無因管理之債、侵權之債等均可設定擔保,這不存在疑問之處。但問題在于勞動合同同樣可設定擔保。在此規定下,若勞動者在向企業提供勞動服務的過程中對企業造成經濟損失,導致企業財物受到損害,如勞動疏忽、以權謀私等。在該情形下,企業是否能夠按照《擔保法》要求勞動者擔保人負責?學界對該問題存在兩種說法:其一,在該情形中,擔保人的擔保對象所涉及的是經濟犯罪,不能以《擔保法》的民事規定對其進行判決;其二,既然有擔保合同,那么就應按照《擔保法》要求擔保人依法承擔責任。實際上,這兩種不同觀念產生于對《擔保法解釋》第一條的不同理解。
二、《擔保法》問題的完善建議
(一)關于保證期間是否可以中斷的建議
筆者認為,既然將保證期間自身視為特殊期間,那么問題的重點便不在于保證期間屬于除斥期間還是訴訟時效,目光應更多地集中于保證期間自身作為特殊期間所具備的特征。縱觀學界相關觀點,可以發現學者并未就保證期間這一特殊期間在法定事由出現時發生訴訟中斷法律效果的認知存在爭議,爭論的關鍵在于保證期間的性質。關于保證期間是否屬于訴訟時效,不能僅憑是否發生中斷就對其定性。要確保其保證期間發生中斷,必須先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發生法律明確規定的事由。《擔保法》第25條明確提出保證期間具有約定與法定兩種屬性,約定保證期間適用于法律效果未發生變化,法定保證期間則適用于訴訟時效中斷。其二,事由發生時間必須在保證期內。因此,對于保證期間是否可以中斷問題,筆者持肯定態度,即“可以中斷”。
(二)關于違反《公司法》規定的擔保合同效力認定的建議
違反《公司法》規定的擔保合同效力認定問題的產生源于學界對“對外擔保”的兩種不同認知:其一,公司在為其他企業及投資者提供擔保服務時,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分別為具備擔保資質、經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商討統一;其二,股東大會及董事會除了需要決定公司是否向他人提供擔保外,還需要討論擔保金額。兩種不同的觀點導致企業對于對外擔保合同的認定始終存在不一致現象。
對此,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較為相似,且由于后者在法律上更為嚴謹,適用性也更廣,故可將前者認定為無效觀點,或為其施加一個前提條件,例如在某一特定金額之下無需經過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投票決定。《合同法》第52條提出:“對于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應強行將其定性為無效合同”對于“強制性規定”的定義,《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指出:“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簡言之,即合同只有在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無效的情況下才能視為無效合同,反之則為有效合同。
(三)關于未得授權的分支機構是否具有擔保效力的建議
對于該問題,筆者認為分支機構若獲得企業法人授權,則其有權對相關產物進行抵押或他人提供抵押擔保服務。在該情形下,分支機構的一切權力都來源于企業法人,分支機構在其中扮演的不過是實施者。企業法人將房產登記在分支機構名下,則意味著分支機構具有該房產的處置權,包括使用、占有、處分、收益等。而分支機構將其用于第三方的抵押擔保則是對處分權的合法使用。因此,若認定分支機構無權將房產用于第三方抵押擔保,則違反了物權法。同時,物權法、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均未明確提出禁止分支機構在未獲得企業法人授權的情況下為第三方提供抵押擔保。因此,分支機構在未獲得法人授權的情況為第三方提供抵押擔保同樣屬于有效合同,只需其抵押權經過法定機關登記即可有效設立。
(四)關于《擔保法》是否適用于勞動合同的建議
對于該問題,筆者傾向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高延民擔保合同糾紛案”的處理方法。在該案件中,原告為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和平支行,被告為高延民。對于該案件的審理,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本案件中,擔保合同約定的是企業內部管理工作,而并非平等主體之間的債權債務。擔保的主要內容在于確保被擔保人在為企業提供勞動服務期間不做出導致企業利益受損的行為,而并非債務、債權。故《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相關規定不適用于本案件。由本合同引發的糾紛不在民事訴訟范圍之內。”簡言之,即“《擔保法》并不適用于勞動合同”。
筆者持該觀點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擔保的關鍵在于民事債權,而勞動合同的約定內容則為企業內部管理,并非債權,這與擔保法的原意相悖;第二,擔保法更多的趨向于財產、經濟,而勞動合同擔保則更多地趨向于人身隸屬關系,應由專門的勞動法律進行規范;第三,若《擔保法》適用于勞動合同且追求其刑事責任,則必須追繳財產返還給債權人。若以民事案件提出起訴而法院予以支持,則違反“一案兩立”司法原則。基于上述原因,筆者認為《擔保法》不應適用于勞動合同。
三、結語
《擔保法》作為我國法律體系的核心構成所在,對維護社會經濟平穩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畢竟其推行于1995年,囿于時代局限,《擔保法》已無法有效滿足當前所需。因此,針對《擔保法》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并提出完善建議已是迫在眉睫。對此,本文提出了現行《擔保法》中存在的四個主要問題,并就問題作出了針對性完善建議,期于能夠對《擔保法》的完善以及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一份貢獻。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作為法治社會、法治國家的根本核心所在,對其的任何修改、完善必然無法在朝夕之內完成,這有待于學者進行數代甚至數十代的研究方可,《擔保法》亦不例外。
參考文獻:
[1]Ghouri A A. Guaranteeing the guarantee law in Pakistan: the UNCITRAL Convention and the guarantee laws of Pakistan, the UK and the USA[J]. Commonwealth Law Bulletin, 2011, 35(4):659-674.
[2]王蓉.物權法與擔保法適用的時間效力研究[J].職工法律天地:下,2016(11):69-69.
[3]敖美玲.共同擔保中擔保人追償權制度研究[D].2016.
[4]黃云發.探討物權法與擔保法的沖突及適用范圍[J].長江叢刊,2016(21):170.
[5]李歡.獨立擔保法律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
[6]杜有梅.保證期間法律問題研究[D].黑龍江大學,2017.
[7]楊惠蘭.論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的適用關系[D].外交學院,2017.
[8]吳小青.關于收費權質押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17:134.
[9]俞悅,楊旭.海關監管權與民事擔保物權沖突問題研究[J].海關與經貿研究,2016(1):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