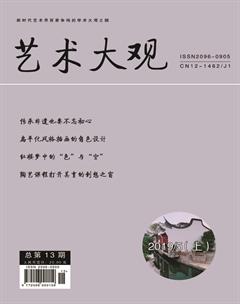從胡經之《文藝美學》中談對書法美學的思考
李洪生
摘要:美學是以人類審美活動的本質、特點和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問,它從屬于哲學范疇。美學所研究的對象并不是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而是情感的需求,審美的需要。將美學與書法相融合考慮書法問題,書法是一種以漢字為載體的藝術表現形式,需要在審美活動中將書寫者作為審美主體與客體產生相互作用,形成一種審美性關系。文章重點論述關于書法美學中內容與形式的問題,雖然前人也做出了諸多的分析,但都意見不一。鑒于此,我把書法的結構和形式美、文化的內涵與美學原理結合,重新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盡量更加接近古人對于書法美學的認識,除了形式美以外,也更加重視書寫文字內容所帶來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美學;書法;書法美學;審美
一、美學與書學的融合
文藝美學以文學藝術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書法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而存在。胡經之在《文藝美學》指出:如果說,哲學美學主要研究人類審美活動共有的普遍規律。那么文藝美學就應該著重研究藝術活動這一特殊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以及審美活動規律在藝術領域中的特殊表現。我們也可以體會到無論是真也好,善也好,要真正成為藝術的內容,都必須通過審美為中介;真、善經過審美之光的折射才能轉化為藝術的內容。《文藝美學》中說新批評派并不絕對否定文學的功能可以引起讀者的感情反應,但是認為作品本身并不表現感情。瑞恰茲認為:“詩歌語言不同于科學語言,它所運用的是感情性語言,而科學語言則是指稱性語言”。
書法與美學的融合,我們稱之為書法美學。書法美學思想是民族文化精神在書法上的表現。一部中國書法史就是一部字體、書體、書寫和書法美學思想形成的發展史。人們常說的“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就反映出不同時期的書法狀況和書法美學思想發展變化。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關于人類社會實踐的理論,人類的活動都是追求目的,掌握規律的,即總是自由自覺的活動”。所以說人類在創造文字的時候,是以實用性的目的為前提的。書法當中的文字特點不僅體現各個時代的審美,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美的認知和對文化的追求。
二、書法審美活動——審美主體與客體的對象性關系
胡經之在文中指出,審美,就其現實性而言,是主客體所建立的審美關系中審美主體的能動活動。在他看來,藝術審美活動的基本條件是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主體、客體缺一不可。審美活動作為人類審辨美丑、悲喜等這些審美對象的精神活動,乃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必然包含著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兩個方面。在審美活動中,第一個必要因素就是審美客體的存在。審美客體極為廣泛多樣,充盈于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第二個必要因素是審美主體的存在。審美主體是處在審美活動中的人,人也只有在審美活動中才可稱為審美主體。
那么,在書法美學中,我們可以將書寫者稱之為“審美主體”,書寫的字跡或書跡當作欣賞的對象或“審美客體”。書寫者應當具有敏銳的感知能力,能夠對客體對象審美特質做出特殊的反映。在書寫實踐活動中,“書寫”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的字跡或書跡。當代“中國書法史”的研究便是以此為研究對象:去考察這些字跡或書跡的點畫、結構等變化,研究其給人們帶來的視覺審美特質,從而肯定其藝術特質。但同時,書法作為我國的一種獨特的“線的藝術”,它兼備具象和表現兩種功能。人們稱其“無色而具備畫圖的燦爛,無聲而具有聲樂的和諧”。
(一)作為審美對象的書法作品,它表現書寫者(書家)內心情感和思想的表達。漢代蔡邕在《筆論》中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豪不能佳也。”蔡邕強調抒情性,強調“情”“性”“懷抱”在書法創作中的重要價值,對書法美學思想具有深遠意義。唐代孫過庭認為書法能“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充分表現了書法家們作為審美主體所具有的情感意緒。近代著名學者朱光潛先生,作為美學家,雖然對書法現象從未作專門的研究,但他在研究美與審美原理時,以書法為例,也指出書法可以表現性格和情趣。
(二)書法“具象說”中有一種典型的說法:“書法同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一樣,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具體說來,書法的美,不僅是人類根據頭腦中的各種事物的形體和動態美,還有更多的其背后文化哲學的美。漢字的發明和創造,最初是以象形造字法為主,那么漢字的形體創造是有它最初實用的價值和意義的。所以說古代所遺留下來的書跡除了點畫優美之外,背后所體現的文化是更加尤為珍貴的。西周時期被稱為“四大國寶”的青銅器作品,除了具有篆書書寫的藝術特征以外,其映射出的當時的社會歷史文化是尤為重要的,可以將其與文獻相參照,對比研究當時的歷史文化發展狀況。因此,大量的書跡遺存,承載更多的是各種“意義”,擔負更為巨大的職能,表達更多的是對于文化的傳遞。
三、對書法美學中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思考
文學藝術是否美,不只表現在它寫了什么,而且也表現在怎樣寫,這是胡經之在《文藝美學》思想中所提到的。把這個思想放在書法美學中,引發了筆者對于書寫內容與形式問題的重新思考,同時這也是文章所要重點講述的。根據這個要求,在內容與形式的問題上,東漢時期著名哲學家、思想家王充的觀點就是把內容的“實誠”放在第一位,在“崇實”的前提下,要求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即所謂“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這當然是一個正確的命題。他所說的“實誠”,一方面是指作品所記之事要真實可靠,要如實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存在的事。例如: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行書代表作《祭侄文稿》,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此稿真實記載了常山太守顏杲卿父子一門在安祿山叛亂時,挺身而出,堅決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取義成仁之事。另一方面是指作品中應當必須是真理,要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規律,從而有助于人們辨別真偽,分清是與非。從他的思想中,我們可以得出藝術作品的內容應該是講求“真”的,這種“真”與“美”應當是統一的。不僅如此,他還認為藝術作品要有用。這個要求,其實就是對“善”的要求了。先秦美學都強調藝術作品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積極作用。王充受其影響,強調文章“為世用”。在泱泱華夏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人們書寫了太多的書跡文本,這些書寫的作品首先也都是以實用為前提的,后而追求其藝術性和審美性。
但是,在現今的書法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形式,很容易忽視書法的內容,筆者則認為這并不代表內容被削弱或可有可無。實際上,我認為書法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互為表里。關于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思考,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也提出過兩點:
第一,形式不應該突出自己。他說:“杜詩只有‘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詩概》)。即,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把性情氣骨充分表現出來,而不應突出語言文字本身。就書法而言,如果我們只是追求形式美,突出形式的變化和豐富性。那么,書法的文化內涵,它所記錄的內容和意義就無從表達,文字最初發明和創造的意義也蕩然無存。無論是“十三經”還是“二十四史”等這些被譽為國粹的經典,還是《禮器碑》《張猛龍碑》等碑刻,它們除了具備形式上線條的審美性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內容的表達。
第二,形式因素不能脫離一定的充實的內容而單獨具有美。“書以筆為質,以墨為文。凡物之文見手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書概》)。用中國古典美學的術語說,就是“文”不能離開“質”。離開“質”,“文”就不成其為“文”。胡經之說:“強調內在生命,并不意味著輕視外部活動。藝術應當通過外部活動的表現,最大限度地表現出內在生命。”也就是說書法的形式反而是無法脫離內容。一旦形式脫離內容,純粹玩形式的話,書法就會變得太淺薄而簡單。書法的困難也就在于:必須用雄厚的文化積累來做最簡單的表達。譬如,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書法作品《黃州寒食帖》被后世譽為“天下第三行書”,這幅作品除了書寫形式、技巧高超以外,在內容上,也是一首好的五言詩詩歌創作作品。這與他自身的文化修養是有密切關系的,與他平時讀書所積累的文化知識是分不開的。所以說,欣賞書法作品,并不是單獨的欣賞書法的點畫形式上的美,形式不能脫離內容而單獨具有美。
綜上所述,書法美的構成是內容美與形式美的統一,內容本身各要素的統一,形式本身各要素的統一。
四、總結
對書法美的重新認知:胡經之在書中說:“只有通過藝術欣賞過程中欣賞者的審美闡釋接受,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值才能得以實現”。筆者認為,書法藝術在欣賞的過程中,它的審美價值具有雙重性。書法作為中國所特有的一種“獨特的藝術”,與其他藝術不同的是,文字既是人的交流工具,又是中國人的藝術。它不僅在形式上以線條構筑文字、表達意象、抒發情感,而且以文字來表達內容、傳遞信息、傳達意義。同時,按書寫內容選擇書寫的藝術形式,用不同的字體表達不同的內容,以書法藝術體現書寫的文字內容,這才是中國書法藝術真正的高境界。書法是建立在文字基礎上的藝術,注重內容的表達,才能切入書法的文化核心。書法既是字的形象,又是人的心像,文字內容是書者表達心愿的內在要求。所以說,書法美除了具有結構美和形態美以外,它所擁有的內容美,它的文化價值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參考文獻:
[1]胡經之.文藝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劉守安.劉守安,高秀清.中國古代“書寫”文化簡論[J].藝術百家,2012,28(05):103-113.
[4]陳振濂.書法美學教程[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41-44.
[5]邱恩義.中國書法問題[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3:55-69.
[6]陳方既.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1-18.
[7]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0.
[8]崔爾平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