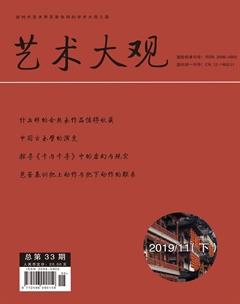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中常見問題之思考
米俊俏 袁劍俠
摘要:植物印染是我國傳統的織物印染方法,捶草印花是植物印染的一種技藝形式,本文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常遇見一些問題,結合捶草印花的保護與傳承案例,提出一些思考建議。探討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發展道路。
關鍵詞:捶草印花;傳統手工藝;非遺;傳承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國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越來越趨同。為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核心的國際力量,倡導人類共同遺產保護,世界各區域人們越來越重視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文化遺產保護活動在世界各民族展開。我國的文化保護政策和保護機制正在產生作用,以政府為主導,全民參與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傳統文化可持續發展工程正如火如荼。文化需求充盈著人們的精神世界,越來越成為大家不可或缺的精神補給。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常遇見一些問題,比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是“人”還是“物”?創新性生產是保護還是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產業化?大家理解不同,各持己見,致使保護和傳承工作也出現不同效果。下文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捶草印花保護與傳承為例探討對常見問題的一些思考。
一、河南非遺捶草印花
捶草印花是河南省三門峽陜州區的獨特植物印染技藝,是一種從大自然中選取各種自然生長的含有色素的花草植物作為染料,在染色過程中使用助劑,如煤染劑、還原劑等,對手工制作的織物進行捶印染色的工藝。
捶草印花起源于何時未得知,但在明、清和民國初期,仍是普遍使用的一種印染技藝,在陜州主要流傳于西部的大營、原店、張汴、西張村、菜園等鄉鎮。制作多為民間的服飾、物件等的裝飾,其地域性較強、技術較為原始,僅在民間流傳,鮮見官方文字記載。自工業革命以后,國外化工染料與機械制備進入中國市場,傳統手工植物印染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和沖擊,民國后幾近失傳。2006年河南省工藝普查中發現三門峽的捶草印花技藝遺存,2008年起河南省三門峽陜州區朱秀云女士著手恢復此印染技藝,2011年,捶草印花技藝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此技藝在河南省三門峽陜州區地坑院5號院和西張馬寨村秀云藝術館有技藝展示和交流基地。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是“人”還是“物”
陜州地處豫、晉、陜交界處,黃河金三角地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新石器時代我們祖先就在此生息,并在現西張村、菜園、窯頭、人馬寨、張汴、西王等地留下大量考古遺存。西周分封焦國、虢國于陜境,是故陜地歷史積淀深厚,與黃土環境、黃河文化關聯密切,民俗風情傳系著傳統禮制文化。捶草印花技藝非遺傳承人朱秀云現所在的西張村,現掌握此項手藝,并仍在生活中使用的有五人。這五人中六十歲以上三人,五十歲一人,四十以上一人。我們可以看到,年齡結構是保護中的重要問題,也就是說,如果這些人不再了,這項遺產是否能夠傳承下去?這個問題也是我常在一些呼吁非遺保護的報道、文章中看到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澄清上文提到的一個問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是“人”還是“物”?
非遺保護在世界范圍內,是人類共同面對的新課題,作為世界范圍人類的公共文化事務,依托國際公約,各國家相繼立法,出臺相關政策、文件,規范指導非遺保護工作。目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一般遵循的規范程序為:普查、認定、申報、記錄、評審、保護等。在這套工作程序中,“人”和“物”是關注重點,所以往往給人以錯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是“人”和“物”,本文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除“人”和“物”,最重要的是“過程”。
乍一聽,好像廢話,保護好“人”和“物”,那么聯系“人”和“物”不就是過程嗎? 所以本文在此首先澄清一下這里所說的 “過程”含義。捶草印花工藝基本制作過程為:備料、尋草(采草)、擺花夾布、捶打、媒染、晾曬。只要看過這項技藝演示的都能知道這個過程,但這過程中有很多的細節在展示中是不體現的。比如:備料中布料的選擇,哪些草葉可以用于捶印,固色時不同草葉所用媒染劑有何不同,套色印染時染料有何選擇等。這些過程都是重要的細節,大多都是靠藝人的經驗積累所得,如果藝人不在了這些技藝的精髓也會隨之而去,這是我們通常的認知。這樣想沒有錯,但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想一想。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至關重要的細節“科學”地記錄下來,不就更加利于保護了嗎? 比如,用于捶印的草葉、花卉的品種,分布區域,實物圖像,汁液成分分析等,媒染劑酸堿性、成分配比、化學反應、呈色圖譜等進行科學整理。這些整理不僅利于捶草印花技藝的保護,也利于運用當代技術擴展于植物印染行業,結合現代生產。現在對非遺進行的研究的人很多,成果也很多,但作非遺技藝科學記錄的人相對較少。注重科學保護過程的細節,才是非遺保護的初衷。
三、創新性生產是保護還是破壞?
陜州捶草印花所用布料都是純天然的手工棉布,所用染料都是來自大自然然的植物,與現代人們追求的天然純凈生活理念不謀而合。按理說應該很受歡迎,但本文在前期調查中發現,陜州捶草印花產品多作為旅游紀念品銷售,鮮見用于日常生活。朱秀云的女兒和外孫女,有高等教育背景,經常參加全國各地的印染培訓學習,她吸收全國植物印染的各種技法和捶草印花結合。她們創新制作的桌巾、披肩、茶巾等擴大了受眾,提高了銷量,但有一種聲音來了,這不是“原汁原味”的捶草印花。那么問題又來來了,創新是不是保護?創新性生產是保護還是破壞?
關于非遺創新的問題,并不是一個新鮮話題,近年來學界對此問題已多有論述,各抒己見。觀點大致可分兩類,一種認為,非遺最大的價值是歷史認識價值,如果創新,原有的歷史認識價值不存在了,那么也就不是非遺了。另一種認為,非遺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生活智慧結晶,作為傳統文化遺產,若沒有當下生活的結合,非遺將沒有生命力,遲早會成為歷史,退出我們的生活。這兩個主流觀點看似“互斥”,實際關注的核心是相同的,即非遺價值體現。說到這兒,我們換個角度思考一下,如果非遺是一個人,他的價值體現是由“讓其發展”和“不讓其發展”的外因決定的嗎?當然不是,價值體現應該由內需里決定的。
縱觀人類手工藝發展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 特別是手工藝類非遺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關乎人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生活在變,服務于生活的手工藝也要變。中國傳統手工漆器、瓷器、金銀、玉石雕刻等,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造型、風格、裝飾都不同,隨著技術的進步,不斷出現新技法、新品種都是自然的規律,是社會進步、文化交流、商業需求、行業競爭等一系列綜合因素影響的結果。傳統手工藝歷史中的這些變化,并不影響今天給我們的價值,它們依然是優秀文化遺產漆器、瓷器、金銀等。其實手工藝非遺,其創新有一定的原則與限度,我們大可不必過分擔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也明確提出了,“保護”是指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各種措施。創新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生命力的需求,我們能做的就是為創新提供更好環境。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產業化
一提到“產業化”,很多人立即會想到“標準化”“批量化”的現代化生產。非遺一旦和標準化聯想在一起,諸多反對的聲音就來了,大呼不可以的為數很多。因為非遺保護的初衷是維護文化的多樣性,是現代標準化生產的反思或措施。文化多樣性與標準化是天敵,故非遺產業化是荒唐的。這里有一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對產業化的誤解,把產業化與標準化對等,是產業化概念與范疇不清楚造成的。產業化的定義:是指產業在市場條件下,以行業需求為導向,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產業化,要視非遺的分類而定。對于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類非遺不能產業化,但對于傳統手工藝類非遺可以產業化。比如,陶瓷類非遺項目,本來陶瓷主要是服務于生活的手工藝術,今天的生活依然需要大量不同種類、不同風格的陶瓷產品。
捶草印花工藝一直流傳在民間,制作多為民間的服飾、物件等的裝飾。他的制作純手工,材料純天然的特點,符合現代高品質生活人群的需求,適合結合現代審美進行現代開發,但其自身的特點又決定產量很低,所以捶草印花的現代開發,應是高端產品、小批量定制的開發。 高端產品開發要求有系列的品牌策劃等產品運作。捶草印花的圖案多是結合陜州民間民俗剪紙的圖案,現代審美的開發,同時吸收同行業植物印染的各種技法結合捶草印的創新也是必需的。
五、總結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如何保持其活力,調整我們與大自然的關系。本文就幾個問題所析的捶草印花技藝發展的一點思考,也是手工藝類非遺發展的探討。如今的市場從關注品牌的知名度,逐步轉變為手工制作的獨特度。傳統手工藝類非遺有工藝之美,有傳統文化,與現代審美結合,定能散發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