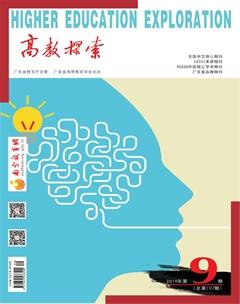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國際經驗與政策創新
許長青 郭孔生
摘要: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國際一流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呈現出地理臨近、組織臨近、文化異質、規模效益、競爭優勢明顯、產教融合等多重特征。國際一流灣區有層級、有梯度而又緊密聯系的高等教育集群強有力地支撐了灣區經濟社會發展。借鑒國際經驗,構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規劃機制、健全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機制、建立灣區高等教育品牌提升機制、制定灣區高等教育法律保障機制、實施灣區高等教育資源共享機制,成為打造灣區高等教育集群、提高灣區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政策創新
灣區因具有天然的地理區位優勢,在全球經濟增長中具有重要地位,“灣區經濟”也成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綜觀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個世界一流灣區,它們既是經濟、貿易、金融中心,也是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一流的教育成就了一流的灣區,一流的灣區反哺著一流的教育。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布實施,這標志著粵港澳跨區域合作發展的藍圖正式拉開帷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了由理念到實踐的新階段。《規劃綱要》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和人才高地,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一流灣區相比,存在一些短板,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高水平大學的積聚與擴散效應不明顯,世界一流的區域創新生態體系尚未形成。因此,借鑒一流灣區的成功經驗,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全面提升灣區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是灣區建設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集群是一個生態學概念,意為不同種群在同一棲所的集聚形式和共生關系;集群也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指集成的通信系統可以起到資源共享、成本分擔、高效運行的效應。高等教育的空間布局符合“核心—外圍”理論,其空間分布同樣可以產生集聚效應,形成高等教育集群。高等教育集群是高等教育結構布局在地域空間上的特殊表現形式,眾多大學集聚在一起就會形成區域性大學群落,它既表現為一定量的規定性,也表現為一定質的規定性。高等教育集群具有相對完整的地域性特征,能夠集聚大學資源、融合教育要素、共享教育設施、推進互動合作、實現大學規模效應。關于集群發展問題的研究,早在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英國中小企業迅速集聚,謀求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社會分工與專業化。[1]這種專業化分工理論所蘊含的集聚思想,為產業集群奠定了理論基礎。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90)稱中小企業集聚區為“產業區”,認為中小企業集聚的動力源于外部經濟。[2]波特(1990 &1998)最早提出產業集群的概念,認為集群(Cluster)是在某一特定區域、某一特定制度下,聚集著一群相互關聯的公司、產業、供應商。[3]產業集群(Industry Cluster)是指在特定的地理范圍內,多產業相融、多機構相聯的共生體,某一產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該產業集群的規模與程度。[4]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997)從工業區位視角切入,認為只要產業集聚更有利于節約運營成本,集聚就會產生。[5]高等教育和區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密切相關,一方面,區域經濟、政治和文化活動為高等教育機構提供支持并對其提出要求、施加影響;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在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與技術服務的同時獲取各種資源以實現自身發展。拉里·羅利(Larry L.Rowley,2000)認為,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國家、城市與大學將會非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一方,那么另一方將不能幸存。[6]伯頓·克拉克(Burton R.Clark,1999)認為高等教育聚集與合作可以極大地促進物質和知識的有效流動。[7]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關鍵在于世界頂尖人才的高度聚集。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1993)指出:“從波士頓到華盛頓之間分布的大學和實驗室中,可以找到 46%的美國諾貝爾獎得主和 40%的國家科學院院士。”[8]
國內學界普遍認為,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密切,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動力。潘懋元(2010)認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高等教育發展的差異,主要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與規模存在差異。[9]何心展、張真柱(2002)認為,高等教育規模與水平都需要區域經濟的支持。[10]謝名家(2003)指出,高等教育對區域文化相關產業具有明顯優勢。[11]郄海霞(2009)認為,高校聚集在一起所產生的收益與效應比任何一所高校單獨為城市帶來的收益與效應都要大,因為“這種集群創造了非常富有創造力的環境”。[12]潘海生、周志剛(2018)總結了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生成機理并將其概括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說、本質說、效益說、動力說,產業集群與高校集群的本質具有共性和一致性。[13]楊芳、王啟兵(2006)從教育聯盟的視角解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認為高等教育集群就是圍繞高等教育目標,高校與高校、政府、企業、家庭、社會名流等機構或個人之間形成優勢資源互補式合作的教育戰略同盟,旨在促進成員間資源優勢互補,增強高等教育競爭力。[14]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產業集群發展研究方面,相關研究對解決粵港澳高等教育深度合作問題提出了一些策略,如粵港澳高等教育共同體建設(朱建成,2009)[15],粵港澳高等教育一體化(朱建成,2010)[16],粵港高等教育合作試驗新區的創建(徐瑤,2015)[17],珠港澳高等教育聯動發展(王坤,2017)[18],大陸與香港高校研究社區的整合(Kim,Horta & Jung,2017)[19],大灣區高等教育深化合作的模式(冼雪琳、安冬平,2017)[20],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歐小軍,2018)[21]。
綜上,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文獻并不豐富,研究的廣度、深度與方法都有待拓展。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背景下,社會各界急需發現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與融合發展中表現出來的各種新問題、新矛盾,需要在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對新問題、新矛盾進行深入剖析,獲得可靠研究結論,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思想、新思路。本研究采用比較研究方法,從集群發展視角分析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政策創新問題。
二、經驗與比較
粵港澳大灣區旨在2030年前后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實現這樣一個宏偉目標,國際一流灣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綜觀世界一流灣區,高等教育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國際灣區高等教育發展表現出共性特征——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呈現集群發展,高等教育集群與產業集群緊密聯系、互為動力、相互推進。美國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高等教育聚集區主要坐落在東北區、五大湖區、西海岸區、南部海岸區。同樣,東京灣區是日本高等教育的最大集聚區,高等教育的集聚作用不可或缺。
1.紐約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
紐約灣區地處美國東北部,面臨大西洋,輻射10 個州、30多個市縣,形成了以紐約為中心的世界級超大城市群與沿大西洋經濟帶,既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集聚中心。美國高等教育起源于東北部最初的13 個殖民地,美國高等教育第一個集群發展區域也是這13個殖民地。從廣義視角看,本研究的紐約灣區是指紐約大灣區,主要包括紐約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賓夕法尼亞州、羅德島州等。紐約大灣區高校林立,眾多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共同組成了灣區內一個有層次、有梯度、有緊密聯系的高等教育集群。紐約灣區擁有副學士學位以上高校304所,四年制大學227所。以馬薩諸塞州為例, 這里擁有副學士以上學位授權高校124所,四年制大學101所,波士頓地區集中了包括波士頓學院、波士頓大學、布蘭德斯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東北大學、塔夫茨大學、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等世界著名大學在內的 52 所高校。以賓夕法尼亞大學為核心,賓夕法尼亞州擁有副學士以上學位授予權高校262所,四年制大學160所。紐約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充分發揮整體優勢,實現了不同大學功能要素的相互作用與相互補充的“共生”關系。
第一,世界頂尖高水平大學集群。紐約大灣區頂尖高水平大學集群除了紐約州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康奈爾大學之外,還包括新澤西州、馬薩諸塞州等周邊州的世界頂尖大學。如表1所示的美國8所“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中,紐約大灣區占據了7所,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加上頂尖的私立高水平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高校,共同組成了世界頂尖高水平大學集群。這些大學辦學歷史悠久、人文底蘊深厚、科研實力雄厚、創新能力強大,對紐約大灣區科技、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了極大輻射效應,為紐約灣區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第二,世界高水平大學集群。繼“常春藤盟校”之后涌現的新生力量就是“新常春藤”(New Ivies)高校聯盟。這些學校不但辦學歷史悠久,而且具有卓越的學術聲譽,有些大學的學術水平還高于常春藤大學。如表2所示,位于紐約大灣區的“新常春藤”高校有9 所,“小新常春藤”高校有14 所(表3)。世界高水平大學高度聚集、集群發展的態勢同樣強有力地支撐了紐約大灣區發展。
第三,世界高水平公立大學集群。紐約州立大學(SUNY)與紐約城市大學(CUNY)兩個公立教育系統中均具有眾多的高水平大學。SUNY包括64所大學,其中賓漢姆頓分校、石溪分校、布法羅分校、奧爾巴尼分校等4所大學是實力強、水平高、聲譽好的研究型、綜合性世界一流大學。CUNY包括17所學院,在校生54萬多。另外,紐約大灣區還聚集了德漢姆大學、羅徹斯特理工大學、雪城大學等眾多高水平私立大學。世界高水平公立與私立大學高度聚集,為灣區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和人才支持。
2.舊金山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電子、信息、航天等新興產業的興起并向美國西部和南部轉移,高等學校隨之在西太平洋沿岸和南部墨西哥灣沿岸形成了新的集群,加州大學群就是其中之一。舊金山灣區依托西海岸區位優勢與加州高水平大學高度聚集優勢,形成了灣區高等教育集群。舊金山灣區高等教育集聚區擁有副學士以上學位授予權的高校達454所,四年制大學249所,成為“世界上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系統”。[22]在加州高等教育集群發展中,大學服務社會的理念和實踐及政府的宏觀調控均影響著舊金山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的產生,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張力共同推動了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自下往上看,主要是基于產業的發展,大學服務適應市場需求。自上往下看,克拉克·科爾主持起草并頒布實施的《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對整個區域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加州公立高等教育是一個多層次、多類型、多形式的體系。第一層次為加州大學(UC):招收綜合成績排位前125%的高中畢業生,UC有碩士與博士學位授予權;第二層次為加州州立大學(CSU):招收綜合成績排位前1/3的高中畢業生,只有碩士學位授予權,博士學位必須與加州大學聯合頒發,并且側重應用研究領域;第三層次為加州社區學院(CCC):招收所有的高中畢業生,由原來的中等教育升格為高等教育機構。與公立高等教育并行不悖的是,加州擁有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學院等這樣眾多高水平的私立研究型大學。這些大學根據“功能分類、競爭合作”的原則,在“規模、結構;管制、自治;公平、效率;競爭、合作”等方面都做到較好協調[23],在協同、戰略、效率、責任等方面,加州高等教育結構和功能都得到了最優化。[24]卡拉克·克爾(Clark Kerr)指出:“沿著加利福尼亞海岸,你將可以看到一幅由延綿不斷的學術山脈組成的新圖景,這里不但聚集了美國20%的科學院院士,而且聚集美國36%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25]同時,加州亦擁有世界頂尖的私立大學,卓越的公立高等教育與頂尖的私立高等教育共同構筑由三部分組成的舊金山灣區高等教育集群。
一是世界一流大學集群。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不但是世界頂尖學府,而且是美國工程與科技界領袖。此外,在國際高等教育各類排行榜中,舊金山灣區內還擁有多所世界前100的大學,最終形成如表4所示的舊金山與洛杉磯南北呼應、多中心聯動發展的世界一流大學集群,對整個灣區科技與經濟產生強大的聚集與輻射作用。
二是美國一流大學集群。美國舊金山聚集了一大批美國一流大學,這些大學雖然與頂尖研究型大學定位完全不同,但完全可以滿足舊金山灣區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個性化與多樣化的需求。如舊金山大學以創業學聞名世界,舊金山藝術大學是美國私立頂尖藝術院校,金門大學與圣瑪麗學院等高校享有很高聲譽。舊金山周邊地區聚集了多名尼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圣塔克拉拉大學等眾多著名的高水平大學。
三是國際一流社區學院集群。加州擁有圣莫妮卡社區學院、歐文河谷學院等119所社區學院。作為整個加州高等教育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區學院對舊金山灣區的輻射作用與溢出效應,絕不低于加州其它高水平大學。這些社區學院因為以本科教學與職業教育為主,所以在技能型人才培養與服務灣區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3.東京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
東京灣區由“一都三縣”組成,“一都”,即東京都,是日本最大城市群的中心,“三縣”,即千葉縣、琦玉縣、神奈川縣,是東京灣區的“三翼”。東京灣區是集聚了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早稻田大學、筑波大學等120 多所高水平大學的高等教育集群。
其一,“超級國際化大學”高等教育集群。日本政府在2013年圍繞教育問題,特別提出了一個長期目標,即在未來10年,致力于將10所日本大學推進到世界前100強行列中。為提升日本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和日本大學生的國際化程度,日本于2014年制定了“超級國際化大學(Super Global University)”計劃。[26]列入“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的大學共有37 所大學,其中東京灣區占據17所。 如表5所示,東京大學等6所被列為A類頂尖型大學,千葉大學等11所被列為B類牽引國際化型大學,致力于牽引日本社會國際化。
其二,“牽引國際化人才大學”高等教育集群。在2014年實施的“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中,日本政府還開列了42所“牽引國際化人才大學”的名單,旨在培養能積極面對挑戰的國際化人才,全面推進日本經濟社會發展。42所“牽引國際化人才大學”中,東京灣區就占據了22所。如表6所示,早稻田大學等5所被列為A類全面推進型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17所被列為B類特色型大學。
其三,其它高水平大學集群。2014年沒有列入“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的其他高水平大學,在東京灣區同樣呈現集群態勢。如日本大學、專修大學、國學院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東海大學等高校,雖然沒有列入“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但與早稻田大學等其他7所大學一樣,都是“東京12大學”聯盟成員中的高水平大學。此外,還有東京農工大學、首都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東京理科大學等一批規模小、有特色、專注于某一學科領域并做到國內甚至是國際領先水平的大學。
綜上可知,國際一流灣區具有一個共同特征,即一流灣區均是全球創新資源、創新人才的集聚中心,也是世界高水平大學的集聚中心,不同層級的高等教育集群極大地推進了灣區經濟發展。美日高等教育集群呈現出地理臨近、組織臨近、文化異質、規模效益、競爭優勢明顯、產教融合等多重特征。地理臨近是大學集群最為顯著的特征。追求辦學效益的時候,地理位置臨近始終是大學考慮的因素之一,不同大學會從其競爭對手、同行臨近中獲得極大的外部收益。組織臨近特征在高等教育區域集群中也表現明顯,雖然高等教育集群內的大學聯系網絡相對松散,但是各大學之間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存在密切的交流和聯系。美國大學集群內“沒有一所大學能夠包容所有專業領域,或是包容的專業領域足以使其擁有充足的專業者群體,大學合作委員會將它們各圖書館的藏書資源合并起來,為研究生開辟了共同市場”[27]。各具特色的大學在地理和組織上的臨近使大學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系,實現了物質和知識資源的交流與整合,獲得了集聚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知識競爭優勢,使灣區大學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文化異質表現在高等教育集群形成過程中,灣區大學始終伴隨著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尊重大學間的差異與傳統成為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主旋律,求異、求特成為美國大學集群中大學的普遍價值選擇。如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一個是人文綜合性特色,一個是工程教育特色,并在各自領域做到了極致。由于地理臨近縮小了大學之間的空間距離,為大學之間合作辦學、共同開發等創造了條件。集群內大學可以通過校際間的課程互選、學分互認、學科共建、教師互聘、設備設施資源共享、科研合作等形式充分利用各自的學科優勢,緩解教學研究資源不足,實現優質教學研究資源的共享,以提高教學、科研水平,進而獲得外部經濟、規模效應等集聚經濟效應。高等教育與產業集群協同發展,全面推動了人才與資本聚集,打通了從科技創新到產業應用的關鍵環節,真正實現了“產學研政用”的完美銜接。這種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共同發力、產教融合、跨界合作,促進了高校與企業間的深度合作,促成了科技與產業間的聯姻,增強了大學知識創造能力、人才培養能力、成果轉化能力,提升了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
三、政策與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要實現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高等教育的聚集與輻射作用不可替代。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集聚了一定數量的高水平大學,百強大學總數等多項指標上具有優勢,發展潛力巨大。盡管如此,區域高等教育協同創新能力仍然不足,國際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格局尚未形成。因此,推動粵港澳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全面提升區域高等教育水平是一項緊迫的任務。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創建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模式,真正發揮高水平大學在灣區建設中知識外溢作用,亟待從高等教育治理、體制機制、法律政策、共建共享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1.構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規劃機制,促進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教育、產業、科技相互脫節,大學、產業、政府聯系不緊密,這是灣區經濟與科技發展過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粵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發展基礎、發展模式、國際化程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所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需要進行合理規劃,科學引導大學合理布局與集群發展,實現大學、產業、行業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只有通過整體規劃,才能更好地對各種資源進行整體布局與優化,促進高等教育資源的積聚,進而使大灣區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得到顯著提高,最終建成教育和科技高地。粵港澳大灣區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在教育、產業、科技、經濟之間,構建一種聯動發展、協調治理的整體規劃機制。對照國際規則與標準,按照打造大灣區教育合作示范區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科技與教育高地、建設人文灣區的目標,深入研究和領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精神內核,加強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戰略規劃,制定具體的工作方案與步驟,出臺相應的配套制度與措施等。把推進高等教育聯動發展與協調治理,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先行先試、引領創新的重點。通過建立創新型聯合大學,引進國際名校和特色學校, 共創世界一流大學,結合國家“雙一流”大學建設標準,共創共建世界一流大學,并在高等教育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2.健全粵港澳高水平大學協同發展機制,促進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粵港澳三地存在著制度上的差異,因而三地教育行政主體的利益訴求也會有所差異,要實現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就必須從國家戰略層面,通過教育融合的手段,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委員會,構建三地高等教育協調機制,以化解制度壁壘。在三地政府部門達成共識、教育行政部門統一部署的基礎上,可以由合作委員會具體落實,促進專業、學科、人才、校企融合、平臺建設等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在“一國兩制”背景下,通過協調機制推進三地高等教育政策體系的銜接和融通,高等教育跨區合作平臺的互聯與互通,從而吸引更多世界高水平大學聚集灣區,形成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的效應,讓知識經濟成為第一驅動力,讓灣區資源實現全球配置,讓“政、產、學、研、用”實現跨界融合,充分發揮科技創新輻射力。此外,粵港澳三地產業集群發展為粵港澳大學集群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目前,最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校企深度合作”、“產教跨界融合”、“校企精準育人”等方法與手段,促進高水平大學從相對松散的狀態向專業共建、學科共融、資源共享、人才共育、產教共融這種相對緊密的狀態與方向發展,有效構建粵港澳高水平大學集群,融合、和諧、協調、共生的教育生態。三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與每一間大學都要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理順“政、產、學、研、用”等與大學集群發展、融合發展密切相關的微妙關系,爭取有利于大學集群發展的外部資源,統籌規劃、密切協同,使之成為世界高水平大學的重要集聚地,構建具有世界高水準的科研創新和人才培養基地。[28]
3.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品牌提升機制,促進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做強、做大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品牌,最為關鍵的思路就是讓教育合作得到進一步擴大,讓教育交流充分體現廣度和深度,讓教育資源實現跨界流動、整合與優化,建立高水平的高校協作群,打造突顯優勢學科的創新平臺。為此,一是要推進國內高校之間、國內一流大學與國外一流大學之間的強強聯合,通過多種形式實現多校聯動、協調治理。如實現資源平臺共享、精品課程資源共用、重點實驗室共建、實習實訓基地共設,招生可以聯考、課程可以互選、學分可以互認、教師可以互聘、畢業生就業指導與培訓工作可以互通,全面提升學校辦學水平和提高人才的培養質量。二是設立粵港澳高等教育特別合作區,引進國際優質課程乃至國際名校入駐大灣區。對照國際標準,加強與灣區內的著名大學合作辦學,與外地著名高校合作辦學,與國外名校合作辦學,打造獨具特色的創新型大學。為了更好更充分地發揮廣州的區位優勢,建議在廣州南沙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特別合作區。合作區內可以借鑒加州大學系統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大學。在廣州南沙設立行政總部,灣區內的11個城市都設立分校,著力推進高水平、高質量、全方位的國際合作,引進國際名校課程,聘請國際名師授課,鼓勵國際名校辦學,最終形成大灣區新型的高水平大學群。
4.制定粵港澳高等教育發展法律保障機制,促進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當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最大的挑戰就是:在“一國兩制”的國家制度之下,如何克服關稅系統不同,法律體系迥異等方面問題,打造與世界一流灣區相匹配的高水平大學集群。因此,制定與粵港澳大灣區相配套的政策、法律與法規是促進灣區內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的關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已經出臺,當前,最為重要、最為緊迫的任務應該是盡快制定、出臺操作性強的配套政策與法律法規,把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納入法治軌道。當然,各大學應當透徹理解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的要求,并主動適應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新定位,通過動態監測與實時調整機制,不斷優化大灣區高等教育的學科、專業、層次、類型等方面的結構,為整個大灣區社會、經濟、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多創新型人才。在新政策、新法律與新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有計劃、有重點地建設一批符合灣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特色專業,有步驟、有針對地建設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產學研創基地,合理、有序地擴大高技術、高技能、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規模。同時,緊扣服務灣區發展、支撐灣區崛起需要的特殊人才培養思路,加快創新型、應用型、法治型研究生培養。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既有政府主導的方面,也有市場主導的特色,既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導向,也有區域發展政策的傾向性。因此,國家和地方政府都應盡快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大學集群持續、穩定、快速發展。
5.實施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資源共享機制,促進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在貫徹“一國”方針的同時,打破“兩制”所帶來的體制機制壁壘,促進高等教育資源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優化配置,從而更好更快地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資源的開放與共享,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開放與共享。首先是要建立硬件資源的共享機制。通過高校共建、共享、互聯、互通的深度聯動,充分提高重點實驗室、大型實驗設備、重點實習基地、精品課程、各類圖書文獻等各種教育資源的利用率,通過多方聯動與協調,盡量減少重復建設、重復培育而造成的人力、物力與資源的浪費。建議推行“粵港澳大灣區大學一卡通”,各類高校教師與學生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大學自由參觀學習,通過教育資源共享平臺,獲取數據資源、文獻資源、優質教育資源等,高校可以共享優質的課程資源,可以共用優質的名師資源,可以讓教師跨校跨區講座授課,可以讓學生跨校跨區選修課程。其次是建立軟件資源的共享機制。一個地區最大的軟件資源其實就是人才資源。粵港澳大灣區必須打造可以引領未來的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群、一流研究機構,與之匹配的當然要有一流的基礎設施、一流的科技企業、一流的創新創業隊伍。要提高粵港澳大灣區高級人才資源的存量與質量,就必須形成高級人才培育與聚集的擴散效應,才能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人才保障與智力支持。[29]人才資源共享機制的形成,其先決條件是人才資源存量充足。舊金山灣區聚集了超過150名諾貝爾獎得主,20名菲爾茲獎得主,40多名圖靈獎得主,這些高端人才資源不但可以共享,而且因這些高端人才匯聚形成了強大的人才向心力,吸引全球頂尖級各行各業人才的大集結。
四、余論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是一個極具創新性與挑戰性的課題。實現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宏偉目標,要求我們站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制高點,站在集群發展與協調治理的塔尖,順應灣區經濟與知識經濟時代發展趨勢,推進灣區高校集群發展。國際一流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經驗值得借鑒,但粵港澳大灣區有著自身的優勢和挑戰,必須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集群發展之路。建立健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規劃、協同發展、品牌提升、法律保障、資源共享五大機制,必將有助于持續推進三地高校合作與國際高端人才聚集,充分拓展教師學術發展空間,提升教師學術發展水平,提高灣區高等教育集聚和國際影響力。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5-7.
[2][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著.經濟學原理(下)[M].朱志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85-96.
[3][美]邁克爾·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M].李明軒,邱如美,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
[4]Porter,M.E.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77- 90.
[5][德]阿爾弗雷德·韋伯,著.工業區位論[M].李剛劍,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18-123.
[6]Larry L.Rowle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Black Urban Communities:The Clash of Two Cultures[J].The Urban Review,2000,32(1):45-65.
[7]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154-156.
[8][25][27]克拉克·科爾,著.大學的功用[M].陳學飛,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65-67.
[9]潘懋元.潘懋元文集之問題研究(上)[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1.
[10]何心展,張真柱.建設大學城促進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J].中國高等教育,2002(9):34-36.
[11]謝名家.建設中國特色文化產業新論[J].廣東社會科學,2003(3):130-138.
[12]郄海霞.美國研究性大學與城市互動機制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203.
[13]潘海生,周志剛.大學集群:高校集聚的本質與研究視角[J].未來與發展,2019(11):79.
[14]楊芳,王啟兵.教育集群:高校當前的發展之路[J].企業家天地(理論版),2006(8):116.
[15]朱建成.粵港澳高等教育共同體建設的探討[J].高教探索,2009(6) :77-80.
[16]朱建成.粵港澳高等教育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J].社會工作與管理,2010,10(2):15-19.
[17]徐瑤,廖茂忠.創建粵港高等教育合作試驗新區的思考[J].高教探索,2015(5).35-38.
[18]王坤.珠港澳高等教育聯動發展的對策研究——基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J].特區經濟,2017(9):24-29.
[19]Kim,Y.,H.Horta & J.Jung,2015,“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Japan,China,and Malaysia:Exploring Research Community Cohe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matic Approaches.”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2(1).
[20]冼雪琳,安冬平.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現狀及合作模式探討[J].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4):7-11.
[21]歐小軍.“一國兩制”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大學集群發展研究[J].現代教育管理,2018(9):23-28.
[22]陳厚豐.中國高等學校分類與定位問題研究[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185.
[23]劉小強.美國加州1960年高等教育總體規劃:一個成功范例[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6,27(2):95-102.
[24]Langenberg,Donald N.Degrees and Diplomas are Obsolescent[J].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97,9(12):8-9.
[26]陳洋.“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日本的一次教育維新[N].光明日報,2015-10-25(06).
[28]黃崴.建立粵港澳大學聯盟——打造世界高水平科研和人才培養高地[J].高教探索,2016(10):18-31.
[29]林貢欽,徐廣林.國外著名灣區發展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5):25-31.
(責任編輯 劉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