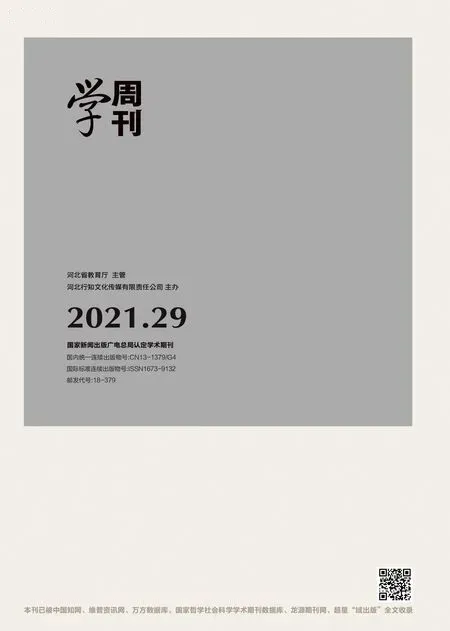淺談成果導向教育(OBE)理念的起源、發展及理論基礎
摘 要:2018年教育部發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其原則和理念主要是以學生為中心、成果導向教育、持續改進。文章以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為背景,分析了成果導向教育(OBE)理念的內容、起源、發展與理論基礎,探討了成果導向教育理念的內涵和局限性。
關鍵詞:成果導向教育;能力導向教育;OBE;教育理論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132(2019)29-0005-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9.29.001
國家標準出臺之前的教學改革研究,所遵循的教學理念各有不同,但隨著2018年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的實施和專業認證的推行,其所遵循的原則和理念(以學生為中心、成果導向教育、持續改進)將隨之得到廣泛運用。在這種背景下,對成果導向教育理念的起源、發展、理論基礎和實施要點加以厘清,無疑對于合理使用成果導向教育理念進行教學改革具有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價值。
一、術語界定
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簡稱OBE,又名結果導向教育、產出導向教育,絕大多數文獻認為,成果導向教育一詞首先由斯派狄(Spady)提出。斯派狄在其著作中認為,成果導向教育的重點不在于學生的成績,而在于學習過程結束后學生真正擁有的能力。
成果導向教育強調成果導向,重視學生學習成效,明確學生能力目標。
與成果導向教育非常接近的概念是能力導向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簡稱CBE。
OBE和CBE兩個概念都關注課程的產品或者結果,而不是過程,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微妙的。
按照阿爾巴內塞(Albanese)等人的觀點,結果和能力之間的區別在于“want”和“need”。“want”定義了我們想要學生具備的技能和素質,而“need”決定了學生從事某項工作時需要具備哪些技能和素質。
學習成果(outcomes)使用層次結構來描述,對教學評估非常有幫助。而能力(competencies)屬于學生或畢業生,而不是教師。成功完成課程的學生的能力至少應等同于規定的學習成果。
盡管不同作者在如何使用該術語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在實踐中,沒有發現成果導向教育(OBE)和能力導向教育(CBE)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因此,本文使用術語OBE來指代兩者。
二、OBE的原理、假設與特點
OBE實質是以學生為中心,重點關注學生“獲得了什么”,而不是社會、學校、教師為教學“投入了什么”或者“講授了什么”,強調專業與課程的建設要從學生的獲得結果出發,進行反向設計,認為只要學生努力都能獲得學習成功,斯派狄強調成果導向教育需要明確規定所有學生畢業后能達成某任務的能力。
成果導向教育的基本原理是“所有學生均能成功”(success for all),其基本假設是所有學生都是有才能的,每個學生都是優秀的,學校是為學生找到成功方法的機構。
OBE教學理念具有如下特點:
1.清晰。
OBE聚焦于產出,使得學生對課程結束時需要完成的目標有了明確的認識,也使得教師對課程的教學內容有了明確界定。
2.靈活。
OBE并不指定滿足學生需求需要采用何種教學方法,只要能達成教學目標,教師可以靈活采用多種教學手段。
3.可比。
OBE可以對一門課程在不同教學機構中的教學效果進行比較。這種比較基于學生已經擁有的技能和知識。
4.參與。
OBE的關鍵是學生在課程中的參與,通過增加學生的參與機會,讓學生意識到學生才是真正的責任者。
三、OBE的起源與發展
(一)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第一輪倡導、批評與復興
1957年,前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并成功進入地球軌道。這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美國將其在太空競賽中落后的主要原因歸結到教育系統。因此,美國政府遂大力干預教育和培訓,大量資金被用于教育。
隨后的辯論和研究大大推進了OBE的發展及其在學校和教師培訓中的實施。首次倡導OBE的浪潮在20世紀70年代初達到了高潮。
早期OBE的理論基石是行為主義(behaviourism),如沃森、巴甫洛夫、桑代克和斯金納等實驗心理學家的著作所述,他們的理論興趣集中在可觀察的行為上。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股潮流轉向行為目標課程模式。斯騰豪斯(Stenhouse)是這一時期非常有影響力的OBE批評者,他認為,OBE未能將影響價值觀、洞察力和判斷力發展的教育過程納入到嚴格關注行為目標的課程模式中。當學生從情感上、社會上、文化上、美學上或道德上從經驗中學習時,不可能明確目標或客觀地評估目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此類學習并不重要。
OBE的復興始于20世紀80年代。但斯派狄倡導的OBE并沒有基于任何新的理論,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具限制性,尤其是在影響(態度、情感和價值觀)方面,斯派狄承認它們(態度、情感和價值觀)的重要性,但認為它們是結果的先決條件,并且由于這些目標不可直接觀察,所以被斯派狄排除在目標之外。
(二)20世紀末——第二輪倡導
受斯派狄啟發,哈登(Harden)等人將OBE描述為“以績效為基礎的最前沿方法(它為教育改革和管理提供了一種強有力且具有吸引力的方法)”。在同一時期,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的醫學院目標項目(MSOP)發表了一份提倡基于競爭的教育報告;研究生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GME)和美國醫學專業委員會共同商定了六項能力,用于醫學專業認證。
哈登的同事們認為,OBE是一種有遠見的教育新方法:從課程內容和結構、教學和學習活動、教育環境和課程評估等方面,邏輯上皆遵循明確的結果。
首先,確定學習成果,明確并傳達給所有相關人員。
其次,教育成果是決定課程的首要問題。在這一時期,OBE開始走向國際,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開始OBE教學實踐。
(三)新千年時期——在批評中應用
21世紀前10年的研究,多為具體學科領域中對學習成果(能力目標)的明確,換句話說,這一時期對OBE的研究主要是對OBE如何應用進行探索。
例如,美國的一項醫學課程組定義了12個關鍵成果領域,這些領域被細分為86個學習成果,讓各個學校根據課程需求進一步細分。后續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課程風格迥異的學校也可以就學習成果達成共識。
隨著理論與實踐的逐漸完善,OBE得到了國際教育界的關注和認可,如,2005年中國香港地區高校和中國大陸高校也開始將OBE應用于教學中。
2010年,庫克(Cooke)等人發表了一份有影響力的報告,認可了以成果為導向的課程開發方法,這份報告建議廣泛采用OBE,并要求項目負責人對學習者提出明確、漸進的期望。根據這份報告,項目負責人必須確定學習者已經達到了標準化的能力標準,并且對學習者的評估必須是綜合和累積的,包括專業的形成、正式的知識和表現、形成性反饋、指導以及各級發展能力的總結性認證。
在大力支持OBE的同時,這份報告指出了兩個重要的尚未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和評估人本主義、問責制和利他主義,這是個人獨有的,因此很難與OBE框架協調一致。第二個問題是當能力以“足夠好”的表現為目標時,如何促進卓越,畢竟“足夠好”還“不夠好”。
當OBE被廣泛采用的同時,批評意見也層出不窮。
雷斯(Rees)認為,關注課程的結果而不是教育過程,與良好的教育實踐是對立的。庫克(Cooke)、霍奇斯(Hodges)等人認為,OBE幾乎完全用評估和問責制來表示,與教學和學習幾乎沒有直接聯系。中國臺灣學者將對OBE的批評歸納成了五個方面:(1)對不同背景的學生、不同品質的學校實施標準化評價有失公允;(2)預設的能力水準對不同學生可能不適用;(3)缺少足夠多的實證研究表明OBE有效;(4)實施OBE會增加教師和學校的負擔;(5)在實施過程中,容易將其他教學改革方案捆綁在一起。
四、尚不堅實的OBE理論基礎
從目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成果導向教育理念與專業評估密切相關,但OBE似乎一直缺乏能將如何定義結果和支持課程的教學活動二者之間聯系起來的強有力的理論基礎。普里多克斯和諾曼的研究,專門質疑了學習成果與教學之間聯系的本質。還有個問題是,OBE的緣起是行為主義理論,但這種理論與現代學習理論相比,已顯得有些過時,行為主義理論無法解釋學習成果與教學之間學理上的邏輯關系。OBE的重點是評估可證明的能力方面,但應該記住,斯派狄說,影響(affects)不是學習成果,因為這與他的行為主義立場相沖突。
能夠幫助我們更廣泛地思考OBE局限性的理論是比格斯(Biggs)和唐(Tang)的建設一致性課程框架(constructive alignment curriculum framework),該框架強調教學/學習過程以及評估。
與OBE一樣,建設一致性課程框架要求明確地說明預期的學習成果,它也將重點放在評估系統上,該框架要求學習者展示對預期學習成果的熟練程度,這一框架通過鼓勵學生參與適當的活動,而達到期望的表現水平。因此,建設一致性課程框架拓寬了OBE的理論基礎。然而,也有研究爭論到建設一致性課程框架排除了與情感和專業屬性有關的學習元素,這一理論框架可以被描述為建構主義的框架。事實上,即便OBE可以與建構主義理論相調和,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證明OBE已經超越了其行為主義起源。
因此,截至目前,我們可以這樣認為,OBE在第二個倡導周期之后,就再也沒有新的理論支持,與上世紀70年代相比,OBE的理論基礎依舊不夠堅實。與其說OBE是理論,不如說它是一種理念,它更接近于為職業精神的情感和復雜要素提供一個課程框架。
五、結語
成果導向教育理念自提出以來,已經經歷了兩輪實施、拒絕、復興的循環,倡導和批評的聲音一直交織在一起,時至今日,對OBE的應用和爭論依然在繼續。
在20世紀70年代,OBE被廣泛實施,隨后受到嚴厲批評,因為它將價值觀、洞察力和判斷力降低到了簡單的行為目標,并沒有將情感、社會、文化、美學和倫理學習過程置于教育的核心。
OBE在20世紀80年代復興,并在新千年之后被大力倡導,這次復興的重點是強調教育產品所帶來的好處,即課程設計、評估、方案評估和問責制方面明確的成果規范。我們在應用成果導向教育理念進行教學改革實踐時,應對這一教學理念的特點、不足和發展有深入的認識,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Spady W G.Outcome-Based Education: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M].AASA,1994.
[2]Cook D A,Bordage G,Schmidt H G.Description,justification and
clarification:a framework for classifying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in medical education[J].Medical Education,2010.
[3]Biggs J B.Teaching for quality learning at university:What the student does[M].McGraw-Hill Education(UK),2011.
[4]李光梅.成果導向教育理論及其應用[J].教育評論,2007(1).
[責任編輯 李愛莉]
作者簡介:楊志宏(1976.9— ),男,漢族,甘肅會寧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網絡與新媒體,成果導向教育(OBE)理念的起源、發展及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