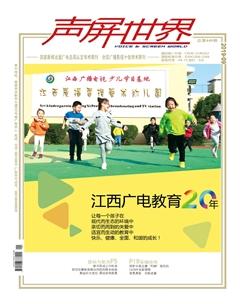媒體融合時代頻道頻率過剩的破解之道
賈軍
摘要:近年來,廣電傳媒在移動互聯網新媒體強勁沖擊下,面臨著競爭壓力日益加大、收視和收入份額持續下滑的困境,頻道頻率過剩的問題進一步凸顯,并在一定范圍內引發了一波頻道頻率關停潮。文章從分析廣電業內頻道頻率結構性過剩的現狀和原因入手,對頻道頻率整合的難點與焦點、機遇與路徑進行了思考闡述。
關鍵詞:頻道頻率? 過剩? 關閉? 整合
2019年以來,傳媒界有消息稱,天津進行媒體改革和跨媒體整合中關閉了國際頻道、高清搏擊、時代風尚、時代美食、時代家居、時代出行6個電視頻道;上海廣播電視臺對多個頻道進行重大調整,關停兩個地面頻道,娛樂頻道和星尚頻道合并成全新的“都市頻道”,炫動卡通頻道和哈哈少兒頻道整合成了全新的“哈哈炫動衛視”。廣電業內引發了新一波頻道頻率唱衰潮,頻道頻率過剩的老問題再度成為業內外熱議的焦點。然而,大批關停過剩頻道頻率的時機是否已成熟,的確是業界學界亟待思考和探究的一個課題。
頻道頻率結構性過剩的現狀
近年來,傳統廣電行業在互聯網新媒體和視頻網站迅猛沖擊下,受眾和廣告收入規模日漸萎縮,絕大部分要素資源和收入向央視、一線衛視與前幾位二線衛視集聚,弱勢衛視和地面頻道頻率的收入呈普遍下滑態勢,頻道頻率過剩的問題日益凸顯。據統計,到2010年,中國有4000家電視臺,頻道多達24000多個。目前頻道頻率結構性過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衛視頻道過剩。央視16個免費頻道全部上星,還有全國43家省(市)級衛視(含副省、市級衛視),其中真正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衛視有五、六個,一些排名靠后的衛視生存日漸艱難。二是專業頻道、頻率過剩。各級頻道頻率的定位和專業化水平不高,幾乎都是“小綜合”的節目結構,造成資源分散、內耗嚴重。據統計,目前國內有100多家付費頻道節目商,90%以上陷入生存危機。三是市、縣級頻道頻率過剩。多數市、縣級頻道頻率傳播范圍出不了所在地域的“一畝三分地”,節目制作水平不高,創收能力有限,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市、縣級頻道頻率,脫離了體制的“庇護”很難存活。
近年來,一些地方臺在創收能力不足、各種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關停了一些弱勢頻道頻率。2016年,深圳廣電集團的法治頻道停播;九江廣播電視臺的旅游文娛頻道關停;天津時代付費系列4頻道(天津電視臺占股51%)停播;TOM集團終止華娛衛視及其附屬公司運營。這大約是國內首次集中出現電視頻道自發退市的現象。2019年初,上海廣播電視臺關停了兩個地面頻道。據調研,一些中部省份的縣級廣播頻率處于關停狀態。
頻道頻率過剩的原因分析
1980年代以來,隨著電視機在國內普及,電視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廣電業歷史上曾先后掀起了三次“頻道頻率擴張潮”,奠定了廣電業現有的頻道頻率格局。一是1983年,中央確立了“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方針,在中央財力不足的情況下,依靠各級政府來完成電視播出、有線無線傳輸的省、市、縣三級基本覆蓋,直接促成了延續至今的“四級辦”格局。這是模擬技術、線性傳播的技術背景和傳統宣傳語境下廣播電視的發展策略及方式,在特定歷史時期對廣播電視普及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從1986年開始,國務院為了解決邊遠地區電視節目覆蓋難的問題,先后允許新疆、西藏、四川等部分省級電視臺通過衛星傳送電視節目,遂一發不可收,許多省級臺紛紛要求上星傳播,至1999年國內已有31家省(市)級電視臺悉數上星,形成了如今的衛視競爭格局以及集聚整合各種要素資源的“全國性平臺”。三是新世紀以來,國家在頻道頻率專業化和數字頻道、電視購物頻道方面出臺了一些政策,直接推動了新一輪頻道頻率擴張潮,各級廣電內部形成了新聞綜合、經濟、公共、影視、科教、付費等電視頻道與新聞綜合、經濟、交通、音樂、文藝等廣播頻率的“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如國家廣電總局于2003年發布了《廣播電視有線數字付費頻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試行)》(廣發辦字[2003]1190號),2005年7月發布了《關于加強廣播電視有線數字付費頻道業務申辦及開播管理工作的通知》,直接推動了我國付費電視頻道的開辦和發展,到2014年,付費頻道已發展到120套以上,覆蓋用戶近3500萬,收入近60億元。
從技術角度來說,頻道頻率的迅速擴張源自于傳統廣電傳播技術的普及和數字技術的興起;從經濟角度來說,頻道頻率擴張是中國廣電業的“黃金時代”(大約從1990年代后期到2012年)各級廣電媒體的收入、資產大幅增長和體量急劇擴大的產物,許多廣電媒體把擴充頻道頻率作為優化產業布局、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的重要舉措,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頻道頻率格局,就連一些縣級臺也申辦了好幾個頻道、頻率;從政策角度說,以政策為載體的行政力量始終是廣電業改革發展的主導性推力。
頻道頻率整合的痛點與難點
解決頻道頻率過剩的問題,涉及到政治、行政、社會、行業以及各級廣電內部多重制約因素。頻道頻率整合的痛點與難點主要體現在:一是因廣播電視的政治屬性,各級廣播電視臺整體上屬于事業序列,在運營層面事業產業處于深度混營狀態,國家曾明確深化事業體制改革中不搞大規模下崗分流,如大面積關停地面頻道頻率有丟失“宣傳陣地”之嫌。二是目前廣播電視臺的頻道頻率都是市場化、實體化運營,有的頻道頻率已實現公司化運營,對外合作、經營、債務、人員等方面歷史遺留問題多,在整合中容易產生某些法律糾紛,且整合成本較高。三是人員身份非常復雜,有事業編、企業編、臺聘、頻道頻率聘、部門聘、節目聘和勞務派遣等多重身份,其中的事業編也有全額、差額、自收自支等差別,如果大面積關停頻道頻率,人員分流安置的壓力大、成本高。如盲目將大量非編制內人員推向社會,還會給社會帶來很多不穩定性因素。
頻道頻率整合方面,這些年來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很多地方臺領導不愿意碰觸這個“燙手山芋”,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寄希望于國家出臺相關政策的行政力量。然而意味深長的是,互聯網作為一股巨大的“異己”力量異軍突起,徹底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傳媒行業邊界和格局,讓傳統廣電業的頻道頻率播出平臺迅速失去壟斷優勢而大幅“貶值”。特別是2016年,一些廣播電視臺在頻道頻率資源整體過剩、頻道頻率創收能力不足、臺內各種要素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收縮戰線、減少內耗、提升整體運營效率效益,關停了一些弱勢頻道頻率。由此可見,關停過剩頻道頻率的力量最終還是來自于傳統廣電媒體內部,隨著各級臺經營狀況的持續下滑,將會由被動而變為一種主動的行為,其實質是傳播技術革命的摧枯拉巧之力由技術領域擴張、延伸到廣電實體領域,又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釋放出來。
頻道頻率整合的機遇與路徑
目前廣電業必須把握時機順勢而為,抓住媒體融合和深化改革的兩大機遇,借助于來自外在客觀環境的推力,與內部活躍要素相互作用,來推進頻道頻率要素的整合及其結構的優化。深圳廣電集團關停法制頻道,天津廣電關停6個電視頻道的案例,已揭示出未來廣電業解決“大而全”“小而全”頻道頻率結構性過剩問題的某種路徑。
頻道頻率整合必須納入媒體深度融合的框架統籌推進。以互聯網及新媒體技術為主的新一輪傳播科技革命是傳統廣播電視超穩定的“常量”結構中最有力的“變量”,實質上已成了打破行業既定格局的顛覆性力量。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化時代的到來,使傳統廣電業的頻道頻率播出平臺失去了自然壟斷優勢,特別是讓一部分地面頻道頻率的重要性和平臺價值、產業價值大幅下降,甚至變成了“雞肋”。因此,廣電媒體的頻道頻率整合應該納入媒體深度融合的框架,與融媒體建設統籌布局,科學評估和確定各頻道頻率在全媒體傳播中的定位,統籌協調好頻道頻率播出端與移動端的關系,通過融媒體技術、業務平臺和“中央廚房”實現新聞采編、節目制作、播出平臺和終端等資源的優化配置,建立起與廣電媒體向融媒體轉型相適應的播出平臺結構體系。
頻道頻率整合必須在深化改革的“自我革命”中推進。如今廣播電視臺高度行政化的管理體制、運營機制和治理結構已越來越不適應于媒體深度融合的需要,特別是現有的事業體制、內部管理運營制度、激勵機制,嚴重不適應于移動新媒體。因此,負效及弱勢地面頻道頻率的退出和整個行業播出結構的優化,必須在深化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的“自我革命”中推進,在堅持“廣電媒體姓黨”和堅守主流價值觀的前提下,按照融媒體時代的要求和傳媒市場規律,建立符合現代傳媒和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治理結構及組織構架,布局并匹配資源,適度壓縮同質化的內容產能與頻道頻率資源來優化廣電制播結構,使臺內人財物等各個要素資源結構得到優化,進而全面提升廣播電視的輿論引導力、綜合傳播力和社會影響力。
頻道頻率整合必須通過市場大潮的“浪淘水洗”來推進。頻道頻率的結構調整和整合必須由傳媒市場供需平衡和廣播電視臺的經營狀況來決定,并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來實現。目前有些廣播電視臺的頻道頻率整合和結構調整仍帶有比較濃的行政色彩,包括讓經營陷入困境的弱勢頻道頻率向客戶端轉型,依然是傳統媒體的思維、做法。試想那些在傳統廣電業務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平臺及團隊,又怎么可能在新媒體業務實現“華麗轉身”?各級廣播電視臺內的頻道頻率整合必須經過市場的優勝劣汰,只有最強壯的頻道頻率才能生存下來。
(作者單位:山西廣播電視臺)本文責編:樂 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