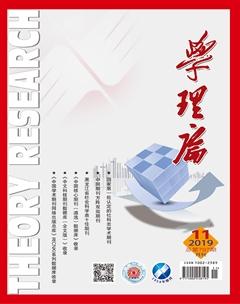形而上學的終結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路向
摘 要:“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哲學”之終結并不意味著現實意義上哲學的終結,形而上學的“本體之思”是人類擺脫原始和蒙昧的“理性之光”。然而,日益脫離感性世界的“理性”逐步失去了其生存根基,在這個“終結”的萌芽里生長出了“歷史唯物主義”新的哲學形態,這種全新的哲學形態在問題的來源、追問方式、思維特質、理論旨趣已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形而上學”,其“地基清理”式的“實踐”思維方式徹底動搖了之前“形而上學”的基礎。
關鍵詞:形而上學;歷史唯物主義;實踐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11-0054-02
從詞源意義上講,“形而上學”與“哲學”同義,某種程度上,亦是“哲學”的代名詞;從問題域意義去看,“形而上學”關注的問題亦是“哲學”關注的根本問題。那么,“形而上學”的“終結”是否意味著“哲學”的“終結”?人類是否還需要“哲學”?如果需要,這將是何種路向上的“哲學”?
這一系列的問題其實就是“哲學”自身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環節,而其中的“否定”正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必然,“否定”是為了更好的“超越”,在更高意義上的“肯定”。
然而,“哲學”不會“終結”,因為人類的“愛智”追求不會停歇,探索和追問的過程彰顯了“哲學”的生命力,人類面對的問題及問題之“源”是沒有盡頭的。抽象的理念懸設、概念推理和精神思辨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在開啟了人類的“啟蒙智慧”以后,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走下了歷史舞臺,歷史帷幕已然“終結”。其“終結”的命運并非邏輯必然,而是哲學發展的歷史結果。關于世界之存在的終極“理性”思考既是“哲學”誕生和發展的原因,也是促其陷入困境的“元兇”。
一、形而上學的終結
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提出并構建了西方“形而上學”基礎,使“存在”從“物我一體”“天人合一”的“混沌”中開顯出來,“智慧之光”照亮了“昏暗”,“現象”和“本質”區分開來,其中的“本質追問”就成了“本體論”殫精竭慮的思考對象,關于世界之存在的終極“理性”思考既是哲學誕生和發展的原因,也是促其陷入困境的“元兇”,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從古希臘巴門尼德提出“存在”問題,到柏拉圖的“理念論”和其后繼者亞里士多德建立了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形而上學”由此初步完成。
步入近代,以“資本”為原則的現代社會生活逐步形成和發展,笛卡爾與之相呼應,開辟了“理性主義”的主體哲學——一切思想來源于“主體”之“思”,根植于“主體的內在性”,“真理”是可以被擔保的,只要“我”發揮“我”的“理性”,就可以發現“真理”,知識的可靠性來自先驗的“理性”,從而“主體”設定“客體”的“主體性原則”確立,也由此造成了西方哲學“主客二分”難題:“主體”如何能“客觀地”認識“客體”?“客體”的“真理性”如何可能?經過休謨為代表的懷疑主義的一系列詰難,人類的知識大廈搖搖欲墜:真理性的知識是否存在?若存在,何以可能?若不存在,人類對知識的信仰將置于何種境遇?
德國古典哲學走在試圖“主客統一”的路上,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雖然捍衛了搖搖欲墜的知識大廈,將“本體論”或“存在論”問題轉向“知識論”路徑,為“理性”劃定了嚴格界限:“理性”不可“僭越”其“認識范圍”,否則將陷入“二律背反”。康德向人們宣告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果——終極真理不可知,作為事物本質的“物自體”非“理性”所能認識。“本體論”的“終極根據”沒有得到解決,“本體”被康德安放在并非人類理性可認識“彼岸”的“形而上”的世界中,問題依然存在,康德終沒完成“主客統一”,他在解決了知識危機的同時,又造成了新的危機:“主客二分”被更加深刻地分裂。
從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都走在試圖統一“主客二分”的道路上,最終在黑格爾那里以“絕對精神”在辯證邏輯發展中“回歸”自身,“絕對精神”統攝一切,實現了“主客二元”的“統一”。在黑格爾看來,世界終極的哲學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在哲學終于得以“圓滿”,形而上學的問題得以“終結”。然而,黑格爾面臨著一個其理論自身難以解決的悖論:“絕對精神”一方面要不斷地自我否定,向更高階段發展;一方面又陷入封閉和循環,所有的發展無非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異化”,最終還要回歸自身的“統一”。此外,黑格爾沒有意識到他的“絕對精神”實則仍然走在“形而上學”的道路上,統攝一切的神秘的“絕對精神”實則仍是“理性”的,并且脫離了現實。
在“理性”專制的哲學史上,“感性”一度失語,但從未被冰冷的理性徹底湮滅,一再地動搖著“理性大廈”:從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到愛爾維修反對“天賦觀念”,強調人的“感覺”經驗;從克爾愷郭爾高舉起非理性主義大旗高揚“人的存在”到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和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兩千余年“感性”與超感性的“理性”始終進行著不屈抗爭。
然而,這些抗爭要么對“存在”做了知性的理解,要么做了抽象的解釋,難以動搖形而上學的根基。問題的解決在問題形成之處,如若跳不出形而上學的問題路徑,就難以有實質性突破,正如懷特海所言,西方兩千多年哲學不過是柏拉圖的注腳。
二、哲學的實踐轉向
我們注意到,馬克思一反傳統哲學以追求最高原因和終極根據的形而上學的“本體追尋”,把哲學的視角轉向了現實、感性經驗世界。我們所要追問的是:離開探討“本體追尋”的哲學還是不是哲學?恩格斯認為不是哲學,是一種“新世界觀”,哲學從黑格爾那里已然到達頂峰并終結了,叔本華轉變以往的“理性本體”為“意志本體”,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但“本體”的消失帶來的結果是人類精神家園無處安放。
無處安放的結果要么走向宗教,帶來的可能是封閉和倒退,而宗教的基礎仍然是形而上學;要么走向藝術的直觀,正如雅克比、海德格爾提出的問題;要么走向實證主義(模糊了哲學與科學的分野)和實用主義(價值的失落、道德的淪喪和今天的社會危機),甚至有可能走向虛無主義。
進一步追問就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建立一定以現象之外的“本體”或“自在之物”為目標嗎?康德懸置了問題,黑格爾想要統一“主”“客”于一體,建立了最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找到了作為本體的“絕對精神”,但脫離了現實、成為封閉體系,這與他主張的辯證否定導致的發展相矛盾,體系自身摧毀了自身,形而上學至此終結。
哲學向何處去?黑格爾之后,現代哲學家們紛紛指向了“生活世界”,實現了從近代哲學到現代哲學的轉型。為什么要轉型?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的原因有二:一是這條尋找終極的路本身就不存在,是個偽命題,無非是思維的“怪圈”和陷阱;二是哲學在自身發展實現著一種戰略“暫時性退卻”,形而上的哲學的追問性思考的沖動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學終會復興;三是哲學本是追問“意義”之學,形而上學隨著科學的建立和技術的發展,已失去其自身意義,而所謂“意義”就是時代性,馬克思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援引黑格爾),脫離了時代主題的“哲學”,終會被“終結”。
如果說哲學以“本體追尋”為其主要內容,馬克思雖終結了傳統哲學以某種固定的“第一起點”為根據和原因的哲學,但并未放棄“本體追尋”。畢竟,沒有“追問”的哲學不稱其為哲學。應該說,馬克思所創立的“本體”就是“實踐”,是一種以現實世界和現實社會生活與人互動的“關系哲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說康德完成了從“自然為人立法”到“人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馬克思則發起了從“理性解釋感性生活”到“感性生活解釋理性”的“本體論革命”或“存在論革命”,在這場革命里,“形而上學”并沒有真的消解,而是以“感性現實生活”和“社會關系”為其“形而上”的追尋起點,以“實踐”為圓點構建起了新的哲學;又因為實踐本是開放的、發展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西方哲學史矛盾發展的一個環節,所以也是自我批判的,在批判中發展。因此,相對比傳統哲學那種封閉的體系,具有更強的革命性和活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扭轉了西方哲學的發展路徑:與康德把知識嚴格限定在經驗范圍內一樣,馬克思把哲學限定在以人為圓點、實踐為半徑的生活經驗世界。開創了嶄新的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或實踐唯物主義,正如恩格斯稱之為“新的世界觀”。
三、歷史唯物主義之實踐路向
革命一定是根基處的摧毀,變革一定是路向上的變革。在形而上學終結的萌芽里生長出了“歷史唯物主義”新的哲學形態,這種全新的哲學形態在問題的來源、追問方式、思維特質、理論旨趣已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形而上學”,其“地基清理”式的“實踐”思維方式徹底動搖了之前“形而上學”的基礎:在形式上否定了建立在以概念、范疇、理念的抽象的“形式邏輯”,代之以“歷史”的和“唯物”的“辯證邏輯”;在內容上又“揚棄”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自我辯證”式的空洞,填充了“實踐”的嶄新內容。
馬克思在“揚棄”黑格爾哲學的基礎上,沿著費爾巴哈所關注的“感性的人”的“人本主義”思路探尋,他發現費爾巴哈試圖重置被黑格爾所“顛倒”的世界,但卻以同樣抽象的“類本質”和“情感”代替了黑格爾那個神秘的、上帝般的“絕對精神”,走向了缺乏歷史感的“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歷史”和“現實”再次湮滅。
如果說“歷史”是人的實踐過程,那么“現實”是人的“生存場”。這個“生存場”體現為各種“社會關系”,人的本質只能從這個“生存場”中尋找,只能在“社會關系”中去實現。
“歷史”體現著“時間”,“現實”體現著“空間”,正是立足于這種嶄新的“時空觀”和“世界觀”,馬克思最終超越了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在對“本體論”意義上的“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認識論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和“機械論”的“揚棄”中,開辟了在本體和認識上以“實踐”為核心的“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無論在“本體論”還是“認識論”意義上都扭轉了“形而上學”的發展路向,開辟了“哲學”的實踐路向,最終成為破除和消解形而上學的突破點。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現實維度上立足人的現實生活,將哲學的世界觀從遙遠的“彼岸”拉回生活世界的“此岸”。馬克思以人的“對象性活動”,即“實踐”活動為突破,從人的“感性需求”在實踐中形成的“感性意識”為脈絡,將“哲學理性”還原為“生活現實”、將“知性問題”還原為“實踐問題”、將“主客二分”統一為“對象性活動”;馬克思深入到歷史中去,斷然否定了“理性”的“先驗”和“感性”的“直觀”,將形而上學的“理性”歷史消融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將割斷歷史的直觀式“唯物”重置于人的實踐過程之中。由此,“世界觀”成為“觀世界”,“人生觀”成為“觀人生”。由此,哲學與科學、理論與實踐得到統一。
收稿日期:2019-06-27
作者簡介:支立平(1978-),男,山西新絳人,當代知識教研室副主任,講師,碩士,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