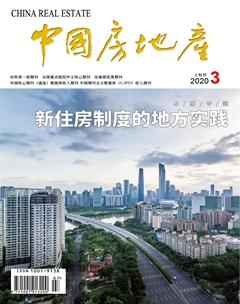遺囑繼承類不動產登記業務審查要點
王秋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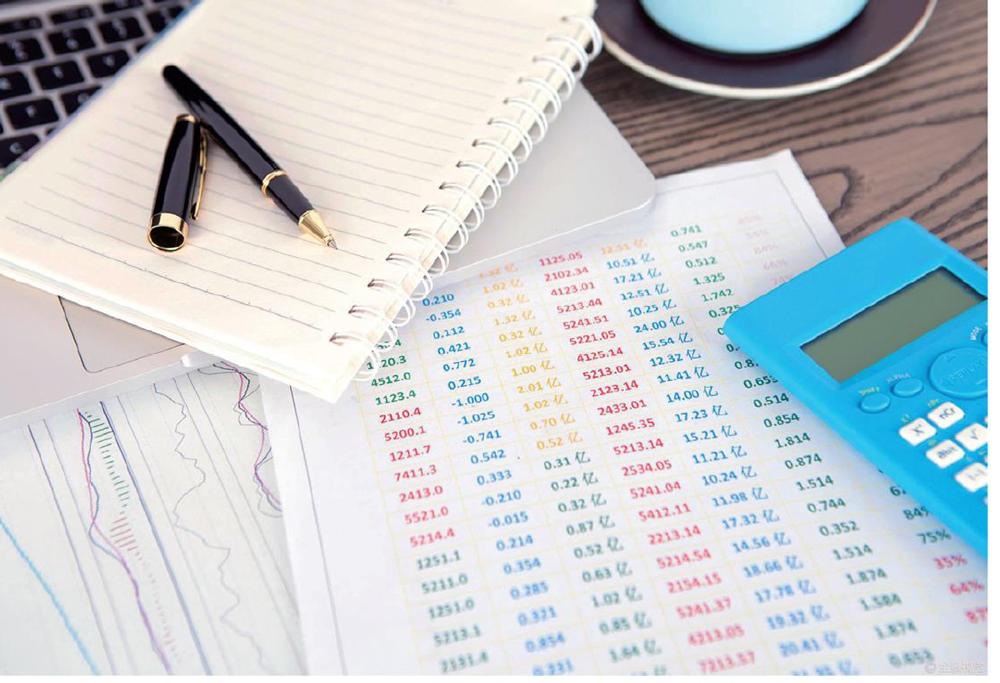
摘要:不動產登記實務中,基于遺囑繼承而申請登記的,鑒于遺囑的特殊性,其較之法定繼承更具審核難度,針對遺囑繼承類登記業務,從繼承人死亡事實的審查、遺囑效力的審查及繼承人資格的審查三方面闡述該類登記業務的審核要點。
關鍵詞:遺囑繼承;審核;不動產登記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1-9138-(2020)03-0044-47 收稿日期:2020-02-03
實務中,鑒于遺囑繼承較之法定繼承效力具有優先性,且因遺囑這一形式的存在,其在相關材料審核中對受理審核人員更提出了較高的注意義務,本文有意對持有遺囑申請不動產登記的情形中登記機構的審核要點及注意義務予以探討。
針對遺囑繼承,筆者以為可自三個方面總體上予以把握,這三個方面無外乎被繼承人、繼承人乃至遺囑這一繼承載體。首先,既然申請繼承不動產登記,那么繼承事實首當其沖應予以明確,即存在被繼承人死亡之事實。其次,鑒于遺囑繼承之效力優先于法定繼承,應針對遺囑這一載體之合法性和有效性予以審查。最后,在明確了遺囑之效力之后繼而展開針對繼承人之審查。
1 被繼承人死亡事實之審查
被繼承人死亡為繼承之開始,依據《不動產登記操作規范(試行)》(以下簡稱《規范》)規定,被繼承人死亡之證明材料包括:醫療機構出具的死亡證明;公安機關出具的死亡證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銷戶口證明;人民法院的宣告死亡的判決書;其他能夠證明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死亡的材料等;此項中醫療機構、公安、戶政及法院所出具死亡之證明材料為具有明確格式和出具主體的“法定材料”。然而,實務中許多繼承人或因非正常死亡、戶籍檔案未予收錄、死亡年代久遠等諸多原因難以取得上述4種“法定”證明材料,也即只能提供規范所規定的其他能夠證明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死亡的材料。鑒于前4項證明材料之形式和出具機構的特性,考慮其證明力,只需為必要之形式審查即可。
而針對其他證明死亡事實之材料則應予以重點核實,尤其是針對相關證明材料之出具單位其是否有權出具相關證明,其意欲證明的相關事實是否在其職責范圍之內,對此,登記機構僅需進行形式上的調查即可。如實務中,很多申請人提交被繼承人生前單位或社區居委會、村委會等證明材料意欲證明被繼承人死亡事實,對此項證明,登記機構應嚴格依據《規范》1.8.6.4規定:“受理后,不動產登記機構應按照本規范第4章的審核規則進行審核。認為需要進一步核實情況的,可以發函給出具證明材料的單位、被繼承人或遺贈人原所有單位或居住地的村委會、居委會核實相關情況”。予以去函核實或者當面核實,重點針對出具材料主體據以做出認定死亡事實的依據進行核查。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可知,居民委員會作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其任務中并不具有管理社區居民之戶政信息及出具相關死亡證明之職責,依據該法第3條第2項規定:“辦理本居住地區居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此條亦為統括性條文,自其內涵中并不能當然得出其具有出具死亡證明之職能,故而對于此類材料,其證明力是有待商榷的,尚需申請人提供其他材料予以佐證,以形成證據鏈強化被繼承人或遺贈人之死亡事實及時間。比如實務中當事人提交村委會出具的證明被繼承人死亡時間及死亡事實的證據材料,在進行核查之后發現,村委會據以出具此項材料之程序頗為隨意,基于村民之間人情社會之基礎,申請人、被繼承人與村委會相關人員相互熟識,其并無過多法律意識,對于材料出具也僅僅可能本著好意相助的善意為之。同時,有些村委會或居委會人員眾多,加之流動性之存在,村委會或居委會工作人員對于出具材料之被繼承人可能根本不認識或熟識。有些村委會便要求申請出具證明之主體尋找證明人或者見證人,通過見證人之敘述或描述出具相關證明材料。參照民事訴訟證據規則,此種證明材料其本質應為證人證言,然而對于證人是否具有舉證能力,其與當事人是否具有利害關系,這些皆需進行排除。而此種工作可以說完全超越了登記機構受理人員之能力和職責范疇,如若要求受理人員繼續順藤摸瓜對相關見證人進行調查核實,一則無法律和行政法規依據,二則有強人所難,將類似司法人員之職責加諸在受理調查人員之上,以現今我國登記機構之水平和條件,無異于削足適履。故而,此情形下,在相關證明不足以支持被繼承人死亡事實和時間完全真實可信的情形下,登記機構自然應要求申請人提交其他材料予以佐證,以形成相關證據鏈,相互印證,以充分證明待證事實。實踐中,此種證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種:村委會、居委會出具證明材料、單位或者所在社會團體、黨派等出具相關材料、被繼承人人事檔案等證明材料、被繼承人或遺贈人喪葬服務相關材料(如喪葬服務協議等)、墓碑照片、火化證等。
2 遺囑之合法性和有效性審查
應排除遺贈扶養協議之存在,再對遺囑之合法性審查。筆者以為,應從處分財產之歸屬、遺囑人之自身條件對遺囑之影響、遺囑之形式要件以及影響遺囑之瑕疵要件幾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把握遺囑是否有效,財產歸屬上,其遺囑處分財產是否為遺囑人所有,登記機構自登記簿記載和權屬證書則可予以明確。立遺囑之遺囑人自身條件上,在立遺囑時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其所立遺囑是否為其親自所立并代表了其真實意思表示,這些均影響遺囑之效力。然而鑒于遺囑人去世之事實,對于前項影響遺囑效力之條件審查,應重點取得全部繼承人之認同,因僅憑遺囑繼承人之一面之詞,其證據效力難免有所局限,而其他繼承人是否存有異議,尤其是對與遺囑是否有效存在爭議乃是登記機構必須掌握之事實,故而應對遺囑人立遺囑時自身要件是否成立予以分別詢問全部繼承人并取得書面確認材料。
其次,針對遺囑之形式分別審查。依據我國《繼承法》之規定,遺囑分為自書遺囑、代書遺囑、公證遺囑、錄音遺囑和口頭遺囑5種形式,其因形式不同有效條件亦各有千秋。
自書遺囑。應重點把握其是否為親筆書寫,是否注明年、月、日。對于筆跡的把握,可提取登記原始資料中記載筆跡予以比對,若因年代久遠,無從查證的,可要求遺囑繼承人提交足以比對的筆跡樣本,如人事檔案機構、社保機構提供的由被繼承人簽名的筆跡樣本等。此外,若自書遺囑并非單獨以獨一文書形式存在,如其在個人日記或者信件等記載了待其死亡之后處分財產的意圖,應重點對于其處分財產內容是否明確,意圖十分清晰予以把握,否則極易造成糾紛,同時針對此類遺囑亦應重點就其他法定繼承人對其形式是否存有異議取得其意見,倘有異議則不應予以受理。實務中尚有一種情形,其因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而產生,遺囑以打印之形式存在,其上雖具有處分財產之意思表示,亦有被繼承人之親筆簽名,然而此種形式之效力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存有爭議,故而針對此類自書遺囑,其他全部繼承人之意見亦顯得尤為關鍵。
代書遺囑。其文本形式上的代書人、見證人以及遺囑人簽名是否完備,時間是否明晰,有無涂改痕跡均應仔細查驗。對于見證人的數量較易明確。而對其是否屬于《繼承法》第18條規定的除外范圍,對于此項審查,有無行為能力可通過現場審查把握、是否屬于繼承人、受遺贈人亦可通過相關親屬關系證明予以排除,而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則較難把握,因民事實務中,法律關系錯綜復雜,見證人與繼承人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并非僅憑相關證明便足以準確明晰的,而且登記機構對此亦無判斷能力,故而是否存有利害關系,亦應取得全體法定繼承人無異議的書面確認。
錄音遺囑。參照代書遺囑,應對于其錄音之清晰程度,遺產標的及處分意愿是否清晰,見證人是否符合法定條件予以把握,鑒于不動產登記的形式要件要求,錄音其因不具備書面之形式,故而可要求申請人對錄音遺囑提供文本備份予以方便核查。同時,鑒于錄音中主體的明確存在一定難度,在其他繼承人存有異議的情形下,應予以明確告知至司法機構予以解決爭議后再行申請登記。
針對口頭遺囑,鑒于不動產登記之特殊性,固定申請文本,明確申請人之意思表示之要求,若申請人以被繼承人留有口頭遺囑為由申請登記,登記機構應重點對見證人予以詢問,并取得全部繼承人之無異議之意見。顯然,在全部繼承人無異議的前提下,見證人之見證作用似也并不明顯了,其類似于全部繼承人對于遺產之處分,但卻因口頭遺囑之存在而阻斷了除去遺囑繼承人外其他法定繼承人繼承之條件。基于還原真實事實的初衷,理應將口頭遺囑由見證人予以書面化作為登記材料予以收取。
公證遺囑。遺囑繼承人未辦理繼承權公證的情形下,應對于是否存在其他后續公證遺囑,必要時可要求其提供遺囑公證機構出具的唯一一份證明材料,但是鑒于實務中遺囑人可能存在異地進行多份遺囑公證的情形,且中華遺囑庫之建設尚不完備,是否存有后續公證遺囑的,實則較難把握,而很多情形下,這些遺囑便可能掌握在其他繼承人手中,故而可見,在整個遺囑審核中全部繼承人之書面意見便尤為重要。
除此之外,尚需把握幾個問題,遺囑人所立遺囑是否存有多份?其所立多份遺囑的效力優先級及其內容是否存在沖突?遺囑是否附有義務?繼承人是否履行相關義務?是否存在需保留必要份額之主體?這些問題均關乎遺囑是否有效,雖不似前文所述情形,倘若存在則直接導致遺囑全盤被否定,這些問題若存在異議則構成遺囑之效力瑕疵,若不加以仔細審核,登記機構亦難逃脫責任。然而,針對遺囑之形式要件、遺囑人之自身要求、遺產歸屬以及其他影響繼承主體認定之情形全部繼承人是否尚有異議,可以說取得全部繼承人之書面無異議確認可謂完全之策,任何疑問和阻礙都可以通過此項加以解決,比如第一個問題是否存有多份遺囑,比如遺囑繼承人持有一份自書遺囑,而其他繼承人又均無異議,自可不經相關證明材料加以確認遺囑為唯一一份。再如是否履行了遺囑所附義務,繼承人無疑為最佳判斷主體,再如是否存在缺乏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繼承人需保留必留份情形,繼承人均具有發言權。但對于內容是否存在沖突的,可通過多份遺囑內容自主判斷,沖突的公證遺囑應優先于其他遺囑類型,屬于其他類型遺囑沖突的,應以時間在后之遺囑優于在先之遺囑,故而對于文本時間之把握便極為關鍵,然而出于時間之被篡改之可能性,登記機構應在詢問中明確告知相關申請人提供真實有效材料之義務,并明確告知喪失繼承權之情形,同時亦應征詢其他繼承人意見,綜合判斷。
此外,尚有一種特殊情形之遺囑,其形式可能涵蓋自書、代書等以上5種情形,但其立遺囑人多為夫妻雙方,即由夫妻雙方共同所立,通俗稱其為共同遺囑。此類遺囑之效力如何確定?在共同遺囑人全部死亡之時其爭議不大,但若存在一方去世而另一方尚存世而相關遺囑繼承人據以申請登記時則亦產生爭議。實務中存在持否定共同遺囑效力之觀點和承認其效力之觀點,筆者以為針對此類申請情形,應把握遺產之共有形式,若財產可按份劃分的,應依據生者和逝者各自所屬份額,構成共同遺囑之部分生效,而若為共同共有,鑒于遺產并未明確劃分份額,其財產之分割亦應由全部共有人共同為之,且其共同遺囑已經明確表明共同處置和安排之意圖,若此處由生者對共同共有財產之處置做出變更或者撤銷,則導致違背逝者意圖,故而在針對因共同遺囑提出申請時,首先應把握遺囑人死亡情況,其次明確財產共有情形,未明確的則為共同共有。針對財產為共同共有的,在尚有存世一方時,則其共同遺囑當尚未生效,登記機構應予以拒絕受理。
3 繼承人之繼承資格審核
審核死亡事實及遺囑之生效要件后,最后一個環節便是針對繼承人之審核,其關鍵在于其是否具備繼承主體資格,而此種資格亦包括普適性的資格,即是否為繼承人之一,此種判斷可據以申請人提供的親屬關系證明明確。而除去普適性資格之外,尚具有一種除外資格,即《繼承法》第7條明確規定的喪失繼承權之情形:“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一)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二)為爭奪遺產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三)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四)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的”。但是此種除外情形由當事人自我舉證似無可能,故而亦應取得其他繼承人之無異議書面材料,以排除遺囑繼承人存在喪失繼承權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