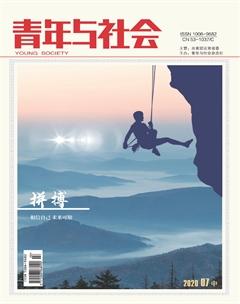充分發揮檢察監督職能,開創檢察公益訴訟新局面
王甜

摘 要:檢察機關應當在法制改革攻堅的當下,把握公益訴訟新職能,坐穩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伴隨反貪、反瀆兩個拳頭職能的轉隸,檢察機關失去了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利器。在公益訴訟這個新職能初展矛頭之時,將公益訴訟納入檢察職能,充分發揮代表國家公共利益的檢察權,對公益訴訟的有力推進和檢察職能的有效發揮是雙贏的。文章針對公益訴訟案件的立法、訴訟程序和辦案權限等方面進行討論和反思,試圖在辦案模式、豐富職權內容等方面找尋讓檢察公益訴訟更具實踐性的新思路,目的是想在通過公益訴訟有效維護公共利益的同時,讓檢察機關利用公益訴訟開創檢察監督新局面。
關鍵詞:公益訴訟;法律監督地位;檢察權;訴訟程序
2018年2月25日,人民檢察院反貪污、反瀆職“兩個拳頭產品”徹底劃出檢察職能。人民檢察院檢察權從偵查權的一家獨大,發展為以批準逮捕權和提起公訴權為主的刑事檢察權占領高地。但我國《憲法》第134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以根本法形式明確了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機關”的根本屬性。新形勢下,公益訴訟因具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性質,成為近年法治發展的重要焦點。在反貪污、反瀆職兩個重要檢察權轉隸后,人民檢察院應當將挑戰轉化為機遇,握住公益訴訟這把新刀刃,利用公益訴訟重新站穩“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
一、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現實狀況
(一)缺少足夠的立法支撐
(1)無統一的《公益訴訟法》
關于公益訴訟的定義一直存在爭論,但在其本質上是解決“公地悲劇”的一種訴訟手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規定:“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擬得公益訴訟......”該解釋相對比公益訴訟的發展歷程,其實際是給予了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較明確、范圍較廣的訴訟內容。
但實踐中,在文物保護、網絡安全、歷史英雄人物名譽保護等各方面也發生了許多熱點公益訴訟案件,其在文化和資源上的損失是單純的經濟賠償不能彌補的。但至今為止,仍沒有一部統一的關于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受案范圍的明確法律條文,實踐中公益訴訟案件也不僅限與上述法律法規中的規定范圍,這使得檢察機關在辦理公益訴訟案件時往往要根據案情在不同法律部門中探索合適的法律依據。
(2)無立法保障檢察公益訴訟的介入權
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的形式包含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主要依靠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收集刑事案件證據,所提起的公益訴訟對刑事案件依賴較大。對于單純的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目前檢察機關案件線索主要依賴線索舉報和走訪,極大限制了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的案件范圍。原本公益訴訟案件線索多是來源于職務犯罪偵查、審查起訴和控告檢察活動,但在目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背景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機構轉隸后,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案件來源不足的問題也會更加突出。但在立法中,并沒有實際賦予檢察機關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等強制性措施,也沒有確定相關行業行為是否合格的資質和能力,檢察機關對于公益訴訟案件的偵察權也局限于《刑事訴訟法》、《兩高》的部分規定,這給予了檢察權運行過程很大的被動性。
(二)程序適用上的矛盾
(1)前置程序弱化了檢察機關公益訴訟職能發揮
《兩高》規定民事公益訴訟應當依法公告三十日。但是在刑事或行政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是否需要對民事公益訴訟進行訴前公告法律沒有明確說明,實踐當中限于刑事案件辦理期限的要求,在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時一般也沒有公告程序,倘若進行訴前公告,那么勢必要拉長訴訟準備時間,期間也必然會出現證據滅失、損害擴大或者行政機關礙于訴訟的履職行為,從訴訟價值來講,這樣的訴前公告又顯的多余。
《兩高》第二十一條將檢察建議作為行政公益訴訟必要的訴前程序,以督促行政機關履行職責同時緩解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在公益訴訟上的關系,但對于行政機關而言,訴前檢察建議督促是一種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外部壓力。(2)訴訟程序沖突制約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的效果
《兩高》的規定:“人民檢察院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進行監督,”那么按照《兩高》規定,提起上訴的人民檢察院就有了對上一級人民法院判決的監督權,但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應當采取的是“平級對抗”原則,所以兩者之間的規定相矛盾。《兩高》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上訴”,也與“抗訴”不同,雖然“上訴”一詞使得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與刑事訴訟相區分,但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檢察院對刑事和附帶的民事公益訴訟判決裁定均有異議,在一張訴狀中,應當如何使用“上訴”與“抗訴”,刑事案件的“上訴不加刑”原則是否同時適用于公益訴訟案件,這些問題還需斟酌。
現行的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多是先刑事后民事的特征。對于在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對于是否附帶民事訴訟是有選擇性的,若選擇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方式,則可能會造成民事公益訴訟對經濟賠償的過度追求。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引發的民事訴訟分別由檢察機關與被害方雙方掌握主動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無論是責任追究還是經濟賠償基本都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另行提起單獨的民事公益訴訟就有可能會造成個案上的不公。
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內容主要是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不作為,在行政公益訴訟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后,對損害公共利益方的實際執行權由誰掌握,又如何監督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合法、合理性,這些問題在法律中同樣尚不得知。
二、對公益訴訟機制發展的新期許
(一)設置獨立的公益訴訟檢察官
伴隨部分檢察人員轉隸,成立監察委,檢察機關“員額檢察官”和“捕訴合一”兩種新形式逐步上線。現如今,在我國的檢察機關辦案方式里一般采用系統輪案制度,也包含檢察官專案專辦。比如未成年人案件,規定由指定未成年人檢察官專門辦理。在公益訴訟方面,檢察機關主要由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負責,但是刑事訴訟與公益訴訟案件存在交叉時采用“1+1”(公訴部門與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就刑事犯罪和檢察公益訴訟分開辦理,共同出庭,各自參與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或“2合1”辦案模式(由民事行政部門集中統一辦理)。在公益訴訟案件數量提升,辦案質量和要求更嚴格的情況下,可以在輪案制度基礎上,采用與未成年人案一樣的專案專辦的模式。這樣即能提升公益訴訟案件辦理的專業化水平和效率,更能有效避免對于一個案件線索在界定罪與非罪上的模糊而導致的辦案權限劃分不清問題。
(二)賦予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獨立職權
任何一種制度創新都存在著路徑依賴問題,從現有的制度傳統中出發進行制度改良和創新也最能取得成功。只剩下“一張嘴和一支筆”的檢察機關在應對公益訴訟時明顯缺少“武力”支持,從給予檢察機關權限上講,為增強檢察權在公益訴訟的“剛性”,在立法上應適當的賦予檢察機關對于公益訴訟案件在調查取證、保留證據、強制措施等方面的權限。因為公益訴訟實質上是兜底性的,在有關組織、單位沒有提起訴訟時,經過訴前程序檢察機關才可提起訴訟,只有配備有力權限的檢察機關才能在“兜底時”做到對公益訴訟的全面、深入、有效。
但在檢察機關對公益訴訟案件線索進行干涉時,應當避免檢察權的過度干預,嚴格區分違法違紀行為和犯罪之間的界限,避免將公益訴訟案件無條件的過度到刑事案件。無論是涉及民事公益訴訟還是行政公益訴訟,建議應當以行政手段優先使用,必要時檢察權提前介入,在遵守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督促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檢察監督職能。
(三)應訴資格的適格性
目前,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是以“公益訴訟人”的名義參加庭審活動。公益訴訟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國家、社會的公共利益,其實質與“公訴人”公訴活動目標一致。“公益訴訟人”雖然能凸顯出“公益訴訟”這個責任特征,但卻忽視了“檢察機關”這個代表國家的特殊主體身份,將其與可以提起公益訴訟的有關單位、組織和個人的功能定位相混淆。公益訴訟的職能是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權行使的一個具體表現,其與刑事、民事、行政訴訟相同,都是檢察機關訴訟職能之一,代表的都是國家、社會的公共利益。檢察機關在對外形象、實質職責上都是有統一定位的——法律監督機關,以“公訴人”的名義統一進行訴訟活動、提起公益訴訟,更容易把握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者”的定位和形象,也更能代表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的職責和訴訟追求。
伴隨我國法治體系逐步完善,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會伴隨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逐步豐富檢察權內涵,以應對來自于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挑戰。公益訴訟顯然是當代檢察院開啟新里程的重要利器,是坐穩法律監督地位的新手段。現有對公益訴訟的立法規定自然有其必然的道理,但在未來可預見的發展路途上,我們仍需要就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進行不斷的完善。
參考文獻
[1] 田凱等.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立法研究[J].中國檢察出版社2017,8.
[2] 于文軒,楊勝男.論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訴前程序[J].中國應用法學,2019(1)68-80.
[3] 石曉波,梅傲寒.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檢視[J]. 政法論叢,2019:30.
[4] [英]約翰·斯普萊克.英國刑事訴訟程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5] 王玄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和檢察機關的發展[J].人民法治,2017(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