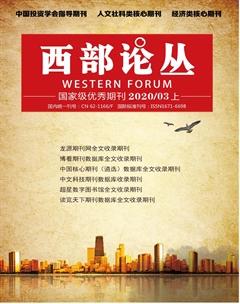彝帶彝路
普艷 朱杉杉 王新 王金衢 江津 楊亦蘭
摘 要:“要想富,先修路”,在現代經濟發展體系中,“路”作為重要的基礎設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調研以五街街道(南景線的一段)為中心,向四周支路分別延向筆掌箐、老五街和衣渣拉村。一個民族的文化集中體現在民族節日及其慶祝形式中,而結婚作為一個人人生中的大事,更是需要一場隆重的儀式感,因此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就有了具有強烈的特色的婚俗。本文就以南景線沿線四個村婚俗的發展變化分析,看通村公路對民族文化的影響。
關鍵詞:公路;民族地區;婚俗變化
南景線基本情況:南景線在修于上世紀末,由土路逐漸硬化成石頭路,再到如今的柏油路,期間經歷了三十多年時間。2016年,因需要在五街鎮安裝風力發電設備,又對道路進行過加寬。通往筆掌箐和衣渣拉村的支路歷史較短,都是近四年內新建成的,舊五街因為是老的五街街道地,所以通往舊五街的道路修成的也相對較早。
一、認識方式
彝族地區婚煙實行一夫一妻制度,青年人大多婚煙自主,很少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過去青年男女一般通過聚會而相互認識,從而自由戀愛。說到這不得不提一下“姑娘房”,彝語“移堵黑”,“移堵”意為“睡覺的地方”。女孩白天與父母一起勞動,晚上便相約姐妹到房中過夜,其間她們點起火把,一起紡麻繡花,小伙子則可以到姑娘房與看中的姑娘唱調子、聊天、傾訴愛意。彝家女孩熱情大方,她們會在趕會和唱歌時主動邀請心儀的男子到姑娘房中玩,并為意中人做晚飯,和第二天的早飯。夜里男孩和女孩手牽手和衣而眠,輕聲細語互訴衷腸,但他們遵守部族傳統,絕不越雷池半步,否則會受到長輩責罰并且難以立足。早上男孩悄悄出門帶走女孩頭晚準備好的飯,并留下點錢物致謝,情投意合者會約好再見,若雙方無意便不再見面,這種純潔的“共眠”會持續到女孩出嫁為止。姑娘房實際上的意義是年輕人談情說愛的場所,歷史悠久的彝族人把到姑娘房中玩稱為“串姑娘房”,結了婚的男女不都不能再到姑娘房。這種古老習俗是母系社會男女走婚的遺跡,它浪漫的內容和自由的形式體現了彝民族戀愛自由、尊重婚姻的婚戀觀。
小伙子住房是那些只有兒子沒有女兒的人家準備給兒子的,離家稍遠。小伙子可約村里年齡相當的同伴共享,親兄弟見則需要避讓,在節慶、趕會的日子由于去了姑娘房,所以這個房間空著的。平時則是小伙子們在一起聊天的場所,夜里也會相約去上山燒蜂或者狩獵。
而如今互聯網時代,姑娘小伙的認識方式不再拘泥于傳統的一套,“姑娘房”則作為非物質文化財產成為了旅游觀光點。
二、婚禮儀式
姑娘小伙互相看中之后,就請媒人提親,第一次請村里口才較好的人和幾個親戚去提親,準備酒,其他的根據自己的家庭情況定。女方家如果答應就喝男方家帶來的酒,不答應則不喝這酒。成了之后就到訂婚環節,雙方的親戚朋友們聚在一起商量正式辦酒的日子,通常是男方家帶上酒等去女方家商量,女方家舅舅和叔叔們出席。
到第三階段正式辦酒,結婚選在雙(偶)日,忌單日。新郎不親自去迎親,討親和送親的人必須成雙成對。迎親隊在女方家和女方家族成員及親友共同吃一餐晚飯,范圍小,儀式簡單,不請外客。飯后,女方家長在家族內找一名伴娘,另安排4-8人送親隊員。新娘著裝和往常無異,也沒有特殊標志。時間宜晚不宜早,早了急于求成之嫌,有損女方面子。給送親隊安排好住宿后,新郎新娘在三對男女青年的陪同下吃夜飯,彝語叫“滿宗著”,直譯為“吃老年飯”,相當于漢族的喝“交杯酒”。吃了這餐飯,意味著新郎新娘已成家立業,告別青年時代,進入了老年人行列,不能再參加跳歌會了,肩負起家庭和社會責任。
回門也擇雙日,早去晚歸,不在新娘家過夜。回門時新郎的父母、哥嫂均陪同,人數仍須配對,而且要和送親人數相等。線路照送親對走過的原路回去,不能另走一條路,新娘在前,新郎在后,保持一定距離,按傳統思想,這樣才顯得穩重。
現在的婚禮則有所不同,女方嫁到男方家,辦酒時間為兩天,第二天由父母親戚朋友送親到男方家,有些則只請要送親的親戚朋友吃一頓中午飯下午就去男方家。如果遇到同一天有多場婚禮,新娘子走的路也有講究,同一條路走得早的人會有好運,走得晚的那個對婚煙不利。新娘子來到男方家之后,新郎新娘由新娘的長輩(一般是舅媽)帶領著去一一敬酒,熟悉新娘的長輩。等到所有客人都吃完晚飯,最后就擺一桌,給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及其同齡的朋友們,讓雙方的朋友互相熟悉,這個時候不會有長輩在場。
總體而言,婚禮的形式在逐漸淡化的趨勢,問及村民原因時,大部分人都認為傳統婚禮過于繁瑣;一方面則認為經濟負擔過重,同時大辦也過于浪費;另一方面婚禮的社會功能在降低,以前辦婚禮的地方不僅是作為親朋好友祝福他們,還是一個與平時許久未見的親戚們交流感情的好時機,而現在基本家家戶戶都有摩托,家庭條件較好的還有小轎車,出行方便,與親朋好友之間平時也可以經常用電話聯絡。所以婚禮儀式變得精簡辦酒人家的經濟條件是一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隨著社會和時代的進步,村民自己本身對自己文化發展價值做出了取舍。
三、婚姻圈
在筆者采訪的十六戶人家中發現,35歲以上的那一代人很大一部分是同村通婚,少數在五街鎮下的其他村委會。由于五街鎮下的很多村基本上都是同姓聚居,也有很多同姓結婚,只要沒有血緣關系,同姓通婚是可以的。五街鎮上除彝族外還有少部分的漢族,彝族和漢族之間通婚,不存在什么歧視現象。
而現在年輕的一代(以90后為主),外出求學、務工使婚姻圈范圍變得很大,從同村到外省甚至外國人,真正實現了地球村。2008年有一批外地人來開發森林資源,時間較長,一部分人選擇和村里的姑娘結婚,在項目結束后在這里安家立業,也有一些本地姑娘回丈夫的家鄉;在調查的村里最遠的有一個通過打工認識并嫁給一個外籍人士。
四、結語
從秦朝的馳道、直道,到現代的公路、高速公路,人們的腳印隨著道路交通新格局的出現踏遍了大江南北。當公路由從外延延伸至越來越遙遠的少數民族山村,人們就漸漸發現外來因素正在一點點滲透進久遠的區域文化因素中,不僅是接受的被動關系,更是農村發展的主動關系。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在全球化的沖擊下處于非常開放的大環境中,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少數民族文化自身具有脆弱性,在發展過程中很容易消失,因此,適時調整民族文化的傳承方式,使文化發展和傳承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發展,讓文化得以綿延不絕傳承下去。
參考文獻
[1] 楊甫旺.楚雄民族文化論壇:第8輯[J].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12.
[2] 翁乃群.南昆八村:南昆鐵路建設與沿線村落社會文化變遷(廣西卷、貴州卷、云南卷)[R].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3] 陳國雄,闡貴福.濱江村落的崛起——有關寧六公路與泰山新村的故事[A].公路運輸文摘,2001(4):14-15.
[4] 黃國建.云南楚雄至南華一級公路投資可行性與建設模式分析[C].黑龍江交通科技,2012,224(10):122.
[5] 鄒海霞,楊文健.高速公路項目嵌入少數民族村落的影響研究——基于桂中三個村落的調查[A].廣西民族研究,2014,116(2):14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