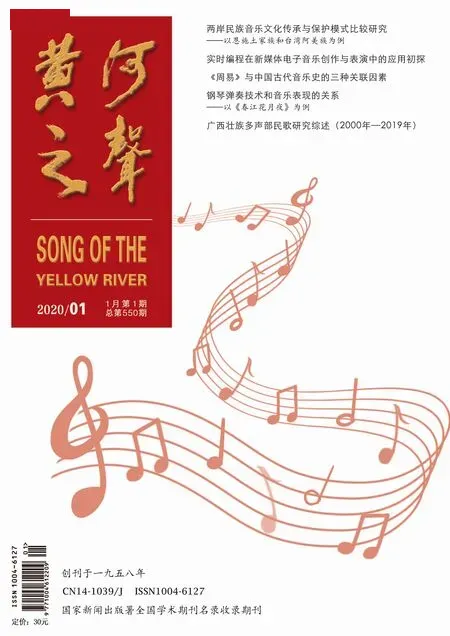一腳在古典,一腳在現代
——看舞蹈屆的“騎墻派”
孫繼黃 (中國藝術研究院)
“騎墻派”三個字,聽起來似乎就帶著一絲貶義的意味,人們常把那些立場不堅定的人稱為“騎墻派”,他們處事往往猶豫不決或者兩邊討好。可是筆者在這篇文章里提到的“騎墻派”并非此意,而是僅僅從字面意出發,看看舞蹈界中那些跨立在不同風格、不同舞種之間的舞蹈家們。
說起近年來舞蹈屆的“騎墻派”,筆者想到了年齡比較小的華宵一,她是古典舞領域“青年舞蹈家”。在很多人心中,她就是兩千多年前漢代女子羅敷的化身,“細綺為裙陌上采桑、蹁躚舞姿亭亭玉立”。她也是一位紅唇癡心女的代表,“閨中少婦多思愁、輾轉騰挪皆有情”。這個以《羅敷行》一戰成名的女孩憑借之后的《水月洛神》、《戈壁青春》等經典舞蹈,成為了今天人們口中的“古典舞青年舞蹈家”,說她是古典舞界的個中翹楚絕不是恭維之詞。
就在人們已經默然認可華宵一在古典舞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時,她卻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另一條更加現代化的道路,就像當年的羅敷出人意料地“懟”了使君一樣,華宵一也不按常理出牌,推翻了自己的人設。2017年10月,華宵一帶著她傾心準備的《一刻》盛宴,在北京保利劇院請觀眾品味她“古典——現代”的跨界大菜,筆者便從其中品出了一些復雜的滋味。
創新立足于現代
早在華宵一之前,就有一些優秀青年舞蹈演員開始嘗試突破自己在古典舞領域取得的成就,帶著自己的思維和身體步入現代舞的發展中,并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績,她們算是較早一批跨立在古典舞與現代舞之間的“騎墻派”,比如王亞彬。但凡是和舞蹈打過交道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她的古典舞經典作品《扇舞丹青》。除卻舞蹈專業的觀眾外,絕大多數的普通觀眾對她的熟知主要是通過電視劇的媒介,《鄉村愛情》中的“王小蒙”、《推拿》中的“金嫣”,這些角色的成功塑造是王亞彬從舞蹈跨向影視之路的最好證明。但是王亞彬并沒有囿于第一次轉型帶來的明星光環和經濟效益中,她依舊選擇回歸較為小眾的專業舞蹈藝術,只不過這一次,她開始用現代舞的方式找自己的路,于是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亞彬和她的朋友們”這個品牌一系列的精彩演出。
還比如唐詩逸。從《碧雨幽蘭》摘得“桃李杯”古典舞少年組金獎到《鄉愁無邊》拿下古典舞青年組的金獎,一路披荊斬棘的唐詩逸一步一步奠定了自己在古典舞表演領域的翹楚地位。在《大夢敦煌》中她用出色的表演牢固確立了其女一號的位置,因此也有了“鐵打的月牙”這一稱號,人們通過這個作品看到了蘊藏在唐詩逸身體中那個出色的民族舞表演者的身影。在近幾年火熱的電視節目《武林爭霸》中她更是用爵士舞《博物館之夜》、倫巴《秋》,以及現代舞《我的愛》、《魔鏡》和《天空》等作品展現了這個優秀舞者身體的多種可能性以及不斷想要突破自我的創新性。所以當唐詩逸推出了一臺她參與編創并領銜主演的作品《唐詩逸舞》時,觀眾也就不會為她這次用現代對話傳統的行為感到詫異,而是對她在不斷突破不斷探索的實踐中交出的這份作業表示贊許和認可。
因此當華宵一選擇大膽地沖出古典舞身體,探尋新的現代舞表達方式時,我們也應當報以同樣贊許的態度去支持她去認可她。因為創新乃是藝術發展的活水,創新不僅體現在藝術作品中,也體現在藝術家不斷超越他人與不斷超越自我的內在革新中。前有齊白石先生的“衰年變法”如蛹化蝶,變出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新天地;今有青年舞蹈家前赴后繼地突破自己所熟悉的身體語言,她們在不斷拓寬自身視域的同時也為舞蹈藝術注入了發展所需的創新力和生命力。華宵一作為古典舞表演領域的佼佼者敢于去突破自己的既有人設,敢于從不斷演繹的既定模式中走出來,足以證明她是有膽識有勇氣的。她塑造過美麗智慧的羅敷,但她不是羅敷,她是華宵一;她表現過思怨癡情的閨中女,但她不是閨中女,她是華宵一。在舞臺上的這一刻,她沒有去演別人,“她”就是她,“她”是一個有華宵一態度的角色,她就是有角色思維的華宵一。這一刻,這個具有勇氣的青年舞者值得我們為她點贊。
發展扎根在古典
在肯定華宵一于《一刻》中表現出的從古典舞跨向現代舞,從他人轉向自我的巨大勇氣的同時,筆者內心也有一些困惑,即中國古典舞留給舞者的發展空間真的就如此狹小嗎?以至于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古典舞科班出身的優秀舞者選擇跨界去現代舞中解放身體、尋找自我,選擇邁上古典舞與現代舞之間的“院墻”。于是筆者仔細梳理了幾個有代表性的跨界舞者的發展之路,伴隨著對“古典——現代”這一轉換過程的深入理解,原本的困惑也逐漸清晰起來。
古典舞訓練是基礎:古典舞的跨界舞者們在正式跨入現代舞領域之前就曾長期接受著專業的古典舞訓練,其中以王亞彬、唐詩逸和華宵一為代表的優秀舞者更是將古典舞“十年磨一韻”的功力融匯在骨子里。王亞彬本人也說:“古典舞對于演員的訓練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它可以很大程度地解決彈跳力、柔軟度以及其他方面演員身體的運動能力問題。如果再借鑒現代舞的一些方法的話,這個演員的可能性就無限大了。”古典舞在塑造演員的身體時使其既有能力又不失細膩。人們常說古典舞的訓練過于束縛人、過于控制人的身體,然而舞蹈本身就在于舞者對身體的絕對控制,控制的越好,身體的可能性就越大。古典舞訓練就是要賦予舞者這種控制力的同時還要使其有暢若流水般的氣息和韻律。因此,無論是王亞彬、唐詩逸還是華宵一,觀眾都能看到這些舞者具有的對動作獨特的敏感度和成熟的表現力,這是這些古典舞跨界舞者的特點與優勢所在。
古典文化是源頭:滲透在古典舞訓練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常常起著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它使這些古典舞專業出身的舞者骨子里流淌著古典精神的血液,因此觀眾會發現這些跨界舞者的創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上是植根于傳統文化的,具有內發而外顯的風骨與氣韻。《唐詩逸舞》中唐詩逸用唐詩的意境作為表現的背景,但是她沒有限制于陳舊刻板如塑料花般的“古風”中,而是用新的肢體語言方式去探索傳統文學的文化價值。這種文化價值背后蘊藏的傳統藝術心靈,就使《唐詩逸舞》這個作品多了一份歷史的莊重和傳統的厚度,這在今天過于求新求奇的現代舞蹈創作中絕屬一股清流。王亞彬的《青衣》亦是如此。
總的說來,古典舞訓練下的語言能力與古典舞背后的文化意蘊,讓“古典——現代”的跨界舞者們對傳統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親屬感,這種親屬感終會化作一股無形的支撐力,伴隨她們在不斷跨越的道路上穩步前行。
追問與希冀
王亞彬、唐詩逸、華宵一,她們都是站立在古典舞與現代舞之間的一批人,她們騎立在區分不同舞種、代表不同文化的那堵墻上。只不過她們這種騎墻行為不是為了旗幟鮮明地隔絕“現代”與“古典”,反而是為了打破隔絕在現代舞與古典舞之間的那堵墻,并將二者融會貫通于自身的藝術風格中。正如前文提到的,創新立足于現代,發展扎根在古典,取各家之精華集于自身,這對于舞蹈家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應當值得被鼓勵。
不過在肯定與鼓勵這些舞者的跨界行為之余,我們也不能忽視古典舞在當下的發展境遇中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如果作為舞蹈發展重要載體的優秀舞者都想去跳現代舞、要踏入現代舞圈,那傳統的古典舞又該交給誰來發展呢?雖然對于演員的個體發展來說,除了有一門擅長舞種外,更應該掌握多種形式的舞蹈,這樣多元復合型人才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但是對于古典舞學科自身來說,其所屬舞者的多元發展未見得是絕對的好事。舞者跨界所帶來的優勢在于現代舞的創新理念和對于身體的解放訓練有助于拓寬古典舞發展中的極度規范性與單一性,促使該學科的吸收機制增強,發展廣度拓寬,是橫切面上的豐富。可僅僅有廣度的發展是不全面的。古典舞從歷史中走來,帶著深厚的傳統積淀走在今天的現代化道路上,它既有需要我們不斷縱深挖掘的文化深度,也有千百年間因發展所累積的歷史厚度,即便一個人專心致志窮其一生也無法透析這樣的深度和厚度,更不用說那些淺嘗輒止的人,只能是遇其皮毛而未觸及其筋骨。因此發展古典舞我們不僅需要樣樣通的人才去拓展其廣度,更需要一門精的匠人去發掘其深度。
說到這里筆者要提一個人,那就是漢唐古典舞學派的奠基人——孫穎先生。先生用畢生的精力打破了從京劇和昆曲中限定繼承的古典舞發展觀,從理論到實踐,一步步重現了中華民族文化母體中孕育出的漢唐舞風。他不盲目效仿中西結合的路徑,而是通過長期對漢畫像上歷史形象的認真觀察,對歷史知識的詳細梳理和對歷史資源的仔細辨識,在古典舞的當代發展中又樹立起了一個經典的漢唐標桿。而這一切成就,都是孫穎先生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和努力才換來的,他把自己的全部作為融入到中國古典舞的發展中,這樣專心不二的匠人精神是古典舞要向前走所根本需要的,也是人類文化要從過去走向未來所必須的傳承保障。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筆者先前的疑惑,古典舞留給舞者的發展空間真的小嗎?顯然不是。古典舞的文化深度和歷史厚度給當代舞蹈工作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供其發掘,只是它需要有“一門學問做到底”的人走進去,不斷探索不斷了解后才有把它帶出來給世人看的底氣和信心。“又紅又專”不是個貶義詞,一顆紅心向傳統,專心致志做學問。當然專心致志不是要讓古典舞者眼界狹隘地鉆到一條道上走到黑,而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汲時代精神博眾家所長來建設起一條古典舞發展的康莊大道。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要支持年輕的舞者多跨界多學習,就是為了使其能有一個開放的視野來更好地完成古典舞在今天社會中的創新任務。當然還是站在古典舞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更希望這些舞者在走出古典舞家門、開闊視域之后,還能帶著一身本領回家,把自身的發展和古典舞的發展結合起來,相互成就豈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