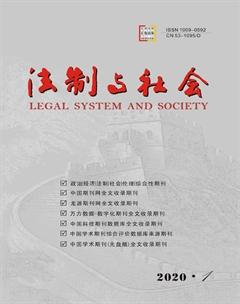高校育人實踐中的主體關系研究
高雷
關鍵詞育人實踐 師生主體 形式社會學 關系分析
本文通過對社會學理論進行歷時性地綜述并借現代性研究契機借鑒性地移植了形式社會學思想中的相關核心思想(如社交論、沖突論命題)并就其中所蘊含的關系思想進行了梳理,以期對高校育人實踐場域中師生主體關系問題處理進行關注:通過育人實踐中師生關系(交互參與)以及回歸育人本質(自助育人)強調,達成對育人實踐體系中的師生雙主體甚至多主體育人參與環境設定(如局部性育人協同沖突處理、共同體式育人體系環境建立)、建設性育人路徑探尋(育人成效常態化保持)以及融入自助性育人實踐中學生個性表達的關注。
一、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關系現象分析
教育部黨組在兩年前印發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中提出高校要充分發揮課程、科研、實踐、文化、網絡、心理、管理、服務、資助、組織等方面協同聯動育人功能,要切實構建起一體化的“十大”育人體系。在此背景下,各高校都應“全面統籌各方面的育人資源和育人力量”,從體制機制完善、項目帶動引領等方面進行系統設計,構建一體化協同育人機制,充分發掘“十大”育人體系每一類育人“子體系”的育人功能及實現機制。如何實現育人“子體系”的同向同行、互聯互通、協同協作?依筆者看來,如何審視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育人參與的關系至關重要。協同、合力育人勢在必行,但如果忽略了“高等教育體系體現出高度專業化的思維,即將人塑造成‘專業人,也即‘某種人,而忽視了培養學生‘成為人的使命”的問題存在,即打破了育人的主體交互性本質,錯過了學生作為育人實踐參與主體的可能,缺位了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關系的審視,便會出現“拔節孕穗”而“苗不長”的育人病象。
作為一名專業教師、輔導員,秉持高校是一個“育人共同體”理念,在“十大”育人體系的每一個“子體系”中主動找準育人發力點和整合起育人渠道的力量應是當務之急。筆者通過對所帶班級學生個案深度訪談與學風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發現因部分專業教師、輔導員“育人共同體”理念不明晰、學生參與育人實踐意識淡薄(自助的行為表現)、育人不到位甚至只教書強管理無育人、弱育人現象時有發生。如純粹從學生感知的角度(主要涉及專業課程認知度及認同感、學生授課感受及學習獲得感、學生專業滿意度及生涯意識)分析專業教師在對學生進行“課程教育”中是否含有“思想引領”“價值形成”“生涯規劃”,等育人元素的過程嵌入,我們會發現上述的現象己逐漸凸顯成育人實踐難題!可見,育人實踐中如何定位師生主體關系,嘗試構建起一套全方位、包括師生共同參與的系統性協同育人機制,并能夠在專業教師、輔導員雙主體甚至多主體育人自覺下助力學生形成完整的自我認知,形塑獨一無二的個性品質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二、齊美爾形式社會學梳理及“社交”“沖突”關系思想的引出
齊美爾強調的社交的民主性,即在社交過程中,每一個個體都應當獲得同其他參與者一樣的社會交往滿足的驅動力。具體地講,即每一個個體應當提供最大量的社交價值(如快樂、歡樂、愉悅等),同與他所接受的最大價值量的價值一致。齊美爾所強調的社交民主其實是有適用范圍的,即只能在同一社會階層內部的交往中才能實現而且它是一種近乎理想型的交往。齊美爾指出,就需要通過規則(如倫理、法律等)來約束雙方。這對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間關系定位以及育人民主、公平環境的設定不無啟示。但在現實中的育人實踐的師生關系處理實踐中,因為權利、政策、資源,等支持性資源體系的不對等往往會導致師生雙主體參與育人實踐的錯位(如只教書不育人現象的發生),甚至出現掣肘現象(如不會育人等)。如何通過齊美爾“社交的民主性”過程分析達成可以通過相關“規則、法律”等出臺保障育人實踐中師生之間育人的協同性、同向性、融入性與常態性值得我們好好探究。此外,齊美爾認為沖突是社會互動交往的一種形式。正如齊美爾所說,“沖突是社會生活的精髓,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筆者認為,如果社會沖突經常發生在社會的次級群體之間的話,那么就更有利于這些群體之間的互相協助和創新精神的發揮。基于此,如何充分挖掘沖突、矛盾性交往的齊美爾論述邏輯從而實現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問關系的維系功能值得我們思考。基于此進一步思考師生主體在育人實踐中如何擱置、規避“結構性利益沖突”(如唯知識、唯師道等),在育人實踐中師生能夠秉持育人共同體的理念,轉“師生獨立的社會行動(只負責“教書”,育人不是分內之事)”為“統一的行動單位”,建立起良性師生主體參與的育人關系共同體,實現學生的師生育人參與自覺顯得尤為重要。
三、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關系的形式社會學視角分析
學生個性品質的凸顯是通過先賦因素、態度行為以及性格體現出的心理思想特征與和環境交互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固定的行為模式。以此進一步思考如何能夠結合學生切合自身實際情況(個性特征、真實自我、實際技能)并進一步思考如何以齊美爾“社交”“沖突”關系論述中蘊含的如民主性育人環境設定、建設性師生關系維系以及以學生獨特的個性品質呈現為啟示切入點達成對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育人共同體關系的建立則為重點。筆者認為,在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參與育人體系的建構、共同體的都離不開對育人對象完整的“自我認識”(包括如價值觀、技能、興趣、才能、天賦,等架構起的個性品質以及就業志趣,等等)的喚醒。
(一)對實現民主公平、協同共建的師生主體育人參與關系的啟示
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問沖突是常見的。歸根究源則為“利益沖突”(教師自我的定位和學生自我認知的錯位)。隨著師生關系的深入,“利益點”也會隨之增加;“沖突度”也會愈演愈烈。齊美爾在形式社會學中提到的“社交民主性”思想是指在社交過程中每一個個體應當提供最大量的社交價值,同與他所接受的最大價值量的價值一致。倘若要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乃至社會階級之間實現這種等價值量的社會交往,齊美爾指出,交往就需要通過規則(如倫理、法律等)來約束。不難發現,齊美爾特別強調社交參與者在享受交往價值量的公平性,同時,即使出現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地位成員之間的交往,社交形式本身難以維持交往的民主性時,他強調就要通過相關法律、倫理等進行約制,最終實現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地位成員之間人們有序、平等的交往。
(二)育人實踐中師生關系的維系的啟示
社交作為社會交往的理想類型,也是形成和諧關系的潤滑劑。社交這種社會交往純粹的形式,不僅在人性的培養,還是在社會運行上,在各類各種主體合作上都起著實質性的作用。而且,齊美爾認為,純粹的社交本身就不該存在著現實利益關系,只能存在著純粹的、人性所提供的品質。當然,要想達到如此境界,齊美爾也會“自圓其說”,他為我們提供了途徑,即要學會“圓通”,即要學會在與自身相關的客觀因素和純粹的主觀要素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平衡點(即處于齊美爾所謂的社交界限內)并且要以純粹的人性品質去面對交往對象。因此筆者認為,師生雙主體良性育人關系的建立路徑如果借鑒性擇取齊美爾“圓通”手段(筆者冒昧將之成為“手段”,是因為齊美爾強調,似乎只有通過“圓通”,才能形成完美的交互形式,才能對參與者進行約束和限制,即實現在特定情景中,價值規范約束下,主體的行為由最初的滿足“自我”需要轉化為滿足“他人”的需要,實現創造隋景的目的)中的相關技巧,則在育人實踐中實現育人對象個體“自我”與教師主體之間的視角交融,減少“角色距離”給育人關系帶來的矛盾和困擾。一言以蔽之,師生育人共同體主體之間就可以實現日常交往中的協調與融洽、實現彼此間價值層面的認同,通過“圓通”達成育人共識與自覺。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之間的“局部性沖突”不僅是桎梏師育人目標的藩籬,更應成為我們思考如何通過齊美爾的“回避”“擱置”技巧實現最終以“成人成才”為終極育人目標為基礎與導向,以“圓通”實現育人的“圓滿”!同時如何讓學生在育人實踐中師生主體育人參與過程中“社交”因素中現實理性少些,多些自我回歸(包括如學生主體價值觀、技能、興趣、才能、天賦,等架構起的個性品質的回歸等)?如何讓他們在“客觀文化”(如校園文化、班級乃至宿舍文化,行動文化、氛圍文化乃至制度文化等)面前,減輕其“壓制性”錯覺,增強學生個體成人成才的主體能動性,充分呈現出育人實踐中過程中的師生育人雙主體參與效力?如何讓學生個體在對“外部力量”(如師生利益沖突、價值錯位、關系失范,等)的博弈中充分發掘自我,呈現獨一無二的自我個性表達?這一系列發問也在提醒我們育人實踐中如何定位師生主體關系,嘗試構建起一套全方位、包括師生共同參與的系統性協同育人機制,并能夠在專業教師、輔導員、學生雙主體甚至多主體育人自覺下助力學生形成完整的自我認知,形塑獨一無二的個性品質在實踐中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