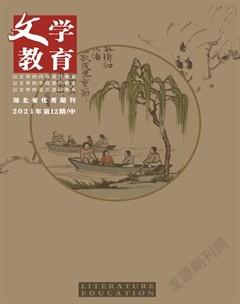寫作中的突轉藝術
胡敏
內容摘要:突轉是敘事性的作品情節設置的常用手法,這種小說情節或人物命運發生突然的轉變往往能給讀者造成強烈的審美刺激,同時突顯主題。
關鍵詞:突轉 寫作 技巧
在一些優秀的短篇小說中,我們往常看到—種令人們拍案叫絕地的富于戲劇性的突然變化,比如說,—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聲勢浩大的搶劫化肥案眼看即將發生,瞬息之間卻改變了性質,搶劫者紛紛排隊掏錢,由“劫”變成了“購”(楚良《搶劫即將發生》);一個平時牢騷滿腹、玩世不恭的農村遠輸專業戶,在大壩出現險情時,竟會開著自己的拖拉機沖進堤壩泡眼,舍身護堤(陳世旭《車燈》),一個離家才幾天,就給丈夫打半小時長途電話傾訴思念之情的女演員,剛放下話筒,卻立即投入另一剛剛相識的男人的懷抱(叢維熙《霉雨》)……
這都是“突轉”技巧的運用。
所謂“突轉”,是指小說情節或人物命運發生突然的轉變,而且這種變化是讀者和作品中人物始料不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突轉”并不等同于—般意義上的轉變。可以說,所有的小說情節或人物命運、人物性格,都處在不停的轉變之中。就情節而言,或由高潮轉入低潮,或由低潮轉入高潮;或由緊張變為松緩,或由松緩變得緊張。就人物而言,或由順境轉入逆境,或由逆境轉入順境;……停滯的一成不變人物和情節,在小說中幾乎是不存在,然而這種轉變是緩慢的、漸進的,作品中的人物和讀者很早就能感覺到這種轉變。而“突轉”卻與之相反。
一.“突轉”是大跨度的轉折
“突轉”的概念最早出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雖然他是針對戲劇而談的,但在小說中同樣適用,尤其是那些篇幅短小、戲劇性很強的性格小說。
在創作中,“突轉”運用最早、最多、最好的是戲劇,《俄狄浦斯王》《威尼斯商人》《雷雨》等許多古今中外名劇,都是運用“突轉”的典范作品。十八世紀末以后,隨著小說結構由故事型向性格型轉化,這一技巧逐步被批判地吸收到小說中來,在《項練》《胖子與瘦子》《我的第—個上級》等名作中,“突轉”都顯示出了它迷人的藝術魅力。
當代小說中,“突轉”越來越受到作家的青睞,短篇小說獲獎作品中不乏其例。
“突轉”技巧在作品中的成功運用,能強烈地震撼讀者。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突轉”可以使表面單純的情節,實際上變得復雜起來,使靜止的、平面的情節變得大起大落、搖曳多姿,象流水突然跌下懸崖,激起奇妙壯觀的飛瀑。
“突轉”可以使人物性格由扁形一躍而成圓形,由單維的低層次進入雙維的高層次,成為多樣統一的結合體,變得豐滿,變得光彩。
“簡短”、“單純”與“復雜”、“豐富”是一對矛盾,“突轉”技巧,則是解決這—矛盾的一把鑰匙。
我們先來看陳世旭的小說《車燈》。這篇六千多字的短篇,情節十分單純:新提拔的縣長夏邦清下鄉指揮抗洪,碰上了中學同學、運輸專業戶胡月生。胡因自己的意中人嫁了夏而對夏不滿,又因自己讀了十二年書而仍在農村覺得屈材,便牢騷滿腹,怪話滿嘴。他明明知道夏縣長正在第一線指揮抗洪,卻對前來視察的地區專員說“不知道”、“大概沒來過”,害得地區防汛指揮部點名通報了夏邦清。誰也想不列,就是這位“老油條”式的人物,在堤壩出現險情時,竟毫不猶豫地開著自己的拖拉機沖進洪水,舍身護堤。
小說至此嘎然收尾,讀者的思維卻無法煞住。對于胡月生的壯舉,他們會想得很多很多!為什么這位護堤英雄在平時反給人一種落后的印象?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客觀社會的原因,還是主觀性格的因素?這不僅激發讀者對小說所創造的藝術世界更深入地體會、把握,還往往會跳出作品的框框,到廣闊的現實世界中去找答案。這就無形中加深拓寬了作品的容量,豐富了人物的性格,使讀者對人物從外部和內部全面把握,并不斷有新的認識。不難設想,假如《車燈》中砍掉“突轉”的文字,情節將會變得怎樣單薄,人物也將會怎樣的黯然失色啊!盧卡契在評論《十日談》時說:“薄伽丘短篇小說的結構——是主觀的故事的結構,雖然象剪影一樣地明了,但也象剪影一樣地是靜的性格的葛藤。”這間接地證明,在創作中運用包括“突轉”在內的一些結構技巧,對于創造復雜的人物性格是多么重要。
其二,在于讀者萬分驚訝后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新的發現,從而獲得審美快感。
“突轉”之所以會使讀者驚訝,是因為“突轉”所產生的結局往往出乎讀者的意料之外。那種“觀前事便知其有后事”,“觀前文使知其有后文”的情節,自然不會使人驚訝。
另外,從小說的基本構成單位——“場面”來看,“偉大場面十分之八九及由突轉造成的。”在這些場面中,除了情節陡折急轉,朝著出乎意料的方向發展外,人物也往往亮出他們性格中最隱秘、最主要的那部分,使讀者從中有許多新的“發現”,新的認識,從而留下最鮮明、最突出、最生動、最深刻的印象。比如《車燈》中胡月生英勇獻身后,人們不能不對他的平時的表現重新加以認識,也不能不對自己的看法來個反省,從中一定會有所“發現”。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突轉”技巧時,往往和“發現”并舉,這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不妨再舉一例。叢維熙有一篇四千余字的小說《霉雨》,大意是:老導演要拍一部歌頌人間堅貞愛情的倫理道德戲,戲中要求主人公的心胸如同浪花一樣晶瑩和透明。女演員阿眉恬靜文雅的氣質和脫俗的儀表一下被老導演看中了。阿眉離家才幾天,便給丈夫掛了近半小時的長途電話,暢述別后思念之情,這位老導演“異常欣慰”,覺得自己“眼力深邃”,沒有選錯人。誰知情節來個“突轉”,老導演在屋里聽見阿眉掛了長途電話,出來尋她時,卻突然“發現”她已和另一個男人摟在一起,用“一團黃黃的”風雨衣擋著,正恣意發泄情欲!這一“發觀”,頓時使老導演“一陣胸悶”,差點兒“心肌梗死”!同樣也使讀者大吃一驚,陷入深深的思考。
二.哲學依據和生活基礎
“突轉”技巧的成功運用并不完全取決于作家的主觀臆造,而有其哲學依據和生活基礎。
“突轉”的哲學依據是什么呢?就是必然與偶然、現象與本質的辯證關系。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的現象都是復雜多樣的,既有與本質相一致的表現形態——真象,也有與本質不相一致的甚至顛倒的表現形態——假象。列寧“假象的東西是本質的一個規定,本質的一個方面,本質的一個環節。本質具有某種假象。假象是本質自身在自中的表現。”一個本質高尚的人,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以“落后”的假象表現出來;而一個品質惡劣的人,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以“高潔”的假象表現出來。“突轉”技巧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也正由于作者較好地認識處理了這二者的辯證關系。對《霉雨》來說,阿眉對丈夫的難分難舍,軟語纏綿,很難說不是為迷惑對方而有意做出的假象。
從讀者角度來看,“突轉”令人吃驚,在其本質上,是因為它帶有偶然性。胡月生假如一直以“英雄”、“模范”、“優秀黨員”的面目出現,那么他的獻身是順理成章的事,決不至于使人吃驚;阿眉假如平時作風不檢點,或夫妻不和,那么她離家才幾天就與人勾搭也是在意料之中,不會使人驚訝。偏偏他們在常態下都以相反的面目出現,這就使“突轉”帶有偶然的性質。也許有的讀者覺得這種“偶然性”不合常理而難以接受,其實這是欣賞水平不高所致。從哲學上說,只承認必然性而否認偶然性,這是機械決定論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對立統一的,因而是相互聯系的,在一定的外在條件之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建立在大量的偶然性基礎之上,馬克思說“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么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有些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在發展的階段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出現的。
那么,從偶然性極強的“突轉”中,能否找到必然的原因呢?應該是肯定的。以《車燈》為例,如果試圖從作品中去找“暗示”,那也許會令人失望,即使找出一兩句話,也難免失之牽強。但如果跳出作品的框架,將生活和作品結合起來,就會發現“突轉”確實含有合情合理的因素。胡月生雖然平時牢騷滿腹、玩世不恭,但畢竟生長在新社會,黨的教育,正面力量的影響畢竟占主導方面,并且,他平時的所謂“牢騷怪話”,與他愛情上的失意,與對夏邦清的誤解,與對社會上某些不正之風的看不慣,有很大關系,并非出于人品本質上的原因。況且,在出現險情的關鍵時刻,他聽到“共產黨員留下來”的響亮號召,看到身為縣長的夏邦清帶頭沖上去,他的性格中的正面因素便立即得到升華,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行動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至于“突轉”技巧與生活的關系,更是顯而易見,我們平常所常見的一些生活現象,如“好心辦了壞事”,“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禍得福”,“聰明一世糊涂一時”等,都可說明“突轉”源于生活。
三.巧設伏兵,欲擒故縱
運用“突轉”技巧,首先,必須創造一個特殊的條件。即在讀者眼皮底下“設伏”,而讀者又不以為這是“伏”,這樣,才能使突然暴發的結尾有必然性和震動性。阿眉如果不是遠離家庭,如果不是碰上另一個風流哥兒,她的輕浮本性也難以表現出來;胡月生如果不碰上堤壩險情,可能還會繼續扮演“老油條”的角色。其次,要千方百計地使讀者對“伏兵”暫時地忘卻,這樣,設伏之后,往往就要用更新奇更富有吸引力的情節把讀音的注意力吸引過去。第三,“突轉”要符合藝術真實,不能憑空捏造,脫離現實。用奇人怪事、神魔鬼怪拼湊的“突轉”,讀者在思想、感情上都難于接受。當然,非現實主義的神怪小說等,又另當別論了。
(作者單位: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