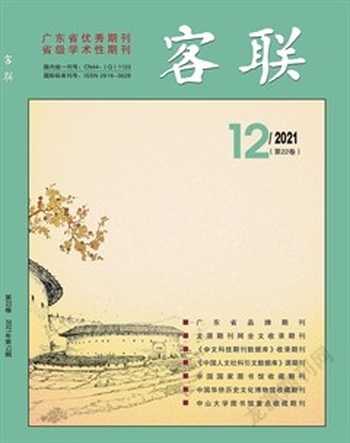社會工作介入流動兒童人際交往障礙策略研究
楊莎莎

摘 要: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民工群體由“單身外出”方式日益轉向為外出“家庭化”模式,流動兒童群體及其問題由此衍生,引起社會關注。人際交往障礙由于影響了其身心健康,也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本文以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為理論基礎,通過跟蹤和分析1個成功個案和2個咨詢性個案的文獻資料,發現其人際交往障礙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其性格、親子溝通模式和校園的融入相關。因此社工介入也應立足于多維層面,從服務對象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層面干預。
關鍵詞:流動兒童;人際交往障礙;心理社會治療模式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末起,農民工群體由“單身外出”方式日益轉向為外出“家庭化”模式,由此衍生流動兒童。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0-14 歲的流動兒童已超過 3600 萬,且數字逐年上升。
流動兒童本身具有獨特性,一般指6-14歲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青少年兒童[1]。由于父母在城市中邊緣化,受其家庭影響,在參與社會生活時,他們因缺少參與機會也處于邊緣化或被隔離的社會系統中。同時由于父母忙于生計,無法關注他們的心理,給予其心理支持,長此以往,他們在參與社會生活中就可能消極應對,由不敢與人交往到不愿與人交往,由此出現人際交往障礙。人際交往障礙指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由于受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等影響,在與人交往中出現困難或不順,主要表現在認知障礙、行為障礙、情感障礙[2]。
心理社會治療模式最早可追溯瑪麗·里士滿《社會診斷》一書,它以“人在情景中”、“心理分析”為理論基礎,認為一個人的行為與其生理、心理、社會有關,正是由于這三者綜合的影響才導致個體產生特定行為。因此它認為,流動兒童的人際交往障礙是其生理、性格等心理因素以及家庭、學校等環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社會工作者在介入時,要多維角度評估與解決流動兒童人際交往障礙問題。全方位評估,多層次解決,這是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的核心所在。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選自筆者所在實習機構漳州市龍文區向陽花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童心筑夢”項目,主要包括項目社工、服務對象—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和相關的文獻資料等資料(如表一)。
(二)研究方法及思路
筆者為了篩選出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對老師轉介來的存在人際關系問題的人(共28人)進行了社交測試。此測試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兒童社交情況測試,旨在了解他們的人際關系,共6題,得分越低者代表人際越好,具體而言分為4個級別,6分以下人際關系很好,6-12分一般,12-18分較差,18分以上很差;另一部分是兒童社交焦慮測試量表,旨在評估他們的人際交往障礙及其程度,共10題,主要測試內容為害怕否定和社交回避及苦惱,得分越高則代表人際交往障礙越明顯。
筆者分析發現89.3%的測試者(25人)表示自己愿意與他人交往,但是82.1%的人(23人)很自卑,擔心別人不喜歡自己,覺得別人不會喜歡自己,因此甚少主動與他人交往。而在這23人中,社交焦慮測試量表結果否定分值與回避分值相加等于或大于10分的有10人。綜合分析這些,筆者認為這10人存在人際交往障礙,因此確定為本文的服務對象。其中得分為前3的即是本文的個案案主,最高的為深度個案案主,另外兩個則為咨詢性個案案主。
同時,筆者對篩選出來的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進行入戶訪談,全面了解他們基本的生活環境、家庭交往、性格、情緒、家校互動以及同輩支持和家庭支持。
然后,結合入戶訪談搜集來的資料進行文獻分析,采用個案工作與小組工作結合的方法進行治療。
三、介入策略分析
在心理社會治療模式指導下,筆者從服務對象個人層面、家庭層面、學校層面三個層次干預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介入策略如下:
(一)著眼多維層面,全方位評估
社工在介入時,既要關注服務對象的當前環境、生理和心理狀態,也要關注服務對象過去的經驗。在評估過程中,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訪談對象擴展化
首次訪談要在服務對象熟悉的場景進行,最好有其重要他人在場,以增加服務對象的安全感。此外,在訪談時還要關心其重要他人的言行舉止。從重要他人的角度可發現服務對象表達出來的狀態給他人帶來的感受及想法。
2.專業關系朋友化
以朋友的身份與案主建立平等的專業關系,更加能貼近案主,了解案主的想法,獲得案主的配合與認可,從而治療也會更加的順暢。同時,從朋友的角度真誠與案主交流,從案主興趣出發尋找切入點,才能逐步了解到案主的生理、心理狀態,從而對案主有全面的了解。
3.訪談內容多維化
社工在進行入戶訪談評估時,除了要觀察服務對象生活的環境,從細小之處發現其生活習慣,還要注重服務對象的其他方面,如自我評價、人際狀況和學習成績。總體來說,訪談內容要涵蓋服務對象的認知、情感以及社交行為等多方面。
(二)紓解心理問題,改變認知偏差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不少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會被重要他人的言語傷害,從而產生自卑情緒,認為自己是一個無用之人,沒有優點與特長,因而不被人喜歡與沒有朋友。
因此筆者認為在紓解其情緒的基礎上改變其自身及重要他人的認知偏差,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認知。其中首先要幫助其建立學習成績不好與天生智力沒有關系,而是各種原因才導致其成績不好的認知。另外,還要改變案主“被欺負是自己不好”的認知偏差。
(三)挖掘校園資源,增加校園支持
在學校層面介入時,社工可尋求老師的幫助與配合,使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有一個開朗活潑的同桌,并且也能夠在學習上給予其幫助。同時社工也要與其同桌溝通交流,尋求其理解與幫助。筆者發現,在介入的過程中,以案主為中心,通過社工、老師、同學為三角的互動,可幫助案主從人際交往障礙困境中解脫出來。在此過程中,案主是溝通的中心,一切行動的中心;社工則是案主與老師、同學溝通的連接點,是案主中間人、信息傳譯者;老師則是案主動態變化的監控者以及鼓勵者,而同學則是案主改變的支持者和融入班級、校園的引路人。
(四)創建社交環境,增加社交技巧
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因為與人交往不順,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長期下去,他們逐漸脫離了同輩群體圈子,不了解同輩群體的想法和興趣愛好。鑒于此社工設計了“迎面困難 助力成長”人際交往障礙流動兒童成長小組,將之前篩選出來的10名服務對象聚集起來。通過“交際尋寶”主題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社交情況,提高他們是社交意識,然后通過“理解與自信”、“信任與溝通”、“同舟共濟”主題來增強他們的社交自信,提高他們的社交技能,增加他們的合作能力。
參考文獻:
[1]劉霞,趙景欣,申繼亮.歧視知覺對城市流動兒童幸福感的影響:中介機制及歸屬需要的調節作用[J].心理學報2013,45(5),568-584.
[2]繆蕓.社會工作介入流動兒童人際交往障礙研究[D].南京農業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