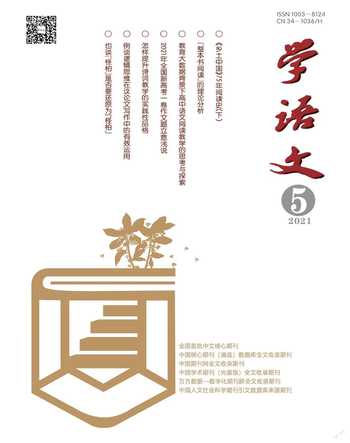寫作精進人生
摘要:通過對“寫作精進人生”的論述,闡述文道與人道的統一關系、以人為本對寫作的要求,以及寫作對人生精進、精神成長的啟示。
關鍵詞:寫作;人生;文道;文化
很喜歡“寫作精進人生”這句話。其它的學問各有其專業對象,譬如物理學是研究物理的,化學是研究化學的,美學是研究美的,其對象都有專門特定的指向,唯有寫作學研究不僅是以寫作活動為研究對象,更以寫作的主體——人為對象進行研究。有人說文學就是人學,又豈止是文學?哲學、美學、心理學,凡哲學社會科學,哪個不是人學?所有的文章學問歸根結底都是人學。
有人說,作家都是人精。作家應該是生活家。寫作的理論就是生活的理論。作為一名寫作者,除了琢磨寫作技巧外,更需要的是體察世態人情、洞悉世道人心,用心琢磨生活、琢磨生活中的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不研究生活、不琢磨人,沒有一定人事經歷、人情練達、人心洞察以及對生活的深刻體察,不可能寫出真正有高度、深度和厚度的文章。即便就文章本身而言,文章的形式、語言、技巧、手法等,實際都與現實生活和現實生活中的人事息息相通。明白了這些,就會明白“寫作精進人生”的真義。
“寫作精進人生”要求寫作要以人為本。人和文本來就是一體的,甲骨文的“文”就是一個站立的人形,上端是頭,頭下是左右伸展的兩臂,最下則是兩條腿。所謂的人文,也是有人才有文;所謂的文化,其實都是“人化”與“化人”。所有文章都是人寫的,即所謂的“人化”;所有的文章都是給人看的,即所謂的“化人”。以文學中的小說為例,一般以為,讀者似乎更關心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其實讀者更關心的是故事中人物的悲歡離合。人物有了魅力,情節才有了靈魂。人們看文章,實際也是在看人。作家寫文章,實際也是在寫人:既寫別人,也寫自己;有時看似寫別人,實際也是寫自己。以人為本不僅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所有寫作的核心。人類生活的世界本就是由自然、人、社會三個部分構成的,而所有文章所反映的也無不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不論什么樣的題材、怎樣的表達,都離不開一個人字。離開人這一寫作主體,文章就不復存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可以說,以人為本也是所有寫作的最高價值取向。
說“寫作精進人生”,是因為寫作對于人生有太多啟迪與教益。一個人的寫作史,實際也是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理性成長史。作為一種精神活動和審美創造,寫作有助于陶冶人的情操心性,拓寬人的胸襟視野,涵養人的氣象氣度,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寫作不僅是修辭,而是一種修為與修煉。簡潔、干凈不僅是文字上的表現,也是為人上的純凈與清省;明白、通暢不僅是邏輯上的呈現,也是為人上的明晰與暢達;寫作上的有所寫有所不寫與為人處事上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其實都是一回事兒。蘇軾論文說“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其實就是取舍恰到好處,這與說話做事的講究分寸,注意火候,掌握尺度,掂量輕重一樣,正如洪應明《菜根譚》中所言:“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說文章要有思想、有學養、有趣味,其實也是說做人要有內涵、有境界和有情趣。對寫作的渴望、寫作的熱情、寫作的追求,甚至布局謀篇、遣詞造句里都有著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都包含著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胸襟、氣象、格局等。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很多大家把寫作視為精神依托、生命核心的原因之一。人常說,人生的意義是創造,寫作的意義又何嘗不是?人常說沒有審美層面的人生不是完美的人生,那么沒有經歷過思考、審美和寫作的人生呢?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過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應有的美點。”“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其中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不能稍有移動或增減。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見出全篇精神的貫注。”“把這種生命流露于語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風采,就是美滿的生命史。”(《藝文雜談》)
說“寫作精進人生”,是因為寫作于做人做事本來就是一致的,立德立功與立言,做人做事做文章,其中的藝術與機關往往是相通的。即便講寫作技巧,古往今來很多人也常拿人事做比喻,說“文人作文,如婦人育子,必先受精,懷胎十月,至肚中劇痛,忍無可忍,然后出之……”(林語堂);說文章就像人體,“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顏之推),而文章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而清人王鐸的說法則是“文有神、有魂、有魄、有竅、有脈、有筋、有腠理、有骨、有髓。”(《文丹》)。李漁說寫文章就像蓋房子,“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閑情偶記》)。有人說寫作就像做菜,先得有料,還要有好食材,還得掌握火候,如此“烹飪”才能有色香味。有人說寫作就像打仗,其遣詞造句、謀篇布局,就像調兵遣將、排兵布陣,戰場的殺伐決斷、排兵布陣、運籌帷幄,球場的騰挪閃躲、補位接應、凌波微步,歌場的淺吟低唱、引吭高歌、婉轉起伏,無不與文章的酣暢淋漓、雄奇瑰麗、謀篇布局一樣妙不可言,如此等等。可以說,萬事萬物都是為文之道,為人處事之法皆為寫作之法。習近平說“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實際也隱含著這樣的道理。
萬法歸宗,理一分殊。文道人道,互鑒互補。文場筆苑風云江湖,學問文章人情世故。有字文章無字理,無字書成有字書。文章看似小天地,實乃天地大文章。寫作不是鼓搗字兒,拼湊句兒,而是琢磨事兒,研究人兒;文章不是炫技弄巧,玩耍詞藻,而是洞悉人性之后的創新創造。在每個作者的每篇文章里,實際都藏著他曾經讀過的書、走過的路、遇見的人、經過的事。寫作雖非人生目的,但其意義卻在于探尋人性,創造價值,也切實有益人生的豐富,故寫作的精進,必然也是人生的精進。
(作者:張英俊,河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一級調研員、中國寫作學會會員)
[責編張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