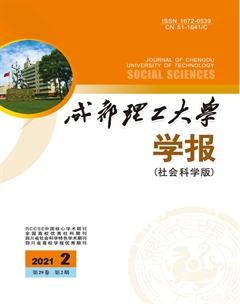生存本體論的困境
陳月瑤
摘 要:從詩的本體論到本體論的詩,《詩化哲學》中生存本體論的建立提供了反思現代性的維度,其中關于詩與哲學實現內在關聯的設想頗具啟發意義。而審美的現代性主題在《拯救與逍遙》中具體展開,以基督教神學中“拯救”性的純粹精神價值來拒斥現代虛無主義,與后現代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思想形成對照補充視野。通過反思劉小楓早期美學思想中存在的生存本體論困境,觀照主體間性美學在面對現代性危機時所起到的審美救贖作用。
關鍵詞:劉小楓;本體詩學;生存本體論;現代性;主體間性
中圖分類號: I0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21)02-0069-06
一、澄明前見:作為方法論基礎的生存本體論
在《詩化哲學》的緒論中,劉小楓明確提出:“本書的目的有限,這就是:認識德意志的浪漫主義思想傳統。”[1]4要把握德意志浪漫哲學的思想主張和發展統緒,重點在于理解浪漫主義哲學是如何擺脫邏輯理性,并以超驗意向來解決人的現實生存困境的,這一理論武器就是生存本體論,通過哲學中心問題的根本轉變建構起人與外部世界的新型關系,意圖在于顛覆被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所固化的話語體系。
劉小楓看到,隨著歐洲資本主義進程發展,現代文明的出現,工具理性的蔓延,唯物主義和經驗主義應運而生,二者雖為勁敵,但都為人的生存意義命題設定了一個智性基礎,由此一來,認識論便取代本體論占據了優先地位。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思潮以“對現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的決絕姿態,基于人性與文明普遍分裂的歷史現狀,執拗地在純粹知性所統治的漫漫長夜下摸索人的內在靈性,尋求靈魂的避難所。
詩的本體論是如何一步步確立下來的?劉小楓認為,比起盧梭,浪漫思潮的先導應追溯到17世紀的帕斯卡爾。帕斯卡爾在唯理主義盛行的時代中就提出了“心的邏輯”來抵抗笛卡爾所推崇的理性邏輯,但不論是盧梭還是帕斯卡爾,都沒有提出完整的理論系統主張,德意志浪漫派的生父還是要歸于以審美(鑒賞判斷力)調和二元對立論的康德。
《判斷力批判》的出現,從整體上將“美是什么”的基本問題轉化為“審美是什么”,通過闡明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使感性主體的情感官能終于尋得一隅合法的棲息之地。康德除了將審美領域提升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外,更是以先驗構架學說啟發了費希特“純粹自我學說”的建立,而后者則直接影響了后來浪漫派解決同一性問題的基本思路。還有一位理論先驅是席勒,《美育書簡》以游戲沖動將審美的功能與人性的自由解放相勾連,認為“詩的價值越大,它們的矛盾就越少”[2],于是,詩成為了構建理想人性的重要中介手段,這一點啟發了浪漫派以詩來解決普遍分裂的方法論探索。
德意志浪漫派詩哲們是如何繼承并進一步完善前輩遺留下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的呢?首先需要看到,存在論設定了一個外在的絕對精神實體的存在,像柏拉圖和黑格爾所做的那樣,劉小楓認為,這種絕對精神將會“取消感性的生息”;同時,這種傳統認知論意味著本質主義立場、二元對立思維和科學至尊態度[3]。浪漫派詩哲們意識到,要拒絕先驗式的二重世界設定,必須將目光從經驗世界轉向詩意世界,從智性思維、工具性邏輯到詩意思維、超邏輯,關鍵點在于尋求一個中介,或稱為過渡環節。施勒格爾對此提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意見,即“中介就是向永恒生活的生成運動”[1]53。
其次,德意志浪漫派對費希特自我學說進行了反思與修正,費希特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確立為世界的本體論實體,通過設定一個“非我”企圖使經驗有限自我返歸超驗無限自我,于是浪漫派的基本哲學論題也就從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轉向有限與無限的同一性問題,時間在此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同時,以施勒格爾為代表的浪漫派詩哲也看到了費希特先驗哲學中以“無限來設定有限”所造成的現實困難,于是將思路倒轉過來,從個別趨近絕對。為解決有限與無限的同一性問題,劉小楓看到,此時德意志浪漫派將重心轉移到了審美(感覺)上,通過超驗性的意向擺脫時間對感性個體的束縛,從而在詩的國度確證人的絕對自由,至此,詩的本體論才真正確立下來。
從施勒格爾、諾瓦利斯到謝林,無論是語言媒介還是神話重建,在理解早期德意志浪漫派的哲學主張時,必須時刻注意詩的本體論與傳統認識論之間的根本性差異。如若不澄明這一前見,將會造成不必要的理解偏頗。當浪漫派詩哲利用費希特哲學思路以自我精神作為超驗原則來設定詩意化的外部世界時,從認識論角度來看無疑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論斷,只有建立在本體論基礎上的闡釋才具備合理性,浪漫派哲學強調的是一種詩化的感覺,而非由自然科學或是經驗主義所提供的思維根據,同時,感性個體的有限自我最終要落到超自我的原我身上,通過這種神性的意識與客觀外部世界再次聯結起來,用劉小楓的話來說,就是“超驗的大我通過一個稟有感性的小我,把有限之物、時間中的物(包括個體的人和世界中的事物)統一領入無限中去。”[1]68維塞爾教授稱之為本體詩學。
落實到具體的概念闡析,例如諾瓦利斯提出所謂的“魔化”學說,其中“愛”作為中介條件使自然經驗世界成為活的生命存在,也就成為了浪漫本體論的終極根據。但如何理解作為情感范疇的“愛”能夠左右物質性的實體甚至改變歷史進程?秉持本體論的研究思路展開生發就不難理解,浪漫派這一關于愛的學說不是在談歷史哲學,更與自然科學無關,它僅僅關涉人生哲學,是超邏輯的審美之維,同時關涉信仰問題,也屬于價值論的倫理學領域。
然而,詩的本體論是否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人生中的所有矛盾與分裂?事實上,依舊存在兩個問題亟待解決。
一方面,正如孫正聿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本體論與人類歷史發展之間存在一種相割裂的矛盾狀態:“‘本體論指向對人及其思維與世界內在統一的‘基本原理的終極占有和終極解釋,……而人類的歷史發展卻總是不斷地向這種終極解釋提出挑戰,動搖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撐點的權威性和有效性。”[4]既然傳統本體論存在這樣一種悖論,即絕對真理總是受到歷史更迭所出現的個別事物的質疑與重釋,那么,如何保持自身的辯證法精神和持續生成的指向就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論題。
另一方面,有限與無限之間同一性問題的解決以時間概念為關鍵點。然而,只有對于感性個體的有限生命而言,時間、永恒、不朽等概念才具備應有之義,只有這些有生有滅、終有一死的生命體才需要苦苦追尋生存的密度并思考人生的終極意義,而自然實體則無須回答這一問題。劉小楓認為,無論是施勒格爾把渴念、愛作為終極依據來構建詩意的價值世界,還是謝林以“絕對”論的本相流溢來達到哲學和藝術中的永恒彼岸,都是一種將價值論轉換為存在論的做法,通俗地說,就是有限與無限的同一性問題繞了整整一大圈,卻最終又回到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的窠臼之中。要建立詩意的人的世界的初衷卻變成建立起一個詩化了的實在世界的徒勞無功,情感范疇自身的合理性就此消解。
所以,在劉小楓看來,對真正的本體應該作何解釋是問題的關鍵,倘若將本體視作世界的本源,這是一種自然存在論的本體觀。然而要拯救浪漫本體論所面臨的厄運,必須把本體論的內涵轉換一下,將其解釋為一種“人的超越性生成”[1]160,從詩的本體論到本體論的詩,于是,傳統的實體本體論也就最終走向了生命、生存本體論。
二、生存本體論的演繹:從尼采到馬爾庫塞
生存本體論的轉換意味著個體的生命意志取代了涵蓋一切的實體或精神成為真正的本體,這一浪漫主義哲學的極端推演是由叔本華和尼采所確立的。叔本華提出,世界是人的表象,人生的根源是欲求與沖動(意志),認為應以超邏輯、審美直觀的認識方式直觀本體,強調非意志審美人格的建立,并將其視作提高精神境界與自我超越的過程,從而真正與對象世界融為一體。叔本華所謂的唯意志的主張最終卻落腳于非意志主義,即寂滅論。這雖然是一種厭世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但也是對超越時間有限性的一種解答方式。
如何把握自身的意志力?尼采從叔本華手中接過意志本體論后,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即強調意志力的擴張。在尼采那里,意志生命本體自身就是詩一般地沉醉、升騰、勃發,劉小楓認為,如果說叔本華手中的意志尚只是盲目的、不可遏止的沖動,在尼采那里,已膨脹為一種原始性的生命力的實體[1]207。“存在”與“世界”在尼采哲學中充當生命力(權力意志)的代名詞,以整個生命來把握對象,以審美直覺與生命本源交融合一,這正是本體論的詩所尋求的出路。
劉小楓認為,尼采在對本體的呈現上徹底摒棄了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然而,酒神精神的狂肆在人類歷史上往往造成毀滅性的極端后果,于是,狄爾泰的現代生命哲學賦予了生存哲學新的內涵,進一步突出了感性生命及其歷史境遇的問題。
狄爾泰對生命本體論的重要貢獻首先在于:引入歷史的概念,生命歷史相對主義出現,使得真理、價值和意義等命題都不存在絕對的形而上學依據;其次是認識論為適應本體論所做出的根本轉變:形式邏輯被感性個體的生命軌跡打碎,出現了解釋性的認識方式——領會、說明(解釋)和體驗。其中最重要的是體驗,即有限生命返歸本心后對生活的反思。劉小楓認為,這種以體驗為中介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統一與黑格爾式的以思維為中介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統一有很大的不同,它確保了感性個體的真實地位,“不致使它在一種形而上學化的思維框架中被取消掉”[1]273。
在劉小楓看來,浪漫主義哲學發展到海德格爾的階段,比前后的任何哲人都要更加深入,原因在于他將“技術科學的勃興與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迷誤聯系起來了”[1]286。在海德格爾那里,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對象性的世界觀,使得人生中的詩與藝術文化在這種計算式的認識之中逐漸窒息,諸神也轉過身離去,人生在世的寄居之所沉入冥暗,只有通過詩才能把握到存在之路。要實現存在的澄明,必須先對形而上學的傳統思路進行批判,這種思考方式把存在當作存在者,技術的統治蔓延開來,使人們陷入對存在的遺忘。為了不把存在變為存在者,不把存在作為對象來觀照,海德格爾不直陳存在的內涵,而是用暗示性的語言來意指,如“恬然澄明地自己出場”“無蔽中的在場”等。由此,海德格爾引發了一場本體論上的革命性轉變:存在不再處于一種認識關系之中,直接抽空了形而上學認識論的基礎。
劉小楓認為,海德格爾進一步鞏固了本體論的轉變:本體不再是一個外在于人的實在,外在于人的超絕對的無限,而是感性個體本身[1]349。存在如何顯現的問題,其實也就是感性個體如何生存的問題。人“站出來生存”,就是存在的澄明,這就使得傳統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徹底轉換為生存的本體論。
新馬克思主義美學(馬爾庫塞、阿多諾、本雅明、布洛赫)作為德意志浪漫哲學傳統的當代表達,將本體論的內涵擴大到社會學的領域,更加凸顯出現代性批判的主題。馬爾庫塞對本體論的定義不僅限于人的普遍的、社會的感性存在,更是強調了作為感性活動的對象化的現實社會。這一本體論是歷史的、實踐的,馬爾庫塞的思路是通過對單向度社會的論述進行社會歷史批判,確立感性與現實社會本體論的優先地位,從而依靠詩的審美力量實現人的自我解放。
于是,本體論的詩也隨之表現為感性和社會的審美變革,通過感性個體的內在的審美解放,將原欲轉化為愛欲,藝術的自律性能夠作用于現實領域,這一命題的提出使得審美之維就凌駕于倫理之境上,在新馬克思主義哲學那里,美學就成為了人類哲學的終點。
從詩的本體論到本體論的詩,劉小楓拉出了一條從德國古典哲學時期到現當代德國哲學發展中浪漫主義哲學的思想線索,為反叛形而上學傳統認識論所建立起的生存本體論提供了反思現代性的維度,其中關于詩與哲學實現內在關聯的設想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然而,在《詩化哲學》的結語部分,劉小楓寫道:“人關心自己的詩魂的超越、心靈的安寄, 為自己的生存意義操心, 是人無法拋棄的內在性。有的問題可能根本無法超越, 但又需要解決。”[1]6這一無法拋棄但又亟需解決的問題指的是什么?所謂“現代之后的審美思想中的惴栗”要如何解讀?關于這一系列審美的現代性主題(劉小楓稱為絕望主題)的理解需要到其1988年所發表的著作《拯救與逍遙》中尋找答案,如此才能把握劉小楓早期美學思想的全貌。
三、現代性問題的延伸探究
1985年在文藝界學術理論發展史上被稱為“方法論”年,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下,“比較文學”或稱“比較詩學”成為許多學者在研究問題時的自覺追求,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以下簡稱《拯》)的引言中坦言自己1986年初版的著作《詩化哲學》(以下簡稱《詩》)也“沒能擺脫積極融貫中西方思想的窠臼,要用莊禪思想映證德國浪漫派哲學”[1]5。然而,對劉小楓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其學術思想始終保持著迅速更新的品質,李澤厚稱他總是“變得很厲害”,并認為“從他的文字中梳理出一條線會很有學術價值”。在《詩》中能夠修正德意志浪漫哲學的魏晉浪漫精神中的靈性與廣柔,到了《拯》的論述里卻轉變為自我批判的對象,將魏晉風度的價值內核視為生物性“求樂”,代表著失敗的價值取向。
由詩性、靈性逐漸走向神性,劉小楓在《拯》中要將《詩》里還未闡盡的現代性問題帶入價值現象學的視野,通過對“中西方詩人對世界的不同態度”引導出超脫與救贖的精神沖突,并在這種沖突中對漢民族精神進行文化尋根,于是儒道禪思想均被歸并為不真實的絕對理念,進而以基督教神學中“拯救”性的精神來拒斥現代虛無主義。
如果說詩化哲學對于生存本體論的強調是反對工具理性的“返魅”嘗試,那么《拯》就是在這種詩意世界觀建立的基礎上通過追問詩人自殺的意義,提出“以虛無主義克服虛無主義,從而恢復古老的虛無主義”的質疑,重新還原作為絕對精神的基督教與古希臘神學的路徑,在劉小楓看來,目的在于挽救現代社會中價值崩潰的歷史厄運。
從《詩》到《拯》,劉小楓反思現代性的書寫方式與后現代主義哲學,特別是與德里達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思想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結關系。在《詩》的再版記中,劉小楓自己就曾提及:“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浪漫派哲學與后現代的關系:本書初版時,后現代哲學在西方正揮灑自如地形塑著自己。”[1]12首先,二者都致力于打破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困境,意圖實現反中心、反傳統的價值重塑。劉小楓用詩意思維和宗教精神來顛覆傳統認知論的努力,在德里達那里,呈現為反語言中心主義,強調元書寫、“替補”以及“延異”等一系列動搖固有等級制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延異”概念的提出,德里達曾自述:“中心并不存在……并且在一種非場所中符號替換無止境地相互游戲著,先驗所指的缺席無限地伸向意謂的場域和游戲。”[6]而“延異”就是這樣一種嬉戲活動,以符號所指的延擱伙同無處不在的書寫痕跡來拆除聲音的在場特權。需要注意的是,延異的存在拒絕精確的定義活動,因為它是無法宣之于口的未名之物,一旦留下痕跡,就會陷入自我解構的悖論之中。舉個通俗的例子,大家都曾打過一個字謎:什么事物,一旦說出它的名字,就會立即消散?答案是沉默,答案也是延異。
其次是隱喻性的哲學表達。無論是詩化哲學自身的表達方式,還是劉小楓闡述上的詩化言辭對傳統社論話語體系的反叛,其隱喻性特征都是不明而喻的事實。對于后現代思想家來說,他們“拒絕現代性的話語表征(地圖),而代之以拼貼畫(collage),拼貼畫意味著總是處于流動狀態,觀看拼貼畫的人實際上參與到了意義的生產之中”[7]。解構者要做的始終是證明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互文性的文本與充滿隱喻的符號系統使哲學向詩過渡,這種開放性的解釋態度保證了意義始終處于生成狀態。正如德里達所說:“與其說隱喻在哲學的文本之中,不如說哲學文本是在隱喻之中”。[8]
最后,德里達哲學思想的最終彼岸即彌賽亞性與劉小楓推崇的基督教精神相似,都將落腳點放在了宗教價值指向上。彌賽亞(Messiah)最初來源于《圣經》,是希伯來語里的所謂“受膏者”,也即“天選之子”,具有特殊的力量。德里達在《維拉諾瓦圓桌討論》會上的講演中解釋過這個詞,他認為彌賽亞性結構是一種開放的經驗,是一種對未來和他者到來的期待,經由正義及和平所承諾。陳曉明教授對此認為,“這種期盼不是消極的等待,它同時具有一種解放和革命的意義”[9]。劉小楓和德里達最終面向先驗純粹精神,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抑制工具理性的擴張,但在人的生存之外設立了一個象征永恒的絕對真理,卻又落入了主體哲學的窠臼。
事實上,在《詩》中劉小楓所強調的生存本體論視野,存在著建立主體間性美學的趨勢,然而到了《拯》,基督教的“拯救”價值便壓倒一切地成為歸謬的依據,將先前所做的取消主客體對立關系的對話嘗試一筆勾銷,絕對精神再次作為世界本源統治一切,回到了實體本體論的原點。
四、面對現代性危機的主體間性美學轉向
主體間性這一理論概念是由胡塞爾所創造并用于解決先驗主體性的片面性問題的,現象學哲學以主體間性試圖達到個體與他人的溝通可能,這種“現象”的客觀性事實上是純粹的主觀性,且意向性還原的過程并不拒絕邏各斯的在場,在德里達看來,其仍舊是沒有擺脫傳統形而上學認識論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同時,主體間性發生在對象性的認識論思維框架里面,本質上還是主體哲學的闡釋行為。
在《拯》中,劉小楓分析了歷史理性對價值真實的壟斷解釋權,以及其棄絕神圣絕對價值的思想背景,又通過進一步考察這種理性思維轉化為“實存情緒”的本體論依據,最終得出這種哲學態度不能夠為人的生存在世提供真正的價值和自由,于是被其否定的神性精神得到反證,成為對抗價值虛無主義的終極根據。運用胡塞爾還原思路構建起這種價值現象學視野的劉小楓,也同樣局限在人與世界基本關系視野的主體哲學之中,從《詩》到《拯》,劉小楓始終執拗于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他者,所強調的是個體的精神追求和救贖指向,確立起的是主體性而非主體間性。而主體哲學在面對現代性難題時,依舊停留在人與世界的二重割裂關系中,并不能夠為實現人的真正自由提供有效方案。于是,德里達和劉小楓面對現代性危機所寄望的高于理性的純粹精神“其結果必然是走向告別現代性的審美主義或神秘主義,走向泯滅現代性分化、徹底否定現代性成就的原始哲學”[10]。關于這一點,姚新勇和翟崇光也有著相同的質疑:“劉小楓在自己的思想歷程中,沒有想到過在批判現代性的同時以主體間性來修整現代理性,……反而是從最初的‘反思現代性開始直到最終告別了現代啟蒙”[11]。
一方面,劉小楓在破除主體性權威神話的過程中混淆了自康德以來就一直在強調的“認知主體”與“價值主體”的界限,在劉小楓美學思想的最終指向上,人將其主體價值讓渡給了外在的抽象絕對精神,神性之維壓倒了工具理性的同時,也消解了人實現自為存在的可能性,這一為了抵抗虛無主義所提出的構想事實上正引向了個體自身生存價值的虛無主義。
另一方面,劉小楓對“詩化思維”與基督教“拯救”精神的強調呈現出“鄉愁”式的回歸傾向,即還原現代性發生之前原初哲學的特征。然而正如哈貝馬斯所看到的,現代性的發生伴隨著主體性觀念的確立,黑格爾歷史哲學中“正反合”的辯證邏輯強調的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倒退式的返歸和重復。以后現代的方式將主體性打成一地零碎的盲目行動必然導致價值虛無主義,所以在擺脫認知思維中心主義的傲慢的同時,不能忽視個人作為“價值主體”的尊嚴,也就是說,要扭轉“我思”與認知對象的分裂關系,必須實現的是主體間性,而其中的關鍵在于將外部對象提升到主體地位,而非將人降至對象世界的無機存在,強調的是主體間進行平等對話的良性互動。
那么,主體間性在現代哲學發展進程中究竟意味著什么?在賀來那里,“主體間性”意味著“對立、統治等不平等的交往關系徹底失去了合法性:每個人都是宇宙中一個有限的個體,需要向他人開放,需要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不斷豐富自己”[12]。
楊春時教授根據主體間性在不同領域中的意義差異,將其分為三種概念,即社會學的主體間性、認識論的主體間性和本體論(存在論、解釋學)的主體間性[13]。主體間性問題最早出現在社會倫理學領域中,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紀神學家討論倫理學問題,到馬克思、哈貝馬斯將其引入社會實踐關系之中,歷經漫長的發展歷史。哈貝馬斯所提出的“交往行為理論”,為現代意識結構提供了溝通和對話的渠道,以此來抗拒人類中心主義的主體哲學根本困境。認識論領域中關于主體間性的探索,除了建立先驗主體性現象學的胡塞爾外,還有提出知覺現象學的梅洛-龐蒂,但在楊春時看來,認識論的主體間性依照的還是主體論意義上的主客對立思維框架,不能夠解決審美何以可能的問題。最后,楊春時得出結論:在主體間性的三個領域中, 只有本體論(存在論、解釋學)的主體間性可以成為美學建構的基礎。
那么,主體間性美學又是如何擔當自身現代使命,來解決人的生存意義問題的?大衛·格里芬曾提出“返魅”來對抗韋伯“祛魅”所造成的工具理性暴政,以過程哲學的有機整體論來實現審美救贖。“返魅”科學觀試圖彌合人與外界自然的分裂,這一點與主體間性美學的追求是共通的。
詩人自殺的根源或許不在于絕對神圣價值的磨滅和無望,更多的是一種與他人、外部世界溝通的不可能,即薩特所提出的“他人即地獄”,始終無法和諧共在的“他者”使生存在世的詩人陷入左沖右突的艱難處境,純粹精神的重建仍是一種外在于感性個體的精神實體,不能為詩人提供生存的方式,即解答生存何以可能的問題。而主體間性美學所建立的是一種始終處于生成狀態、允許對話的價值依據,正如楊春時教授所言:“要求自由本性的充分實現就必須把主體性提升為主體間性,世界由客體變成了主體,審美個性取代現實個性,人與世界的關系變成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和諧公在并最終融合為一體的關系。”[14]主體間性美學消解個體與社會的對立,建立起主體間實現充分和諧的世界,是現代人克服異化的避難所,通過共情感使自我體驗與對象體驗的合而為一,最終將通向“物我交融”的澄明之境。
參考文獻:
[1]劉小楓.詩化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席勒.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古典文藝理論叢書(第二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48.
[3]張偉.文藝理論研究中的知識論前提反思與生存本體論建構[J].文藝研究,2007,(5):26-34.
[4]孫正聿.存在論、本體論和世界觀:“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的辯證法[J].哲學研究,2016,(6):25.
[5]劉小楓.拯救與逍遙[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6.
[6]德里達.書寫與差異[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505.
[7]查爾斯·E. 布萊斯勒.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M].趙勇,李莎,常培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125.
[8]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M].Chicago:The Harvester Press,1982:258.
[9]陳曉明.德里達的底線——解構的要義與新人文學的到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7.
[10]趙良杰.價值現象學的迷失:評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的思想視野[J].文藝研究,2014,(9):155.
[11]姚新勇,翟崇光.劉小楓學術轉向批判[J].揚子江評論,2017,(2):40.
[12]賀來.寬容意識[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117-118.
[13]楊春時.本體論的主體間性與美學建構[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8.
[14]楊春時.文學理論新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93.
The Dilemma of Survival Ontology:A Reflection on Liu Xiaofengs
Early Aesthetic Thoughts in 1980s
CHEN Yuey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6,China)
Abstract:From poetical ontology to ontological poet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rvival ontology of existence in Die dichtende Philosophie provides a dimension to reflect on modernity, the idea of realizing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has profou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he them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is embodied in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to reject modern nihilism with the pure spiritual value of “salvation” in Christian theology, in contrast with the deconstruction thought of post-modernism anti-logos centrism, it forms a complementary field of vision. By reflecting on the dilemma of survival ontology in Liu Xiaofengs early aesthetic thoughts,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 redemp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aesthetics in the face of modernity crisis.
Key words: ?Liu Xiaofeng; Ontological poetics;? Survival ontology;? Modernity; Intersubjectivity
編輯:黃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