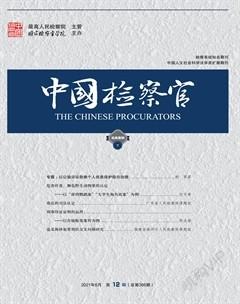個人信息領域消費欺詐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探索與實踐
趙昊宏
摘 要:檢察機關應結合具體案情確定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類型。從檢察機關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初衷分析,為消費者提供正義正是公益訴訟替代性和補充性的價值體現。針對非法獲取消費者個人信息并進行消費欺詐的行為,檢察機關提出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可以加大對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和權益行為的懲治力度,維護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權益,對懲治和預防該領域嚴重違法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民事公益訴訟 消費欺詐 懲罰性賠償 思考
一、基本案情與辦案過程
(一)基本案情
2017年以來,被告李某通過購買、置換等方式非法獲取包含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信息的電子數據。經北京網絡行業協會電子數據司法鑒定中心對李某存儲數據的設備進行鑒定,并經核查篩除重復信息,李某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共計1290.9176萬條。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4月1日,被告李某伙同郭某某(另案處理),將李某非法獲取的19061條個人信息數據非法出售給韓某某(另案處理)、蘇某某(另案處理),李某從中獲利人民幣3000元。
2018年1月2日至2019年4月22日期間,被告李某先后在多地租住 “工作室”,雇傭電話銷售客服,由李某操控電腦系統“磐石云”電銷外呼軟件,導入其非法獲取個人信息數據資源,通過電腦自動批量群呼撥打騷擾電話方式推銷商品。在推銷過程中,被告李某虛構或者冒用收藏品公司的名義,使用含有“收藏價值高”“有升值空間”“全國限量發行”等詞語的虛假話術,欺詐消費者購買腎寶片、紀念冊、紀念幣、禮品、郵票、字畫等商品。經查,李某利用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數據以撥打騷擾電話方式推銷商品欺詐消費者,實際取得收入金額共計人民幣55.4605萬元。
(二)辦案過程
1.線索來源及線索初核。2019年8月2日,易縣人民檢察院刑檢部門對郭某某等三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訴。這起刑事案件引起該院民事行政檢察部門的重視,對于是否能辦理公民個人信息這個新領域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因無相關判例參考,也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或者地方人大的授權,還處于審慎穩妥的探索階段。案件請示到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后,市檢察院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專門進行討論研究,一致同意易縣檢察院對郭某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并層報了河北省人民檢察院審批同意。2019年9月1日,易縣人民檢察院向易縣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損失、公開賠禮道歉等。2019年11月8日,易縣人民法院判決支持了檢察機關全部訴訟請求。
在辦理郭某某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請示案件過程中,李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線索進入市檢察院的視野。市檢察院辦案人員發現郭某某向他人出售的個人信息數據全部都來源于李某。經初步核實,李某因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已經于2019年5月20日被高碑店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2019年7月15日高碑店市公安局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經請示省檢察院批復同意,2019年11月8日,保定市人民檢察院對李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立案。
2.調查核實。市檢察院辦案人員調取了李某案件的全部刑事偵查卷宗材料的復制件,詢問了郭某某等相關證人,到看守所詢問了李某。經了解,李某除侵犯眾多不特定公民個人信息權益外,還存在向個人信息權益人進行營銷滋擾侵犯他人隱私權以及對個人信息權益人進行消費欺詐等嚴重違法行為,檢察機關是否可以代表消費者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訴請什么,是辦案人員初步調查以后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為此,辦案人員聯系了河北大學法學院(保定市檢察院公益訴訟研究基地)進行專家咨詢論證。參與論證的教授們都支持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并提出檢察機關可以嘗試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第1款請求法院判令李某支付消費者購買商品價款的三倍懲罰性賠償金。
通過咨詢論證和民意調查,辦案人員明確了調取證據重點,即查清李某對公民個人信息權益人進行消費欺詐和獲取銷售價款收入的事實,也是提起懲罰性賠償訴訟的依據,這部分證據要靠公益訴訟檢察官獨立調查核實完成,并且也必將是庭審中爭議的焦點,是訴訟的關鍵。只有以最嚴格的證據標準使這部分事實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程度,才能為提出懲罰性賠償金奠定證據基礎。辦案人員制定了詳細的取證方案并進行了嚴格規范的取證工作:一是查清了李某通過順豐速遞銷售商品的具體數據。通過和已經調取的李某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數據進行比對之后,證實李某全部銷售記錄關聯的收件人(也就是消費者)均是李某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權益人;二是查清了李某銷售商品的價款收入。對比李某通過順豐快遞發貨的貨款金額與順豐快遞轉入李某銀行卡的款項金額,確認李某銷售的商品收入金額。結合李某筆錄,剔除發貨地點和托寄物名稱不符的運單信息,得到李某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以欺詐手段推銷商品的收入金額;三是查清了李某欺詐消費者的行為。調取了李某電腦里、U盤中存儲的其銷售商品所使用的話術音頻及話術文檔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對46名從李某處購買商品的消費者進行了詢問,證實了李某的欺詐行為。
辦案取證工作輾轉北京、杭州、石家莊等地,2020年受疫情的影響,多份證據通過北京市檢察機關、杭州市檢察機關協助完成,部分證據如46名消費者證言則是依托公安機關全國取證協作平臺進行異地協助完成。2020年6月完成了全部取證任務。
3.訴前程序及訴訟過程。經在全國范圍發行的媒體上公告,公告期滿后,沒有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提起訴訟。2020年3月18日河北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復函建議由檢察機關起訴。經河北省檢察院批復同意,保定市檢察院于2020年7月20日將此案向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主要訴求:(1)請求判令被告支付三倍懲罰性賠償金,共計人民幣166.3815萬元;(2)請求判令被告采取有效措施刪除所有非法持有的公民個人信息數據;(3)請求判令被告在國家級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4日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并于同年12月30日判決支持了檢察機關全部訴訟請求。
另悉,李某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于2020年10月29日被高碑店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萬元。
二、本案爭議焦點分析
(一)對“眾多不特定”概念的理解爭議
李某及其代理人辯解認為,李某行為所針對的是1200余萬條信息中的消費者,屬于確定的范圍,故而不屬于不特定公民的定義。檢察機關認為,首先,李某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即針對社會公眾不特定個體;其次,李某的行為通過計算機軟件在其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中通過隨機篩選,尋找潛在消費個體亦具有不特定性;第三,本案中受害人無論從年齡、性別、所處地域等細節分析均具有不特定性。
(二)對李某行為是否屬于消費欺詐的爭議
李某及其代理人辯解其推銷商品的行為屬于正常的商業活動,不是欺詐,消費者驗貨后再付款,屬于自愿選擇,其并非陷入錯誤認識后交付的財產。檢察機關認為,李某推銷商品雖然采取消費者先驗貨后付款的方式,但消費者同意驗貨是基于李某事先虛構或者冒用收藏品公司、隱瞞商品系購買于馬甸市場并非收藏品且不具備“有收藏價值、有升值空間、限量發行”等真實情況,其虛構隱瞞行為使得消費者陷入錯誤認識自愿交付財產最終受到財產損失,消費者本身雖具有較強的選擇性,但其購買行為系受到錯誤誘導所致,并非基于其真實意思表示和主觀判斷,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與其預期明顯不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2021年1月1日廢止)第68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
(三)已經承擔刑事責任,是否還應當再承擔民事責任的爭議
李某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已受到刑事追究,但不影響其承擔民事責任。原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參考民法典第187條規定,“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影響承擔民事責任;民事主體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優先用于承擔民事責任”。
三、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并訴求懲罰性賠償的思考
(一)有關辦案類型如何選擇
本案選擇民事公益訴訟辦案類型更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發現案件線索后,辦案人員在選擇行政公益訴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還是民事公益訴訟上進行了利弊權衡。
1.案件不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辦案人員發現案件線索時,李某已經因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訴,且李某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推銷商品的行為是否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司法辦案單位之間存在認識分歧,最終檢察機關以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和獲利數額的證據不足、事實不清對該部分事實未提起公訴,如果附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訴訟的事實會出現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范圍不一致的情況,如果僅就李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附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而對李某民事欺詐事實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不僅增加訴累、拖延訴訟進程,更難以保證訴訟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相對于李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而言,其更為嚴重的侵權在于對信息數據的非法商業化利用和欺詐眾多不特定消費者獲利的行為,這種嚴重的民事侵權行為更具有可訴性和訴訟的必要性。
2.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條件欠缺。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公益訴訟的前提條件是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本案中受到侵害的社會公共利益包括眾多不特定公民的個人信息權益、隱私權和消費者合法權益,這些侵害事實的存在與李某侵權行為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尚無證據證實負有監管職責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網信部門、電信部門等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
3.消費者難以通過訴訟進行有效維權,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也很難主動發現案件線索并提出維權訴訟。辦案人員調取的發貨清單以及快遞公司到付貨運單等證據顯示,李某獲取的個人信息系從網絡上兜售流轉取得,所使用的發貨人均為化名,發貨地址也非李某實際住址,個人信息權益人(消費者)自身無法獲知信息如何泄露以及如何被他人非法進行商業化利用,同時也難以自行取證并準確查清侵權人和侵權事實,即使上述問題都能解決,因涉案消費者遍及全國各地且貨品單價都在幾千元以內,單獨維權的訴訟成本和時間成本也都太高。本案訴前已函告河北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其明確復函不起訴,建議由檢察機關起訴,檢察機關也進行了訴前公告。
(二)有關檢察民事公益訴訟調查核實權的行使
司法證明的環節包括取證、舉證、質證、認證。其中,取證是基礎,是庭前為獲取證據而開展的專門調查活動,是司法證明的第一個環節。但實踐中,檢察公益訴訟調查核實權法律保障不足已經制約了取證工作的開展,比如,要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取物證、書證,向金融機構調取查詢當事人賬戶信息或者銀行流水,所需要的法律文書包括《調取證據通知書》《協助查詢金融財產通知書》等,文書中所引用的法律依據均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依據系司法解釋,其效力遠低于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辦案中,個別金融機構以適用法律是司法解釋而非法律為由拒絕提供協助查詢。此外,有關檢察機關公益訴訟調查核實權的規定散見于檢察機關辦案指南或者各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或決議中,其對外效力不足、保障不力。特別是個人信息領域案件的取證,被侵害對象分布范圍廣、遍布全國各地,甚至涉外,檢察機關公益訴訟調查核實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成為困擾公益訴訟發展的最現實問題。
(三)有關個人信息領域檢察民事公益訴訟提出懲罰性賠償訴求的價值
1.檢察機關能否提出懲罰性賠償訴求。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這是對公益訴訟檢察“以訴的形式履行法律監督本職”新的更高要求。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民法典也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的懲罰性賠償規定,為檢察機關探索建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撐。河北省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檢察公益訴訟的決定》也明確授權檢察機關辦理個人信息保護等領域公益訴訟案件,該決定也同時規定,“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應當對食品藥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實施懲罰性賠償,落實食品藥品安全監督工作制度”。由此可見,地方人大已經授權檢察機關在食品藥品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也就是檢察機關可以以公益訴訟起訴人的身份提出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
2.懲罰性賠償訴求提出的必要性。公益訴訟具有替代性、補充性和威懾性。當消費者損失較小且投入訴訟的成本遠大于收益時,理性的選擇便是放棄訴訟。因此,從檢察機關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初衷分析,為消費者提供正義正是公益訴訟替代性和補充性的價值體現。由此可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受害人眾多、造成的損害較小且分散,檢察機關在該類訴訟中享有提起懲罰性賠償的權利,讓不法經營者承擔更大的損害賠償責任,對其形成威懾,能夠最終達到減少此類違法案件數量的目的。同時,也必須要考慮懲罰性賠償提出的適用條件,準確把握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遏制和預防嚴重不法行為的功能定位,結合侵權人主觀過錯程度、違法次數和持續時間、受害人數、損害類型、經營狀況、獲利情況、財產狀況、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等因素,綜合考慮是否提出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具體到本案分析,李某違法次數多、持續時間長、受害人眾多、不僅損害個人信息權益還侵犯隱私權和消費者權益、李某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被處罰金三萬元顯然難以達到增加其經濟責任的目的等,因此對其提出懲罰性賠償,可以起到責罰相當的懲戒與預防作用。
3.個人信息領域懲罰性賠償訴求提出的社會意義。當前,個人信息泄露、電話營銷欺詐嚴重侵害個人信息安全和消費者合法權益,是民生痛點,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侵犯個人信息行為之所以司空見慣,是因為不法分子能夠從個人信息違法中獲取經濟利益,其后果是違法犯罪分子能夠利用信息對信息權益人進行精準侵害或者使得信息權益人處于被侵害的高度危險中。檢察機關針對不法分子利用公民個人信息數據欺詐消費者的嚴重違法行為,探索提出懲罰性賠償訴求,是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的有益嘗試,有利于加大對嚴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和《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要求,激活懲罰性賠償制度,起到懲治和預防嚴重違法行為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79條將懲罰性賠償作為承擔民事責任的一種方式,“法律規定懲罰性賠償的,依照其規定”,提出懲罰性賠償訴求必須要有法律明確規定。
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個人生活安寧屬于隱私權受法律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當眾多不特定權利主體諸多合法權益均受到嚴重侵害時,檢察公益訴訟將成為守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線,通過懲罰性賠償,懲戒、制裁并威懾、警示、預防個人信息領域嚴重違法行為的發生,從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利益不受非法侵犯,也是本次訴訟的意義。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八檢察部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07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