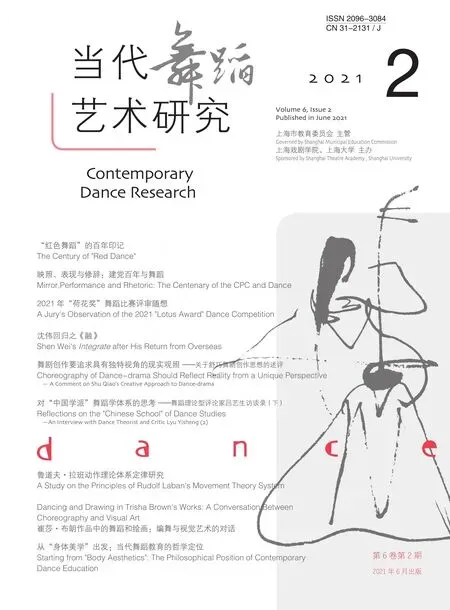2021年“荷花獎(jiǎng)”舞蹈比賽評(píng)審隨想
王 玫
好多年沒(méi)有參與舞蹈賽事的評(píng)審活動(dòng)了。因?yàn)樽鲅芯浚枰锌醋髌贰⒂^察現(xiàn)象,今年就參加了舞蹈賽事的評(píng)審活動(dòng)。在超長(zhǎng)的時(shí)間區(qū)隔之下,果然獲得了強(qiáng)烈的感受和思考,體現(xiàn)在:第一,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區(qū)別;第二,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自我體認(rèn);第三,舞蹈明星的自我體認(rèn);第四,無(wú)關(guān)舞蹈種類(lèi)的感動(dòng)。
一、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區(qū)別
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概念,以及它們?cè)诮F(xiàn)代的中國(guó)建立于什么時(shí)間、什么地點(diǎn)、由誰(shuí)建立、建立的初衷,筆者都不清楚。但對(duì)兩者的區(qū)別卻一目了然。同時(shí),每個(gè)舞人都心里發(fā)慌,因?yàn)殡m然看得明白,卻難以說(shuō)清道理。其實(shí)也不是所有道理都難以說(shuō)清,而是符合道理的“道理”難以說(shuō)清,不符合道理的“道理”也難以說(shuō)清。
第一,關(guān)于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
兩個(gè)舞種的“原生概念”,都是指當(dāng)下某一時(shí)間段內(nèi)的舞蹈編創(chuàng)作品,也包括兩者在相關(guān)時(shí)間內(nèi)前后延伸的“作品繁衍”。如20世紀(jì)初的瑪莎·格雷姆就是現(xiàn)代舞的代表;到了60年代,賈德遜紀(jì)念教堂(Judson Memorial Church)的藝術(shù)家們就是當(dāng)代舞的代表。所以,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舞種及其原生概念,描述的就是20世紀(jì)初的“瑪莎·格雷姆們”到60年代的賈德遜紀(jì)念教堂的藝術(shù)家們,在這一段時(shí)間內(nèi)的舞蹈編創(chuàng)作品以及前后的“作品繁衍”。其特征有兩個(gè):第一,現(xiàn)代某一時(shí)間段內(nèi)產(chǎn)生的編創(chuàng)作品;第二,該時(shí)間前后的“作品繁衍”。就其總體的思潮而言,現(xiàn)代舞發(fā)生在前,當(dāng)代舞發(fā)生在后。
往下就得說(shuō)語(yǔ)言的“異化”了:原本的現(xiàn)代和當(dāng)代兩詞,共同具有時(shí)間的特性—直指某段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在的時(shí)間”。可以想見(jiàn),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代舞以“現(xiàn)代舞”命名,除了區(qū)別于傳統(tǒng)舞外,其發(fā)生于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在的時(shí)間”才是主因。但是,當(dāng)另外一種新舞在現(xiàn)代舞誕生的幾十年后再誕生,被命名為“當(dāng)代舞”,其命名之緣由也一樣,除了區(qū)別于已經(jīng)是“傳統(tǒng)現(xiàn)代舞”的現(xiàn)代舞外,其發(fā)生于最新的“現(xiàn)在的時(shí)間”也是主因。所以,現(xiàn)代和當(dāng)代原本幾近相同的詞義,因?yàn)樗汲钡母爱惢保含F(xiàn)代舞“異化”為傳統(tǒng)舞,當(dāng)代舞“異化”為現(xiàn)代舞。隨后,思潮繼續(xù)“繁衍”,并出現(xiàn)了更多的命名混亂,如后現(xiàn)代舞、后后現(xiàn)代舞等。但是,其混亂的底層邏輯卻與上文所述相同:首先是為了區(qū)別之前產(chǎn)生的各種舞蹈,筆者索性將其稱(chēng)為“前舞”,并把這種種“前舞”從時(shí)間發(fā)展線索上定位為傳統(tǒng)舞;其次是發(fā)生于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在的時(shí)間”。
相較而言,現(xiàn)代舞與后現(xiàn)代舞這一對(duì)概念命名關(guān)系相對(duì)清晰—既于時(shí)間方面推演合理,也客觀呈現(xiàn)了思潮的更迭;現(xiàn)代舞與當(dāng)代舞這一對(duì)命名關(guān)系相對(duì)混沌—雖然呈現(xiàn)了思潮的更迭,但二者更迭的客觀時(shí)間卻難以分辨。
當(dāng)現(xiàn)代舞蹈命名過(guò)多、雜亂難辨的時(shí)候,大家又開(kāi)始“九九歸一”。發(fā)現(xiàn)其實(shí)怎么命名并不重要,處于什么年代、什么地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獨(dú)立思考。先從成功學(xué)上說(shuō):獨(dú)立思考才能與眾不同,與眾不同才能引起舞蹈思潮更迭,舞蹈思潮更迭才能“降維打擊”所有的“前舞”。再?gòu)木帉?dǎo)學(xué)上說(shuō),獨(dú)立思考才能誕生獨(dú)特的作品,獨(dú)特的作品才能被社會(huì)辨識(shí)。社會(huì)辨識(shí)是藝術(shù)表達(dá)的必要前提,辨識(shí)之后,其個(gè)人訴求才能通過(guò)作品在社會(huì)上產(chǎn)生效用。
第二,關(guān)于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
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概念與其“原生概念”既相同又不同。
相同點(diǎn):某段“現(xiàn)在的時(shí)間”編創(chuàng)的作品。
不同點(diǎn):不是前后相繼發(fā)生,而是同時(shí)地、重迭地發(fā)生。
當(dāng)兩種舞蹈編創(chuàng)同樣發(fā)生于“現(xiàn)在的時(shí)間”,并同時(shí)重迭地發(fā)生,其發(fā)生時(shí)間之先后就沒(méi)有區(qū)別。沒(méi)有區(qū)別何以需要區(qū)別其名?其需要區(qū)別的到底是什么?毋庸置疑,中國(guó)的當(dāng)代舞之謂就是為了區(qū)別于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舞。但是,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舞和中國(guó)的當(dāng)代舞到底有什么不同?
其一,編創(chuàng)主體不同:現(xiàn)代舞的編創(chuàng)主體龐雜,什么人都有,但是其龐雜又可清晰地歸一為“民”;當(dāng)代舞的編創(chuàng)主體單一,主要為軍隊(duì)中的職業(yè)舞人。
其二,作品不同:二者的舞蹈作品,先是共同發(fā)生于某一段“現(xiàn)在的時(shí)間”,共同具有現(xiàn)代舞蹈形態(tài)的特征,但是現(xiàn)代舞的作品更具個(gè)體意識(shí),而當(dāng)代舞的作品更具集體意識(shí)。
綜上,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區(qū)別主要是兩個(gè):一是編創(chuàng)主體不同,二是編創(chuàng)主體攜帶的意識(shí)不同。當(dāng)然,其后的部分當(dāng)代舞又發(fā)生“異化”:作品編創(chuàng)于“現(xiàn)在的時(shí)間”,卻具有現(xiàn)代舞的形態(tài)特征,又相對(duì)表現(xiàn)出集體意識(shí),這些作品也被編導(dǎo)和表演者自我體認(rèn)為是當(dāng)代舞。
當(dāng)然,中國(guó)的舞蹈形態(tài)以及概念自成一派不是問(wèn)題,不用亦步亦趨于他人。但是自成一派還需要三層考量:其一,我們需要區(qū)別的到底是什么?其二,能否借用歷史之力和他域之力?其三,當(dāng)需要借力時(shí),已經(jīng)約定俗成的符號(hào)勢(shì)必影響其在現(xiàn)在的應(yīng)用,這一點(diǎn)是否清晰考慮過(guò)?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異同成為“世紀(jì)之謎”,原因就在于:概念源自他域,事實(shí)卻自有特點(diǎn)。事實(shí)上,借用他域的概念是常態(tài),不見(jiàn)得就是問(wèn)題。但是,借用當(dāng)慎重,因?yàn)楦拍畈恢皇歉拍睿浜诵氖巧筛拍畹氖聦?shí),概念的借用出現(xiàn)“消化不良”,是因?yàn)樗虻氖聦?shí)與我們的事實(shí)不符。
第三,關(guān)于中國(guó)今天的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
今天的當(dāng)代舞又發(fā)生了巨變。因?yàn)椴筷?duì)文工團(tuán)的改革,軍隊(duì)的編創(chuàng)主體基本全員“消解”。其“消解”意味著,原本區(qū)別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一大指標(biāo)—編創(chuàng)主體的區(qū)別已然不再。因此,識(shí)別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就更加困難了。但是,識(shí)別的困境也是機(jī)遇。
事實(shí)上,以編創(chuàng)主體區(qū)別舞蹈的種類(lèi)原本可行,但其需要正向而不是反向的思考。正向在于,時(shí)間不同,空間不同,舞蹈亦不同,并自然形成不同的編創(chuàng)人群,這個(gè)順其理而成其章。但如果反向行之,在時(shí)間相同、空間相同,舞蹈也相同的情況下,卻硬性劃定不同的編創(chuàng)群體,并以編創(chuàng)群體而劃定舞種,其理不順,更難成章。
舞蹈編創(chuàng)的原理類(lèi)似于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原理,都是個(gè)人的創(chuàng)造。因?yàn)槿说母惺芎捅磉_(dá)以個(gè)體的形式發(fā)生,同時(shí)也表達(dá)著個(gè)體的認(rèn)識(shí),這是物理世界的客觀事實(shí)。如果有不同,其不同絕不在于舞蹈編創(chuàng)的意識(shí),而是舞蹈編創(chuàng)的對(duì)象。對(duì)象有兩種—自己或者他人。也就是說(shuō),對(duì)象可以是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是他人的生活。
但現(xiàn)實(shí)是他人常被“人民”一詞替代,并產(chǎn)生了替代的問(wèn)題。這里的“人民”一詞并非客觀存在的“人民”之義,而是主觀的、帶有修辭色彩的、有意識(shí)塑造的詞語(yǔ),其傾向是拔高,結(jié)果就導(dǎo)致有意識(shí)塑造的“人民”不但高于他人,也高于自己(編創(chuàng)者本人)。如此,自己和他人這一對(duì)詞語(yǔ)關(guān)系,原本具有轉(zhuǎn)換的自由而揭示出人的種種復(fù)雜性,現(xiàn)在則喪失了自由轉(zhuǎn)換的可能:拔高的人民位于自己的頂端;降低的自己位于人民的底端,進(jìn)而也喪失了揭示人之多樣化的可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是揭示人性。其對(duì)人性的揭示正是基于他人與自己可以自由轉(zhuǎn)換的事實(shí)。正是因?yàn)檫@一自由轉(zhuǎn)換的事實(shí),才可能最小范圍地揭示他人和自己的關(guān)系真相,最大范圍地揭示我們和人類(lèi)的關(guān)系真相。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兩點(diǎn)結(jié)論:其一,當(dāng)代舞的編創(chuàng)主體已經(jīng)“消解”;其二,編創(chuàng)意識(shí)的分野并不是事實(shí)。當(dāng)代舞是時(shí)候?qū)ふ页雎妨恕F涑雎酚袃蓷l:一是從編創(chuàng)的時(shí)間方面歸屬于現(xiàn)代舞,二是從編創(chuàng)的題材方面并入現(xiàn)實(shí)題材舞蹈。筆者認(rèn)為,其終極出路,包含現(xiàn)代舞的終極出路,似乎應(yīng)該并入現(xiàn)實(shí)題材舞蹈。因?yàn)楝F(xiàn)實(shí)題材舞蹈既是特定題材的舞蹈創(chuàng)作,其形式也表現(xiàn)著“現(xiàn)在的時(shí)間”的特性。
二、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自我體認(rèn)
此次“荷花獎(jiǎng)”中現(xiàn)當(dāng)代舞蹈的比例是1∶2。其中,當(dāng)代舞的編創(chuàng)主體已經(jīng)沒(méi)有了軍隊(duì)職業(yè)舞人,但評(píng)委卻大多是軍隊(duì)職業(yè)舞人。軍隊(duì)職業(yè)舞人的“見(jiàn)與不見(jiàn)”,不經(jīng)意間呈現(xiàn)了中國(guó)舞蹈的歷史變遷。
比賽中,現(xiàn)代舞和當(dāng)代舞的分界就全靠編導(dǎo)自己的體認(rèn)了:認(rèn)為自己的舞蹈是現(xiàn)代舞,就報(bào)現(xiàn)代舞組,劃歸現(xiàn)代舞類(lèi)別比賽;認(rèn)為自己的舞蹈是當(dāng)代舞,就報(bào)當(dāng)代舞組,劃歸當(dāng)代舞類(lèi)別比賽。由此卻導(dǎo)致現(xiàn)代舞賽場(chǎng)出現(xiàn)兩種情況:“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就是現(xiàn)代舞”(報(bào)名現(xiàn)代舞組,形式上也是現(xiàn)代舞的某一種);“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卻是傳統(tǒng)舞”(報(bào)名現(xiàn)代舞組,形式上卻是傳統(tǒng)舞的某一種)。
第一,“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就是現(xiàn)代舞”。
這一類(lèi)作品,大多看幾眼就想放棄。因?yàn)檫^(guò)于陳舊:編舞形式陳舊、跳舞形式陳舊、思考舞蹈陳舊、舞蹈的思考也陳舊。其陳舊還表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上,即思維結(jié)構(gòu)的陳舊,導(dǎo)致舞蹈的思考陳舊、思考的舞蹈陳舊以及編舞的和跳舞的形式陳舊。有趣的是這一類(lèi)編導(dǎo)的共同特征:他們多多少少了解一點(diǎn)現(xiàn)代舞,或者多少接受過(guò)現(xiàn)代舞蹈的教育,所以才有“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就是現(xiàn)代舞”的可能。也因?yàn)槿绱耍麄儾拧耙嗖揭嘹叀庇诂F(xiàn)代舞,其編創(chuàng)和舞蹈,基本就是照著現(xiàn)代舞既有的形式和思路依樣畫(huà)葫蘆,所以陳舊。
第二,“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卻是傳統(tǒng)舞”。
這一類(lèi)作品,剛開(kāi)始看的時(shí)候特別興奮,因?yàn)槠洹俺醅F(xiàn)”的形態(tài),一反現(xiàn)代舞的常態(tài),以為是對(duì)現(xiàn)代舞的新解。但是看下去卻失望,因?yàn)槿珶o(wú)新解,就是傳統(tǒng)舞蹈編創(chuàng)的思維。
同樣有趣的是這一類(lèi)編導(dǎo)的共同特征:他們大多不了解現(xiàn)代舞。所以他們“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卻是傳統(tǒng)舞”。他們自報(bào)現(xiàn)代舞的緣由,或許是自覺(jué)與傳統(tǒng)舞蹈編創(chuàng)的不同。但是其不同只是停留于動(dòng)作層面而不是思考層面。當(dāng)動(dòng)作層面的編創(chuàng)沒(méi)有思考層面的支撐,其編創(chuàng)將難以脫身于傳統(tǒng)舞蹈編創(chuàng)的定式。
以上兩種情況都是對(duì)現(xiàn)代舞的誤解。現(xiàn)代舞的核心不是舞,而是思想,是獨(dú)立思考的思想。獨(dú)立思考之下,才誕生了種種舞蹈的形式。其舞蹈的形式也有清晰的屬性,即屬于他人—是他人獨(dú)立思考的結(jié)果,其結(jié)果也呈現(xiàn)著他人的生命。所以,現(xiàn)代舞蹈編創(chuàng)的問(wèn)題就在這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知其一:只知道現(xiàn)代舞有固定的形式,所以不斷拿來(lái)。
不知其二:不知道固定形式背后的成因—現(xiàn)代舞一切的固有形式都屬于他人,都是他人編創(chuàng)和研究的結(jié)果,其結(jié)果就是他人生命的結(jié)晶,也閃耀著他人的生命光輝。
舞蹈的形式重要,形式背后的成因更為重要。新的創(chuàng)作當(dāng)然可以借用他人的形式,但應(yīng)該只是借用,借用的目的是發(fā)揮自己:或發(fā)揮自己對(duì)題材的認(rèn)識(shí),或發(fā)揮自己對(duì)世界的認(rèn)識(shí)。但是很遺憾,不少舞人的借用卻反客為主:借題表題,其形態(tài)是重復(fù)現(xiàn)代舞的固有形式。編創(chuàng)的藝術(shù)價(jià)值自然也就因?yàn)橹貜?fù)了他人而難以實(shí)現(xiàn)。
這里需要警覺(jué)的是“自報(bào)現(xiàn)代舞就是現(xiàn)代舞”這一群體的身份:其主體身份往往被認(rèn)為具有先鋒意識(shí),因?yàn)檫@種先鋒意識(shí),這一原本出身于傳統(tǒng)舞蹈的群體,傾心于現(xiàn)代舞,顧自“投奔”現(xiàn)代舞,并自我體認(rèn)為現(xiàn)代舞人。但是其先鋒的心性,卻因?yàn)椴幻鳜F(xiàn)代舞背后的成因,終至形左而實(shí)右,并因其先鋒的身份而貽害不淺。
那么,到底什么是現(xiàn)代舞?盡管其標(biāo)志不是舞而是思考,但是這一舞蹈也有形式,其形式也需要辨識(shí)。現(xiàn)代舞具有眾多而繁雜的形式,不易辨識(shí):你所見(jiàn)過(guò)的形式都可能是現(xiàn)代舞;你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的眾多形式也都可能是現(xiàn)代舞。
情形一:“你所見(jiàn)過(guò)的形式都可能是現(xiàn)代舞”。現(xiàn)代舞的形式眾多而繁雜,原因有兩個(gè):其一,現(xiàn)代舞本身就是個(gè)體生命的呈現(xiàn)形式;其二,浩如煙海的個(gè)體生命創(chuàng)作了眾多而繁雜的作品。但其巨大而多變的體量卻帶來(lái)了辨認(rèn)的困難:這是現(xiàn)代舞嗎?這也是現(xiàn)代舞嗎?這還是現(xiàn)代舞嗎?困難的根源就是“像”與“不像”的觀念:傳統(tǒng)舞蹈以“像”而體認(rèn);現(xiàn)代舞以“不像”而體認(rèn)。現(xiàn)代舞“不像”的體認(rèn)更是登峰造極:眾“大家”的“不像”往往招致“人神共憤”的程度,并重新定義了藝術(shù)的范圍。所以,當(dāng)我們以“像”來(lái)辨識(shí)現(xiàn)代舞時(shí),當(dāng)然困難,因?yàn)槠浔嬲J(rèn)的核心是“不像”。所以,你所見(jiàn)過(guò)的眾多的現(xiàn)代舞的形式都是現(xiàn)代舞,其“是”的核心不是相似的形式,而是相似的獨(dú)立思考,正是其相似的獨(dú)立思考,致其產(chǎn)生了全然不同的形式。
情形二:“你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的眾多形式也都可能是現(xiàn)代舞”。已有的現(xiàn)代舞盡管眾多而繁雜,但其后的現(xiàn)代舞依然需以獨(dú)特性存活并自證價(jià)值。所以,如果新的舞蹈編創(chuàng)想自認(rèn)是現(xiàn)代舞,那么對(duì)過(guò)往眾多而繁雜的現(xiàn)代舞的形式進(jìn)行探索就面臨歧路;相反,放棄形式的追索,建立獨(dú)特的思考,以其思考探索新的形式,這透著獨(dú)特思考的新形式才能成就自己的現(xiàn)代舞。
所以,新的編創(chuàng)如果與先前的現(xiàn)代舞不同,才有可能是現(xiàn)代舞,且可能是最好的現(xiàn)代舞。只是尋求現(xiàn)代舞的形式,是舍本逐末,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事實(shí)上連芝麻也沒(méi)有,因?yàn)檫`背了現(xiàn)代舞的原理而難以成為真正的現(xiàn)代舞;相反,注重現(xiàn)代舞的獨(dú)立思考,以其思考而誕生新的形式,這才是舍末逐本。因?yàn)槠漤槕?yīng)了現(xiàn)代舞的原理而成就了新的現(xiàn)代舞。
但是就新編創(chuàng)而言,摒棄見(jiàn)過(guò)的現(xiàn)代舞形式,以獨(dú)立思考而創(chuàng)作新的形式很困難。因?yàn)榍奥肪褪菬o(wú)路。但是無(wú)路卻有心路:其心路就是深諳現(xiàn)代舞背后的成因—獨(dú)特的思考,以其獨(dú)特的思考才可能創(chuàng)造獨(dú)特的現(xiàn)代舞的形式。
三、舞蹈明星的自我體認(rèn)
不知道從什么時(shí)候開(kāi)始,眾舞蹈明星介入了現(xiàn)代舞。先是他人編、明星跳,后來(lái)就是自己編、自己跳了。最初這都是好的現(xiàn)象,因?yàn)榫幬栌谔瓒裕黠@多了思考,且思考還需要獨(dú)自發(fā)生和進(jìn)行,所以就總體的藝術(shù)活動(dòng)而言,這絕對(duì)是一種進(jìn)步。但是后來(lái)卻出了問(wèn)題:?jiǎn)栴}還是“依樣畫(huà)葫蘆”—當(dāng)某個(gè)舞蹈明星以某種現(xiàn)代舞的形式獲得了成功,該形式便開(kāi)始泛濫。形式逐漸雷同為:舞者的身體條件和能力極好;選擇了非常好聽(tīng)的音樂(lè);在音樂(lè)里自由地舞蹈。
其實(shí),張揚(yáng)極好的身體條件和能力就是一種舞蹈形式和編舞形式,其原理在于打破了原有的舞蹈邏輯,建立了新的舞蹈邏輯,因?yàn)槠湫拢部梢苑Q(chēng)之為現(xiàn)代舞。但是,當(dāng)其形式已經(jīng)“著名”,這“著名”將再次生成邏輯,這時(shí)邏輯需要的就是被打破,而不是被重復(fù)。如果被重復(fù),且不斷地重復(fù),將因?yàn)椤案唷倍a(chǎn)生問(wèn)題。問(wèn)題雖顯而易見(jiàn),卻不斷重復(fù),此次的參選作品中,幾乎所有的男子獨(dú)舞都在其列。原因有兩個(gè):其一,舞蹈編創(chuàng)的原理不清;其二,“天生麗質(zhì)難自棄”。
第一,舞蹈編創(chuàng)的原理不清。
舞蹈編創(chuàng)的原理如下:自己有話想說(shuō),且想向社會(huì)說(shuō),并需要社會(huì)聽(tīng)到;社會(huì)聽(tīng)到而反饋價(jià)值;由社會(huì)反饋的價(jià)值而獲得收益。
這里的關(guān)鍵有兩個(gè):其一是自己的話;其二是自己的話需要社會(huì)的接受和評(píng)價(jià)。但是社會(huì)的接受和評(píng)價(jià)需要條件,首要條件就是鮮明。鮮明與否,與編創(chuàng)的“率先”和“滯后”關(guān)系十分緊密。
編創(chuàng)需要優(yōu)質(zhì),這個(gè)問(wèn)題人人都知道。但是編創(chuàng)還需要“率先”,卻少有人理解。于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而言,“率先”是頗具深意的。其第一效果顯現(xiàn)為物理性的鮮明:“率先”的編創(chuàng),就是創(chuàng)造一片沒(méi)有先例的“荒原”,作品一旦誕生,就將比對(duì)出編創(chuàng)的物理性的鮮明,并由此吸引眼球。其第二效果顯現(xiàn)為精神性的鮮明:“率先”編創(chuàng)產(chǎn)生的物理性鮮明不是目的,目的是“文以載道”,以物理性的鮮明承載精神性的鮮明—或者率先揭示社會(huì)的問(wèn)題,或者率先張揚(yáng)社會(huì)的美好,其揭示和張揚(yáng),因?yàn)椤奥氏取倍r明,因?yàn)轷r明而有力量,這才是“率先”編創(chuàng)的終極目的。所以,“率先”編創(chuàng)的價(jià)值,就是敢于吃螃蟹的先鋒性。其“率先”的是“一呼百應(yīng)”之一呼;是“揭竿而起”之揭竿;是開(kāi)風(fēng)氣之先河,領(lǐng)風(fēng)騷之獨(dú)特。“率先”更如春天盛開(kāi)的第一朵花,冬天飄落的第一片雪。豈止于花和雪,更是由花和雪揭示了春天和冬天的來(lái)臨。“率先”也往往因?yàn)榻沂玖耸聦?shí)的真相,體現(xiàn)出“率先”編創(chuàng)的核心價(jià)值。
“率先”編創(chuàng)的反向是“滯后”編創(chuàng)。“滯后”編創(chuàng)一樣頗具深意:其第一效果是物理性的非鮮明—因?yàn)椤奥氏取本巹?chuàng)已經(jīng)一片“紅海”,滯后于此,干了也是白干,根本就看不見(jiàn);其第二效果也是精神性的非鮮明—相似于春天最后盛開(kāi)的花和冬天最后飄落的雪,盡管也是花和雪,但是其原本可能揭示的春天和冬天的來(lái)臨的價(jià)值,卻因?yàn)椤奥氏取本巹?chuàng)已經(jīng)搶占了先機(jī)而喪失殆盡。
進(jìn)而,“滯后”編創(chuàng)還有“異化”:“異化”為利益的孵化器。“率先”編創(chuàng)往往存在風(fēng)險(xiǎn),因?yàn)榇嬖陲L(fēng)險(xiǎn)所以先鋒,因?yàn)橄蠕h所以有價(jià)值。但是,“率先”編創(chuàng)一旦被社會(huì)接受和肯定,原本的風(fēng)險(xiǎn)就“異化”為安全,甚至“異化”為政治正確。這時(shí),其“異化”往往就招致“滯后”編創(chuàng)的發(fā)生,原因就是冀望以其獲利。但是,以其獲利卻一樣有風(fēng)險(xiǎn):第一就是非鮮明;第二就是獲利的動(dòng)機(jī)清晰可見(jiàn)。
第二,“天生麗質(zhì)難自棄”。
舞蹈演員都愛(ài)跳舞,尤其是優(yōu)秀的舞蹈演員,并由跳舞的登峰造極而可能產(chǎn)生幻象:似乎無(wú)所不能,并延展至編舞。所以近年來(lái),優(yōu)秀的舞蹈演員大都開(kāi)始編舞。但是大多的編舞行為卻表現(xiàn)著無(wú)法掩飾的跳舞的動(dòng)機(jī):張揚(yáng)極好的身體條件和能力。
由此引出了兩個(gè)詞語(yǔ):“作品時(shí)間”和“肌肉時(shí)間”。當(dāng)舞蹈作品的時(shí)間符合舞蹈作品的表意,就是“作品時(shí)間”;當(dāng)舞蹈作品的時(shí)間不符合舞蹈作品的表意,且又受制于人體的運(yùn)動(dòng),并以人體運(yùn)動(dòng)的展示而設(shè)定時(shí)間,就是“肌肉時(shí)間”。“肌肉時(shí)間”和“作品時(shí)間”的區(qū)別就是時(shí)間的不同選擇—自然選擇或自主選擇。
自然選擇:自然選擇的就是“肌肉時(shí)間”。其選擇基于完成動(dòng)作的能力,能力主要表現(xiàn)為肌肉展示的能力。所以,其時(shí)間也被稱(chēng)為“肌肉時(shí)間”。
自主選擇:自主選擇的就是“作品時(shí)間”。其選擇基于作品需要的時(shí)間。作品需要的時(shí)間不會(huì)顧及肌肉的能力,只會(huì)顧及作品的效果,即表意作品的效果。所以,其時(shí)間就是“作品時(shí)間”。
難道選擇“肌肉時(shí)間”就不能編創(chuàng)出好的舞蹈作品嗎?當(dāng)然可以,但是必須有所兼顧:其一,如果身體條件和能力極好,可以適應(yīng)所有舞蹈作品需要的時(shí)間,那“就放手一搏”;其二,如果身體條件和能力不好,那就需要慎重選擇與其適應(yīng)的舞蹈作品。總之,就舞蹈編創(chuàng)而言,肌肉能力一定服從于作品的需要。
此次有兩個(gè)舞蹈明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個(gè)是張振國(guó),一個(gè)是石強(qiáng)。他們都是身懷舞蹈絕技、一身優(yōu)質(zhì)“疙瘩肉”的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國(guó)防大學(xué)軍事文化學(xué)院2016級(jí)畢業(yè)生。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yàn)橛袣v史的比對(duì):2016年筆者教過(guò)他們編舞課。時(shí)隔5年,首先是石強(qiáng)讓人眼前一亮,原因是他與5年前有了很大差別:他終于知道以柔性的力道舞蹈了。盡管他的舞蹈編創(chuàng)還是限于“肌肉時(shí)間”,但是其力量的改變卻讓人欣喜,因?yàn)檫@一改變十分困難:看似是身體的改變,實(shí)則是觀念的改變。改變的困難,唯有天長(zhǎng)日久地不滿足于自己的現(xiàn)狀,并死命“修煉”才能達(dá)成。其實(shí),這批學(xué)生在近年的舞蹈之中,大都還是當(dāng)年的樣子,也就是說(shuō),大都還在“啃老”于當(dāng)年的“一招鮮”。唯有石強(qiáng)的變化明顯,盡管其變化的結(jié)果不見(jiàn)得能入圍或者獲獎(jiǎng),但比入圍和獲獎(jiǎng)重要,因?yàn)榧皶r(shí)厭倦自己的“光輝”過(guò)往,這正是藝術(shù)家不斷前進(jìn)的重要?jiǎng)右颉?/p>
張振國(guó)這小子就厲害了。其厲害之處是竟在極好的身體舞動(dòng)之中糅進(jìn)了作品的感覺(jué)。什么是作品的感覺(jué)?就是作品的表達(dá)。也就是說(shuō),張振國(guó)把自己極好的舞蹈身體和能力出讓給了作品需要的表達(dá)。他的舞蹈既是一個(gè)男舞者的獨(dú)舞,也是出色的舞蹈身體和能力的展示。作品設(shè)定在一種身體背轉(zhuǎn)、永不正面面向觀眾的形式之上,讓人不禁贊嘆他頭腦的聰明與思維的獨(dú)特。這個(gè)形式看似簡(jiǎn)單,實(shí)則困難,相似于哥倫布的“立雞蛋”,能與不能之間就是觀念。其不轉(zhuǎn)身的形式以及堅(jiān)守也是同理:看似是形式,實(shí)則也是觀念。深諳舞蹈編創(chuàng)之“作品為大”的觀念,這才使他“出讓”了自己極好的舞蹈身體能力給舞蹈作品,并以舞蹈作品的力量而勝出為藝術(shù)家。
四、無(wú)關(guān)舞蹈種類(lèi)的感動(dòng)
有一種舞蹈就是讓人感動(dòng)。它們看上去不那么先鋒,但就是透著一股精氣神。這樣的作品讓人一眼就能看個(gè)底兒掉,即“隊(duì)伍”不行,“隊(duì)伍”不上檔次。但是作品的表演卻相當(dāng)過(guò)硬:有的整齊劃一,有的“參差不齊”,但配合和完成的專(zhuān)業(yè)度極高。尤其厲害的是其“整齊劃一”和“參差不齊”,竟還透著一股子精氣神:不計(jì)弱小、相信美好、努力認(rèn)真、昂揚(yáng)向上。面對(duì)這動(dòng)人的精氣神,一瞬間,是什么種類(lèi)的舞蹈,是什么人跳的舞蹈都不重要了,就感覺(jué)這是最好的舞蹈。其好在另辟蹊徑:不是種種先鋒之好,而是信仰之好。
每每看到這樣的作品,就會(huì)聯(lián)想到作品后面的人,即編創(chuàng)和排練這個(gè)作品的人。由舞蹈編創(chuàng)多年的實(shí)踐而知,其作品如果有風(fēng)骨,其風(fēng)骨就源于編創(chuàng)者和排練者本人,正是其人的風(fēng)骨傳達(dá)至舞者和作品,使得舞者和作品有風(fēng)骨。進(jìn)而,因?yàn)榫巹?chuàng)者的“風(fēng)骨”,也才可能“死命”地排練。其“死命”不是有意為之,而是無(wú)意為之:被心中的風(fēng)骨牽制,并以“死命”地排練而呈現(xiàn)心中的風(fēng)骨。但是,這樣的人常被舞者詬病,因?yàn)樗麄兣啪毱饋?lái)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似乎既無(wú)膀胱也無(wú)胃,甚至干脆就拋棄了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人的正常屬性,原因就是其風(fēng)骨的召喚。
此次的“山東大學(xué)(威海)藝術(shù)學(xué)院”就是一例;以往所見(jiàn)的“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文華學(xué)院”也是一例。隊(duì)伍看上去都不上“檔次”:山東大學(xué)和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都是當(dāng)?shù)氐恼泼#际侵摹案吒粠洝保弧吧綎|大學(xué)(威海)藝術(shù)學(xué)院”和“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文華學(xué)院”都是當(dāng)?shù)貟炜棵5膶W(xué)校,著名的“矮窮丑”。但是,它們的作品卻有風(fēng)骨,其風(fēng)骨正是以過(guò)人的排練而呈現(xiàn)的。
每到一地進(jìn)行講座,筆者常被問(wèn)到的問(wèn)題就是如何應(yīng)對(duì)領(lǐng)導(dǎo)。言下之意,因?yàn)轭I(lǐng)導(dǎo)不行,所以自己才不行。但是“山東大學(xué)(威海)藝術(shù)學(xué)院”和“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文華學(xué)院”面對(duì)同樣的國(guó)情和政策,面對(duì)不盡如人意的生源和師資卻做得更好。其“更好”的法門(mén)應(yīng)該就是三條:第一是想做;第二是做;第三是有眼界地做。法門(mén)的動(dòng)因便是風(fēng)骨,從而自有信念、自有尊嚴(yán)、自有定力。
這是一篇關(guān)于舞蹈比賽和舞蹈編創(chuàng)的文章,最后卻說(shuō)到了排練,因?yàn)檎J(rèn)真排練才能呈現(xiàn)好的作品,才能呈現(xiàn)動(dòng)人的風(fēng)骨。好的作品除了有編創(chuàng)的機(jī)巧、豐富的形式和獨(dú)特的思維之外,有沒(méi)有傳達(dá)出風(fēng)骨才是核心。說(shuō)起風(fēng)骨,就聯(lián)想到了北京舞蹈學(xué)院的張羽軍和曾煥興兩位教師的“神奇”之處,但凡他們考試,課上的學(xué)生們就會(huì)突然改頭換面:突然就不見(jiàn)了“脂粉氣”……根源就是張羽軍和曾煥興兩位教師的信念和定力,經(jīng)年累月而修煉不斷—不給錢(qián)練,不評(píng)職稱(chēng)也練,不結(jié)婚沒(méi)孩子也練,有了老婆孩子也一起練,最終修得風(fēng)骨,并因其風(fēng)骨使人格影響了課堂。
舞蹈編創(chuàng)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編創(chuàng)出一個(gè)個(gè)舞蹈作品,還是由其作品傳達(dá)出風(fēng)骨?諸多有信念和定力的教師們并沒(méi)有編舞,只是教學(xué),但是其教學(xué)之所以優(yōu)秀,就是傳達(dá)出了風(fēng)骨,并以其風(fēng)骨影響了學(xué)生。其風(fēng)骨還有厲害的地方,就是看上去不講政治,實(shí)則卻講了最大的政治:做一個(gè)正直善良的人,做一個(gè)光明磊落的人,做一個(gè)剛正不阿的人,做一個(gè)無(wú)愧于心的人。其做人的核心就是樹(shù)人,并以其樹(shù)人而成就了舞蹈教育的最大政治。
但是可惜,中國(guó)舞蹈界一向重表演而輕編創(chuàng);或者重編創(chuàng)而輕傳達(dá),導(dǎo)致這一“風(fēng)骨”背后的價(jià)值被小覷,沒(méi)有機(jī)會(huì)以其價(jià)值而真正貢獻(xiàn)于中國(guó)的舞蹈教育。
——東西方現(xiàn)代舞藝術(shù)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