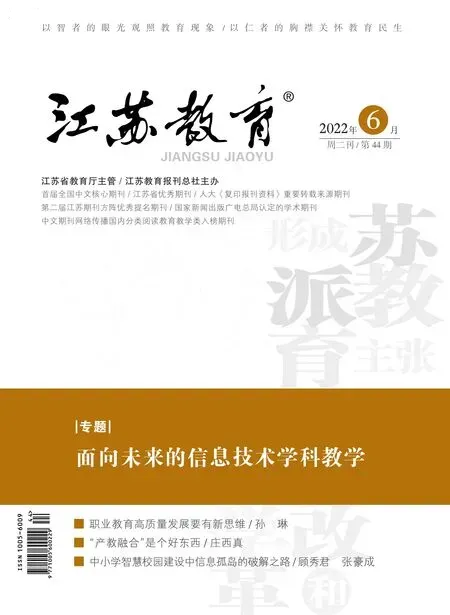“產(chǎn)教融合”是個好東西
莊西真
從事職業(yè)教育研究工作多年,我的體會是,在中國的各級各類教育中,職業(yè)教育是最“出力不討好”的教育。所謂“出力”,是指我們的職業(yè)院校在“為國育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明顯成效。這么多年來,中等職業(yè)學(xué)校、高職院校分別把中考成績、高考成績排在后面的學(xué)生,用3年時間(學(xué)習(xí)時間2.5年,還有0.5年是頂崗實習(xí))培養(yǎng)成具備一定職業(yè)知識、職業(yè)技能和職業(yè)道德的畢業(yè)生,這些畢業(yè)生在各行各業(yè)的崗位上工作,或生產(chǎn)產(chǎn)品,或提供服務(wù),其中有些還成長為技術(shù)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國工匠,支撐了我國經(jīng)濟(jì)尤其是實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所謂“不討好”,就是職業(yè)教育的成績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rèn)可,社會上某些人對職業(yè)教育的誤解、曲解、錯解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生源質(zhì)量差、在校學(xué)習(xí)時間短、畢業(yè)水平要求高、外部環(huán)境支持弱的情況下,職業(yè)院校的辦學(xué)可以說是步履維艱。
好在這幾年,國家決策層面重視,連續(xù)出臺助推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政策。更為關(guān)鍵的是有一大批愛崗敬業(yè)、孜孜以求的職業(yè)院校校長、教師,立足于國家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大局和學(xué)生職業(yè)生涯長遠(yuǎn)發(fā)展,明知不易為而為之,千方百計改革教育教學(xué)方式,提高教育教學(xué)質(zhì)量,盡其所能地幫助職校生在學(xué)校里學(xué)有所知、練有所能、行有所依,走出校門后做一個合格的職業(yè)人。無錫汽車工程中等專業(yè)學(xué)校就是全國成千上萬所負(fù)重前行的職業(yè)院校中的一分子,它以產(chǎn)教“深度融合”、校企“全面合作”為切入點,改革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創(chuàng)新實踐,符合職業(yè)教育發(fā)展規(guī)律,符合技能人才成長規(guī)律,符合職業(yè)學(xué)校和15~18 歲這個年齡段職校生的實際,育人成效顯著,做法可圈可點。
一、精確理解產(chǎn)教融合的內(nèi)涵
作為一個概念,“產(chǎn)教融合”是近些年來的熱詞。2017 年12 月國務(wù)院辦公廳專門印發(fā)了《關(guān)于深化產(chǎn)教融合的若干意見》;2019 年10月,國家發(fā)改委、教育部等6 部門又印發(fā)了《國家產(chǎn)教融合建設(shè)試點實施方案》,產(chǎn)教融合受重視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作為一種實踐,產(chǎn)教融合并無新意,在現(xiàn)代國家中,高等教育和職業(yè)教育(甚至基礎(chǔ)教育)發(fā)展的規(guī)模、層次、類型及其內(nèi)部的專業(yè)設(shè)置、課程框架、教學(xué)方式、實習(xí)實訓(xùn)、設(shè)施設(shè)備等都與所在國家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和所處階段息息相關(guān)。產(chǎn)教融合是常態(tài),不融合才是怪事。區(qū)別不在于產(chǎn)教是否融合,而在于融合的方式、內(nèi)容、深淺各異。
理解產(chǎn)教融合,應(yīng)該從分析產(chǎn)教不融合開始,先有分然后才有合。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分工、分化的社會,不同行業(yè)、不同產(chǎn)業(yè)、不同組織、不同群體、不同的人各自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情、有獨立性,彼此之間又相互支撐、有依賴性。有分化才有融合,產(chǎn)教融合是現(xiàn)代社會分工背景下,物質(zhì)生產(chǎn)(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比如汽車產(chǎn)業(yè)、新能源汽車行業(yè))這種人類經(jīng)濟(jì)活動和教化育人(教育系統(tǒng),比如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普通教育等)這種人類社會活動之間互動、交流和合作的狀態(tài)。分工是產(chǎn)教融合的前提,分工導(dǎo)致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和教育系統(tǒng)具備不同的屬性和功能。比如,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以生利為目的,教育系統(tǒng)是以育人為目的,一個是掙錢的,一個是花錢的。又比如,從我國管理體制的角度看,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中的國有企業(yè)屬于國資委管理,教育系統(tǒng)的公辦職業(yè)學(xué)校屬于教育行政部門管轄,兩者“雞犬之聲相聞,往來交流不多”。互補(你有我沒有但是我需要,我有你沒有但是你需要)是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基礎(chǔ),雙贏是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動力,這一點要搞清楚,正所謂“沒有三分利、誰起早五更”。
二、精準(zhǔn)分析產(chǎn)教雙方的交匯點
職業(yè)學(xué)校培養(yǎng)具備一技之長的職業(yè)人,不能沒有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但是產(chǎn)教畢竟是在兩條道上跑的車,不同之處遠(yuǎn)遠(yuǎn)大于相同之處,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融合呢?前面提到產(chǎn)教融合建立在產(chǎn)教、校企雙方互利共贏的基礎(chǔ)之上,就是要找到產(chǎn)教、校企雙方目標(biāo)的交匯點、利益的共同點。交匯點、共同點就是產(chǎn)教融合的切入點、著力點。從無錫汽車工程中等專業(yè)學(xué)校產(chǎn)教深度融合的實踐來看,主要有3 個這樣的交匯點。
第一,技術(shù)工人的企業(yè)需求和學(xué)校供給是產(chǎn)教融合的交匯點。技術(shù)技能人才的供給包括數(shù)量和結(jié)構(gòu)兩個層面。理想狀態(tài)是行業(yè)企業(yè)需要多少人才,職業(yè)學(xué)校就培養(yǎng)多少人才;企業(yè)需要什么樣的人才,職業(yè)學(xué)校就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但是現(xiàn)實中這種理想狀態(tài)很難出現(xiàn),因為人才需求的數(shù)量處于動態(tài)變化之中,人才的年齡、學(xué)歷、性別、能力等結(jié)構(gòu)層面的供需更為復(fù)雜,如果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和教育系統(tǒng)間沒有相應(yīng)的溝通和反饋機制,兩者只會“各行其道”,出現(xiàn)所謂的結(jié)構(gòu)性失業(yè)的問題。產(chǎn)教、校企雙方通過建立信息渠道和合作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企業(yè)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樣的人的交匯點,這是產(chǎn)教融合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職業(yè)教育產(chǎn)教融合一定是圍繞人才培養(yǎng)展開的。
第二,操作技能的企業(yè)實習(xí)和學(xué)校練習(xí)是產(chǎn)教融合的交匯點。職業(yè)學(xué)校培養(yǎng)的學(xué)生畢業(yè)后要到企業(yè)去,在生產(chǎn)服務(wù)一線崗位上工作,這些崗位對從業(yè)人員最核心的要求是掌握在基本原理基礎(chǔ)上的操作技能,要熟悉設(shè)施設(shè)備,熟知生產(chǎn)工藝,“來即能用”。這就給職業(yè)學(xué)校出了個難題,職業(yè)學(xué)校是教育機構(gòu),企業(yè)是生產(chǎn)機構(gòu),學(xué)校的教學(xué)不可能完全和生產(chǎn)過程對接。再加上職業(yè)學(xué)校囿于條件,訓(xùn)練學(xué)生操作技能的設(shè)施設(shè)備不可能經(jīng)常更換,只能用老設(shè)備練新技能。產(chǎn)教融合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學(xué)生在職業(yè)學(xué)校里練習(xí)基本的操作技能和工藝流程,到企業(yè)生產(chǎn)崗位上熟習(xí)真實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和生產(chǎn)流程,這樣對職業(yè)學(xué)校的技能學(xué)習(xí)是一個效果檢驗,也是一個熟練程度的強化。
第三,教學(xué)資源的校企轉(zhuǎn)換與統(tǒng)籌利用是產(chǎn)教融合的交匯點。職業(yè)學(xué)校的辦學(xué)需要校舍、經(jīng)費、設(shè)施、師資等教學(xué)資源,這些資源從哪里來?公辦學(xué)校幾乎全靠政府的財政撥款,但總是顯得捉襟見肘,不敷使用。學(xué)校就要另辟蹊徑,眼睛盯住行業(yè)企業(yè)。好在與職業(yè)學(xué)校主干專業(yè)聯(lián)系密切的行業(yè)企業(yè)都有比較豐富的諸如企業(yè)文化、生產(chǎn)工藝、生產(chǎn)設(shè)施設(shè)備、具有生產(chǎn)實踐經(jīng)驗的技工、各種各樣的制度文本等資源,這些資源經(jīng)過轉(zhuǎn)換(比如經(jīng)過從企業(yè)車間到學(xué)校教室的空間轉(zhuǎn)換、從崗位要求到課程教材的內(nèi)容轉(zhuǎn)換、從人作用于物的生產(chǎn)到人影響人的教學(xué)方式轉(zhuǎn)換、從生產(chǎn)場景熟練技工到校園環(huán)境指導(dǎo)教師的角色轉(zhuǎn)換等等)后可以成為職業(yè)學(xué)校的教學(xué)資源,助力職業(yè)學(xué)校培養(yǎng)出企業(yè)用得上的員工。同樣的道理,經(jīng)過多年辦學(xué)積累的教育教學(xué)資源經(jīng)過轉(zhuǎn)換后也能被企業(yè)利用,助力企業(yè)培訓(xùn)員工、改造工藝、提高效率、增加收益。
三、精心開展產(chǎn)教融合的實踐
職業(yè)學(xué)校以技能人才培養(yǎng)為核心、以操作技能的熟練為重點、以校內(nèi)外資源的統(tǒng)籌為基礎(chǔ),千方百計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這其中離不開產(chǎn)教的深度融合。職業(yè)學(xué)校要把產(chǎn)教融合這件好事辦好絕非易事,從一些做得比較好的職業(yè)院校的實踐來看,須強化以下四個措施。
一是發(fā)揮行業(yè)協(xié)會產(chǎn)教融合的橋梁作用,為企業(yè)提供產(chǎn)學(xué)研融合的信息。政府和行業(yè)協(xié)會不僅僅只是人才需求創(chuàng)造方和經(jīng)費、設(shè)施設(shè)備供給方,更為重要的是應(yīng)該發(fā)揮其自身制定規(guī)則的作用。政府和行業(yè)協(xié)會既能在國內(nèi)外接觸到職業(yè)院校、科研院所,又能接觸到各類企業(yè),可以說是各種信息、資源的集散地。政府和行業(yè)協(xié)會就要在產(chǎn)教之間起到橋梁與紐帶的作用,建立專門機構(gòu)、區(qū)域范圍內(nèi)的數(shù)據(jù)庫、信息交流平臺,服務(wù)于有意為企業(yè)提供新技術(shù)、新工藝、新產(chǎn)品、員工培訓(xùn)的職業(yè)院校,也服務(wù)于對上述新技術(shù)、新產(chǎn)品、新工藝、員工培訓(xùn)有需求且愿意與職業(yè)院校合作的企業(yè),為它們牽線搭橋,讓產(chǎn)教雙方真正互動起來。
二是建立和運營適合的產(chǎn)教融合載體。職業(yè)院校可以和行業(yè)企業(yè)圍繞具體的目的,根據(jù)各自的實際情況,形成松散式的合作(如技術(shù)服務(wù)項目合作)、名義上的合作(成立校中廠、廠中校),以及實體上的融合(成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產(chǎn)業(yè)學(xué)院、企業(yè)學(xué)院、訂單班等)。事實證明,產(chǎn)教融合做得好,必須要有一個能夠被賦予獨立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實體做支撐,這個獨立實體的意義在于形成同時遵循職業(yè)教育和產(chǎn)業(yè)行業(yè)雙重邏輯的運行機制,從而在規(guī)避合規(guī)風(fēng)險的同時,盡可能地放大產(chǎn)教融合的優(yōu)勢。有條件的學(xué)校和企業(yè),應(yīng)該通過新建、改造、合建等方式,盡可能地?fù)碛歇毩⑦\行的產(chǎn)教融合實體。比如無錫汽車工程中等專業(yè)學(xué)校與相關(guān)行業(yè)企業(yè)共建了無錫東方汽車產(chǎn)業(yè)學(xué)院、蘇州清研智能網(wǎng)聯(lián)汽車產(chǎn)業(yè)學(xué)院、京東物流智能供應(yīng)鏈產(chǎn)業(yè)學(xué)院、無錫市汽車職教集團(tuán)等產(chǎn)教融合載體。
三是系統(tǒng)設(shè)計職校生的生涯發(fā)展體系。產(chǎn)教融合背景下的職校生生涯發(fā)展路徑,應(yīng)將企業(yè)作為重要一元,使以企業(yè)為主體的生產(chǎn)元素貫穿職校生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的全過程。從學(xué)校方面來看,人才培養(yǎng)模式、課程體系、教學(xué)體系等的設(shè)計應(yīng)由企業(yè)全程參與。“現(xiàn)代學(xué)徒制”“校企模塊化課程體系”“學(xué)校與工作場所的交叉學(xué)習(xí)”等都是職校生生涯發(fā)展路徑產(chǎn)教融合設(shè)計的體現(xiàn)。學(xué)生在職業(yè)學(xué)校與工作場所的空間轉(zhuǎn)換中,從一個“小白”逐漸轉(zhuǎn)變?yōu)榫哂谢韭殬I(yè)能力的準(zhǔn)員工。系統(tǒng)設(shè)計基于產(chǎn)教融合的職校生培養(yǎng)方案和職業(yè)生涯發(fā)展體系是職業(yè)學(xué)校和企業(yè)共同的任務(wù),做到“項目共建、課程共定、師資共通、人才共育、成效共評”,不僅有利于職業(yè)學(xué)校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企業(yè)技術(shù)技能人才隊伍的建設(shè),最終體現(xiàn)為企業(yè)效益的提升和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
四是優(yōu)化和完善產(chǎn)教融合的制度環(huán)境。產(chǎn)教融合歸根結(jié)底要學(xué)校和政府、行業(yè)協(xié)會、企業(yè)合作的創(chuàng)新,良好的制度環(huán)境很重要。這不僅需要政府一系列的“松綁”“讓利”政策,也需要職業(yè)學(xué)校了解每一個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對象,考慮每個合作方的特殊性,有針對性地劃定制度創(chuàng)新的空間和邊界,創(chuàng)造性地和企業(yè)開展在人才培養(yǎng)各方面的合作。職業(yè)院校和企業(yè)應(yīng)該發(fā)揮產(chǎn)教融合主體的制度創(chuàng)新功能,在合規(guī)的前提下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約束制度的突破。目前很多職業(yè)院校都有比較好的制度創(chuàng)新案例,如確保企業(yè)高質(zhì)量參與產(chǎn)教融合的“產(chǎn)教融合保證金”“聯(lián)合招生和培養(yǎng)、一體化育人”“校企黨建聯(lián)盟”制度,成立校企混合所有的托管公司等。相信來自職業(yè)學(xué)校的制度創(chuàng)新,能夠為未來的產(chǎn)教融合提供更有借鑒意義的解決方案。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十全十美的職業(yè)學(xué)校產(chǎn)教融合育人模式,正因如此,也就給所有想在產(chǎn)教融合育人實踐方面有所作為的職業(yè)學(xué)校提供了無限的創(chuàng)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