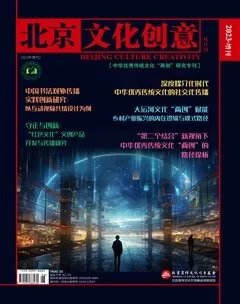“第二個結合”新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路徑探析
楊佳欣 陳燕
摘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凝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氣節和民族風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中華傳統文化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保證,也是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兩個結合”是黨帶領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形成的規律性認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偉大成功的“重要法寶”。本文以“第二個結合”為視角探討了“第二個結合”的價值意蘊以及“第二個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契合關系,并從系統分析法的角度出發,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與發展開放性為導向,探討了在“第二個結合”新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第二個結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一、“第二個結合”的價值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①此論斷闡明了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并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的未來道路指明了方向,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法和規律的新認識,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探索。“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深遠意義:“第二個結合”是“第一個結合”理論延伸的必然結果、是夯實中國式現代化文化根基的內在機理,并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高度。
當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新的風險和挑戰,也對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須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進一步結合,將馬克思主義深深鑄牢在中國大地上,才能用中國式理論、思維和智慧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淬煉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歷史,凝聚了獨一無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活”的靈魂,而馬克思主義以其科學性、實踐性、人民性和發展開放性的鮮明特征占據著真理與道義的制高點,因此,只有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進一步使馬克思主義扎根于中國大地,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出新的果實。
二、“第二個結合”賦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理與路”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匯聚成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鑄就了中華民族鮮明的民族精神,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影響和重要意義,“兩個結合”的提出,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精辟論斷,深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理論基礎,并為其明晰了發展方向、創新了實踐路徑。
(一)理:深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理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傳承弘揚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源頭活水。”①此論斷為我們指明了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馬克思主義之“根”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脈”的關系。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辯證統一的,它們都是創新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方法,但側重點不同:創造性轉化在于“改”,即對那些在當代仍有借鑒意義的內容及其舊的表達形式加以改造;創新性發展在于“新”,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注入新時代的活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可以進一步理解“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深刻內涵。②首先,辯證否定觀的實質是揚棄,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所例證的那樣:“按園藝家的技藝去處理種子和種子長出的植物,那么我們得到的這個否定之否定的結果,不僅是更多的種子,而且是品質改良了的、能開出更美麗花朵的種子,這個過程的每一次重復,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升了這種完善化。”③我們可以將傳統文化看作“種子”,于中華5000多年文化歷史中生長、開花、結果,是各個歷史朝代的產物,匯集著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統治階級的思想,而中華民族經歷了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傳統文化中必然會有一些維護封建統治舊道德、舊禮教的思想觀念,對此,我們必須像“園藝家”一樣對這些舊觀念進行剔除和改造,才能讓傳統文化開出“更美麗的花”。
(二)路: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對外傳播話語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④國際關系和局勢復雜,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隨著互聯網和融媒體技術的發展,西方國家滲透其意識形態的方式更加隱秘、形式更加多樣、內容更加立體,這就迫切需要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表達方式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受眾本位原則是新聞傳播的根本原則,即在對外傳播中既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要以受眾為主,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言,就是要增強國際受眾的自主性,能夠真正撥動國際受眾的心弦,讓國際受眾聽得懂中華傳統文化的故事,愿意接受中國文化,主動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兩創”時要在遵循外語表達方式,不僅要提煉中國元素和中國標識,更要被國際社會更好的理解與接受,這就需要找準中華傳統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連接點、話語共同點和情感共鳴點。馬克思主義就其發源地而言,發源于十九世紀的西歐,以其真理性和科學性為人類揭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并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⑤轉變的道路,其致力于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個性解放的目標是人類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目標,具有超越世界民族特殊性的全球視野和人文關懷,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依托馬克思主義可以增強其世界影響力,并擴大其受眾范圍。同時,馬克思主義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深厚的學理支撐。例如,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使得西方國家感到“不安”,西方更是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對此,除了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以外,還必須通過理論權威合理闡釋中國和平崛起模式。中華傳統文化崇尚“和為貴”“和而不同”“兼愛非攻”的理念,在民族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對外侵略和殖民主義。自新中國成立來,我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與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相契合,馬克思、恩格斯構建了與資產階級殖民擴張截然不同的國際關系,并指出:“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及“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擁護和平”,這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和平理念給予科學理論的支撐,并且將政治性與學理性相統一,創新了中華傳統文化“兩創”的話語內容供給。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產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體系是新時代話語體系的核心,中華民族歷來講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天下一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體系生成的中國基因,而“共同體”則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將“真正的共同體”與“冒充的共同體”“虛假的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等概念相區分,并指出,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體系”將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與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思想相結合,詮釋了中國“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的美好設想和偉大構想。
三、“第二個結合”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實現路徑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諸多方面有著天然的契合點和相通之處,并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一)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科學價值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其科學性在于它是以事實為依據、以規律為對象,以實踐為檢驗標準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當前,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沒有變,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背景沒有變,人們對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的追求沒有變,這說明,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認識把握當今世界變化趨勢,依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因此,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科學價值是傳統文化永葆生機活力的前提。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5000年發展歷程中無數中華兒女集體智慧的結晶,具有豐富的科學價值。首先,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樸素辯證法的思想。辯證法是西方哲學專有名詞,西方哲學史上公認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然而我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老子所著《道德經》已蘊藏了古代樸素辯證法的思想。老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萬事萬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有與無、難與易、長與短、高與下、美與惡等都是相互比較而存在的,如果沒有一方則沒有另一方,并且矛盾雙方可以相互轉化,如《道德經》中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中還蘊含著質量互變的辯證關系原理。第六十三章提出:“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天下的難事,一定從簡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從微細的部分開端,即沒有量的積累就無法促成質的變化。其次,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無神論”的思想。無神論奠定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石,是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堅守的原則,儒家學派代表人之一的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東漢時期思想家提出“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譯為人死后不能變成鬼,沒有知覺,不能害人。用什么來驗證這一點呢?用萬物來驗證它。人是物,人以外的萬物也是物。由此可見,中華傳統文化具有豐富的科學價值,我們要堅持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對于傳統文化中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具有科學性的內容繼續保持和發揚;對傳統文化中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內容,自覺加以改造或剔除。因此,進一步挖掘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的科學元素,將其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重大意義。
(二)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兩創”導向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三大工人運動”標志著無產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歷史舞臺,馬克思恩格斯在親身參與工人斗爭實踐、同時吸收時代思想精華的基礎上,完成了被譽為共產黨人“圣經”的《共產黨宣言》,指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一個每個人自由發展的聯合體”。追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的指引,一代又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在實踐中孜孜探求人類幸福的真諦,因此,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須深刻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而我國西周時期(公元前十世紀)的《尚書·周書·泰誓》中記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意為只有天地能哺育出世態萬物,只有人擁有世間萬物中的靈氣之體,《禮記·禮運》中記載:“人者,天地之心也”,古代醫學認為心臟居人體中央,主思慮情識,為五臟之主宰,而人是天地的心臟,即為天地的主宰,對人的價值作了高度的肯定。春秋時代的政治家管仲在《管子·霸言》中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孟子》中記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都體現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相契合。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以大眾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展現出來,才能激發人民群眾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比如央視綜藝節目《典籍里的中國》,以文化節目與影視化相結合,并用當下喜聞樂見的“穿越”為表達形式,為觀眾們呈現出了古代與現代的時空對話,讓典籍中的文字“活”了起來,展現典籍中所蘊含的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再比如《我在故宮修文物》,以故宮內的普通工匠的工作為視角,映射出廣大工人階級們的內心世界和信仰,同時講述了他們對青銅器、宮廷鐘表、百寶鑲嵌、織繡、書畫的修復、臨摹和摹印時的感想,讓人民群眾近距離地“聆聽”到這些文物所蘊含的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回響。因此,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理念,創新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表達方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不會失去其價值。
(三)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實用性
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首要的、基本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最顯著的特征。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以三大工人運動為實踐基礎,科學地解答了“什么是資本主義、如何取代資本主義”“什么是共產主義、怎樣實現共產主義”重大時代課題,為人類社會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20世紀初,列寧以“十月革命”為實踐基礎,回答了“什么是帝國主義、如何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時代課題,指導和推動了俄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①在我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解答不同時代提出不同問題的過程。因此,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始終要以實踐為基礎,體現時代的要求。《易傳》中記載:“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生生”指生生不息,“易”為變化,詞句意思為萬事萬物都是生生不息,循環往復,革故鼎新的。“吐故納新”出自于《莊子·外篇·刻意》,指人呼吸時,吐出濁氣,吸進新鮮空氣,引申為揚棄舊的、不好的,吸收新的、好的。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萬事萬物在變化發展的觀點,我們要將其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相結合,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實用性。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于社會存在,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因此,要充分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濟效用。作為一個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國家,各個省市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符號,如代表陜西的文化符號——盛唐、兵馬俑、大雁塔、法門寺等;河南的文化符號——少林寺、《清明上河圖》、司母戊大方鼎等;山東的文化符號——孔孟之鄉等,這些文化符號不僅可以成為國內各地區相互交流的平臺,同時也是促進國際貿易和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可以打造能表現獨特文化符號的城市IP,并結合互聯網技術與大數據功能對其進行再創新、再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內容,推動這些有代表性的符號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持續發展。只有將傳統文化轉化成物質力量運用到社會生活中,文化才能不被時代淘汰。
(四)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開放性,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對外傳播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始終站在時代前沿。”②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開放性是解答其永葆青春活力秘密的鑰匙,同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也在于其有“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特點。《國語·鄭語》中提道:“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諧,則萬物即可生長發育,但如果完全相同一致,則無法發展和繼續,“不同”是事物的本性和特質,是萬物得以生長繁衍、和諧共生的客觀規律。《禮記·中庸》中也提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尊重差異性是推動世界發展的重要前提,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遵循,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深入挖掘以“和”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傳遞給全世界,為解決人類文明問題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增強國際話語權,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建設。具有影響力的對外傳播話語內容必須具有鮮明的政治導向、深厚的學理支撐、通識的話語表述,要求我們要進一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念、思想理念等話語資源,從中提煉出新概念、新表述,增強話語內容的生動性、思想性,使其成為國際共識,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等表述中,蘊含了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志同道合”“大同世界”等思想。當前,由于西方長期以來對國際話語傳播媒介的霸權,導致我國對外傳播經常處于“傳而不通”的狀態,網絡新媒體的發展為我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多元化發展的契機,要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自媒體等新型傳播方式構建多元化傳播語境,重視利用視覺圖像向世界傳達中國傳統文化。同時,構建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的話語體系,其主體不僅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刻的認識,同時需要擁有熟練運用外語轉譯的能力,因此,復合型的對外話語轉化和傳播人才是構建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的話語體系的重要資源。因此,只有始終堅持文化的對外開放,使其走向世界,才能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載體增強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從而進一步推動文化強國的建設。
四、結語
“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經驗總結,是黨帶領人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勝利的“最大法寶”,促進了新時代黨和人民新的思想解放。“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雙向互動,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注入了科學理論的新鮮血液,增強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科學性,并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立足于人民、服務于人民,推動人民群眾的文化自覺性和自信心,從而為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近年來,西方國家通過互聯網、報刊影視、學術交流等手段,對我國進行“普世價值”的滲透,歪曲、捏造中國歷史、詆毀中華傳統文化,企圖消弭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地位,“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為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適用性提供了思想指引,并進一步鞏固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因此,我們要始終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指導方針,鑄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基,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動力,推動中華文明走向新的輝煌。
基金項目:陜西理工大學科研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化觀視域下漢中紅色文化建設研究(209010483)
作者:
楊佳欣,陜西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文化建設
陳燕,陜西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
(責任編輯:李欣)
Absrt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bond that solidifies the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 spirit, integrity and style.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eternal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whole Party and society to enhance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s a regular understanding formed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is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the “doubl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analysis, it is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popular, practical and open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 selection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econd combination”.
Key Word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