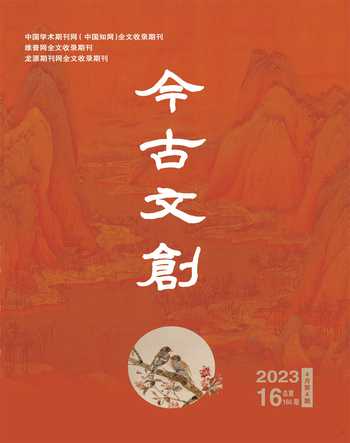淺論王陽明“知行合一” 思想
丁玉龍
【摘要】 在中國哲學史的發展歷程中,“知”與“行”的關系問題一直備受矚目,從先秦諸子到宋明理學家都對這一問題保持了關注,直到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才為中國哲學發展史“知”“行”關系的探討畫上了終止符。本文旨在梳理“知行合一”的思想脈絡,并從理論依據、具體內涵及其實踐能力三個方面來對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價值進行粗略地探討和分析。
【關鍵詞】知行合一;王陽明;實踐能力;理論價值
【中圖分類號】B248?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6-006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19
一、“知”“行”關系的歷史演進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①,在承載中國哲學史的早期典籍《尚書》中就曾提到“知”與“行”的關系問題,但是由于早期中國社會獨特的社會環境,人們無法對于“知”和“行”的關系進行進一步地深入探討和分析,因此對于“知”“行”關系的理解和認識只能停留在比較淺薄的層面,所以可以看到在這一時期人們只是簡單地從二者難易程度來進行闡述,但是,這確實也是中國古人的智慧,不可否認的是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一“起點”才有了之后人們對于“知”“行”關系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探討,或者換句話講,我們也可以認為“知易行難”的這一理解是最早對“知”與“行”概念比對的思想結論。
到了先秦諸子時期,《論語》中有記載關于“知”“行”關系的看法:“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②“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③從《論語》中的部分對“知”“行”關系的闡述可以看到,不同于早期中國社會中對于“知”“行”關系地簡單看待,孔子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對該關系進行解釋的:孔子將“知”與“行”聯系起來從同一層面來進行說明,在他看來,獲得知識的途徑是學習,而學習的目的就是“知”,但“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也就是說在孔子那里,“知”和“行”的地位并不是同一的,也不是對等的,從《論語》某些句章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行”依舊是要重于“知”的,而也正是自此開始,中國思想家們對于“知”與“行”關系問題的探討就一直沒有停歇。
等到中國哲學史發展到宋明理學時期,二程和朱熹又對“知行關系問題”的闡述增添了許多解釋和說明:例如在程頤看來,“知”的地位是遠高于“行”的,也就是說“知”決定“行”,而“行”是由“知”所決定、派生的,“知”可以分為“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行”之所以能行,是建立在“知”的基礎之上的,倘若沒有“知”的存在,那“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換句話講,只有先知才能行得,只要知存在,自然見于行,反之,自然也并不存在知而不能行的現象,如果真出現了知之而不能行,那必然是因為沒有獲得“真知”,而且“知得淺”;不同于二程對于知行關系的認識角度,朱熹則是從“理”的角度來進行闡述,在朱熹那里,“知”是對自己心中固有“理”的認識,而“行”則是按照這個“理”來發生的行動,在對二者關系認識的層面上,朱熹認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知行相須,限于篇幅原因,這里不再展開,朱熹更是提出了“知行并進”“知行并列”等觀點,但卻始終沒有給人具體的方法去理解二者。一直到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才算是為在中國社會討論了幾千年的“知”“行”關系問題畫上了終止符。
二、王陽明對“知”“行”關系的總結
面對“知”與“行”關系的問題,王陽明并沒有簡單地按照前人的路子走,而是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新路,在合理吸收了程朱對“知行關系”問題的看法和理解,王陽明認為不應該簡單地把“知”和“行”割裂開來看待,而是應當“知行合一”,唯有“知行合一”才能夠合理地認識“知行關系”問題,正確地對待“知”與“行”。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論依據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程朱對于“知行關系問題”的看法和理解,是對以往哲學家關于“知”“行”關系認識的揚棄,也是中國哲學史上“知行關系”探討的一大突破。在論述“知”與“行”關系問題的時候,王陽明認為程朱理學的“格物說”是不符合道理的,一定要讓人們踐行“知行合一”的思想觀念。而為什么要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王陽明自己也有所闡述:“此需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兩件。固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心中。此是我立言宗旨。”④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大背景之下,王陽明是為了讓人們摒除掉受環境影響所產生的知行分離,因此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觀點,他的這一學說同朱熹與陸九淵在本質上來說就是不同的,對于朱陸二者,他們的主張都是知先行后,而王陽明卻反對將知行分作兩截,認為知行本一、當“求理于吾心”,因此這也就催生出其另一個重要的哲學思想——“致良知”。湖北大學的周海春教授就認為想要理解“知行合一”就必須從“致良知”出發:“對于還原‘知行合一思想的本來面貌和進一步地補充,首要出發點就應當從王陽明‘致良知的思想出發。”⑤筆者部分認同此觀點,但不同意將二者緊密結合的看法,“致良知”只能作為了解“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不能將二者完全混同起來,二者應當屬于相互補充、相互佐證的關系。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具體內涵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也就是說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可分,在王陽明看來,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認知和實踐是互不分開的,二者相互連接,相輔相成;另一方面王陽明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知是行的前提,借用其“良知說”來進行說明就是行為要在“致良知”的基礎上,而不是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借口。當我們對其本來面目進行考究時可以看到,王陽明對于“知”與“行”的理解也是獨特的,中國人民大學黃仕坤教授認為“就知行本體而言,‘知為發端,事物初顯時便能有‘知;‘行則不僅包括人的意念,同時還包含著人的身形,又因為意念、身形與萬物的存在都是同一的,因而‘行也就是良知的開顯。”“所謂‘知行實則唯一,二者不過是‘致良知功夫的兩個方面。”⑥而關于“知行合一”的具體內涵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吳光研究員也有所表述:“概而言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主要有三點:第一,知與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所謂‘過程是指理解和實踐的過程。其次,‘知和‘行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知是行的起點,其指導行,實際上真正的知不僅能夠行,而且已經在行了;行是知的最終結果,真正真誠的行在過程中已經有了自己自覺和感性的知……第三,在知與行的過程中‘行的根本目的是徹底克服‘不善的念,進而實現至高無上的善,這本質上是一個道德修養和實踐的過程,究其根本,王陽明將‘知稱為‘我良知的天理,而他所謂的‘行則是‘將我良知的天理應用于萬物的道德實踐。”⑦通過對兩位學者的研究比較起來,可以看出無論是將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分成三部分來看,還是兩部分來看,其基本內涵都是不變的,也就是說“知”與“行”的統一是不變的,在王陽明這里,“知”和“行”就是不能割裂的一部分,它們是相互依存,且不可被分割的。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實踐能力
東南大學陸永勝教授認為“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作為兩種不同的創新形式來看,從理論上,其為‘知行合一思想的實踐能力提供了一種理論的效力范圍;而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其又立足于具體現實的時代生活之中。從這兩個角度的意義上來看,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實踐能力就體現在其有限度的實踐價值上,換句話講,其實踐能力的具體表現則是既為心與事的統一,又是思想視域同勢的統一。”⑧在這個基礎上,想要深入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能力首先就要清楚其“心即理”的哲學思想及“良知說”的內容,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再對其加以說明,因此就簡要談一下其實踐能力。在知行關系問題上,朱熹基于理先氣后的哲學觀,強調知先重行,并提出知行互發并進,王陽明因此痛砭時弊:“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于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于無豪杰之士者為之倡焉耳。”⑨王陽明強調“真行”,即是要保證行與知在德行意義與價值取向上的絕對一致性,這可體現為兩個面向:一為意識層面的依知而行的自自然然,絕無將迎意必之間隔;一為實踐層面的德性與德行的統一,即“行為的合法性”與“意向的道德性”的一致。從中可以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究其根本而言一方面是為了傳播儒家思想在道德層面的理想實踐,另一方面確實是為了矯正當時的社會學子對“知”“行”側重看待的不一致,以保證學子們可以“知”“行”并重而不忽視其中一方,因此“知行合一”思想的實踐可以說在當時是極其重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社會的學術氛圍,讓求學者、治學者不僅僅著眼于“知”或者“行”其中的一部分,而是將二者結合起來,并重地看待,進而催生出一大批優秀的學者,不是僅僅專注于理論或者實踐的“跛腳”學生。
三、王陽明“知行關系”思想的現代價值
對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有了初步認識和理解之后,立足于現當代,把握和剖析其思想的理論價值是必要的,如何吸收其思想精髓、加速社會文化發展是要點。
第一點,深入理解和踐行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有助于增強文化自信。首先,加強創新性發展,這也就要求既要在認識理解傳統文化的同時合理吸收其精華,又要立足于現代社會做出不同于往常的新詮釋。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前進的方向,其注重經世致用、致知力行的方式方法對于社會道德建設等具有明顯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凈化社會風氣、加強社會公德、個人品德,并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其次,對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進行合理地揚棄,忽略掉其主觀唯心主義部分,關注其面對社會現實問題提出的合理性觀點“知行相互統一”,然后對其進行創造性發展,擴充“知”和“行”的內涵,以求增強文化自信。
第二點,王陽明關于“知行關系”的思考有助于加強人們的思想道德建設,提高個人反思能力。例如在學習先進思想的過程中,可以借用王陽明對“知行關系”的思考結論,做到“知行合一”,一方面對所學思想的內容和內涵進行理解和認識,同時還要在內化于心的基礎上外化于行,將其通過自己的行動展現出來,換言之,要做到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正如同王陽明對“知行關系”的認識,“未有知而不行”,因此只是單純地去學習了解所學思想的內容、知識,但是卻不去實地行動、實踐,這樣是無法真正了解這一思想內涵的,只有在認識理解其內容的基礎上去切實實踐,才能夠真正地把握、提升道德修為,強化實踐能力,讓自身在“知”與“行”合一的基礎上推動其更高層次地內化于心。同理,在日常生活和學習的過程中,也可以借助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時常對自身進行反思,檢查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不是紙上談兵、夸夸其談,在日常生活中聯系“知行合一”,從“知”中去實踐“行”,再反過來從“行”中去思考“知”,最后使“知行合一”,在不斷的反思中進步和發展。
“知行合一”的思想是王陽明對“知行關系”問題的一大總結和對歷史研究該問題的集大成,至此,中國哲學史關于“知行關系”的理解正式走向“知行合一”的途徑,無論王夫之還是后世明清思想家對于知行問題的研究都沒有脫離“知行合一”的范疇,但是我們也要注意的是,對該思想進行批判地繼承而不是全盤吸收是必要且必須的。
四、總結
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在當今時代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此外,其中也包括不符合現實社會的弊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基于當時的歷史現狀而做出的關于“知行關系”的解答和闡釋,這是具有特殊的歷史語境存在的,而隨著這一語境在當代社會的轉變,“知行合一”其原初的理論效率和實踐能力范圍就難免要轉化為當代才能夠被合理地吸收和接納,要看到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其中具有的局限性,正確地把握其思想內涵,才能夠對于創新和發展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產生有利影響,只有對其思想進行合理地揚棄之后再進行吸收,如此方能真正學習理解,并以身體力行之。
注釋:
①源自《尚書·說命中》:“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②楊伯俊譯注:《論語·季氏篇》,《論語譯注》(簡體字本),中華書局2006年版。
③楊伯俊譯注:《論語·學而篇》,《論語譯注》(簡體字本),中華書局2006年版。
④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周海春、韓曉龍:《論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109-117+176頁。
⑥黃仕坤:《王陽明“知行合一”新論——基于心物一體存在視域的分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18-25頁。
⑦吳光:《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內涵及其現實意義》,《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29-32頁。
⑧陸永勝:《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效力與實踐能力》,《江淮論壇》2020年第6期,第106-113+197頁。
⑨王陽明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參考文獻:
[1]鐘俊平.“知行合一”思想的歷史嬗變[J].學理論,2018,(08):67-68.
[2]鄭澤綿.從朱熹的“誠意”難題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重構從理學到心學的哲學史敘事[J].哲學動態,2021,(02):92-101.
[3]高正樂.王陽明“知行合一”命題的內涵與局限[J].中國哲學史,2020,(06):89-97.
[4]何心.“知行合一”思想的內涵及現實意義[J].學理論,2020,(06):53-54.
[5]董平.王陽明哲學的實踐本質——以“知行合一”為中心[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6(01):14-20.
[6]張新民.天命與人生的互貫互通及其實踐取向——儒家“天人合一”觀與“知行合一”說發微[J].天府新論,2018,(03):31-53.
[7]張黎.淺析王陽明知行思想的價值啟示[J].西部學刊,2021,(10):151-154.
[8]高海波.王陽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新詮[J].國際儒學(中英文),2022,2(03):79-92+170.
[9]丁為祥.“踐行”還是“踐形”?——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根據、先驅及其判準[J].哲學動態,2020,(01):4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