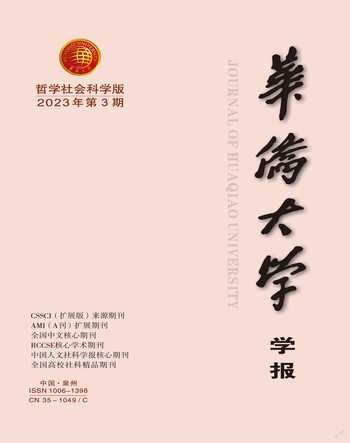“村改居”居民文化認同的消解與重塑
楊繪榮 劉佳佳
摘要:“村改居”社區作為由傳統農村向現代城市過渡的特殊樣態,因其“亦城亦鄉”的獨特性而為學界所廣泛關注。在“村改居”社區這一過渡型社會形態中,受文化延續性、穩定性的影響,社區意義空間、交往空間、權力空間的重構遠滯后于生存空間(物質空間)樣態的變化。從空間變革的視角審視“村改居”社區居民的文化認同現狀,可以發現社區居民面臨著文化記憶斷裂、文化歸屬感消解、社區情結轉化艱澀、主體意識薄弱等多重瓶頸。有鑒于此,基于物質空間、意義空間、交往空間和權力空間之界分,重塑公共景觀這一空間之“基”、深挖符號資源、完善社會關系網絡、推行網格化管理等則是紓解“村改居”社區居民文化認同困境的創新路徑。
關鍵詞:“村改居”社區;多元空間;文化認同
作者簡介:楊繪榮,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文化、認同理論(E-mail:yang_ivy@qqcom; 山西 太原 030006)。劉佳佳,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政治儀式中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國家認同的強化研究”(22YJC710082);山西省科技戰略研究專項課題“山西省‘村改居社區治理中的文化認同問題研究”(202104031402032);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創新項目“鄉村振興中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重塑問題研究”(2022Y054)
中圖分類號:C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3-0034-11
文化建設與文化認同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內容,向來為黨中央所重視。如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由此,文化建設尤其是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近些年來,在城市化過程中,“撤村并居”作為推動個體獲得現代性的有益探索,它在促進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也引發了“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認同危機,很顯然,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所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此外,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空間社會學逐漸成為顯學,空間的社會性意義也隨之得到重視,但現階段有關“村改居”社區治理的研究大多將空間視為承載“村改居”社區治理的純粹物質性場所,極大地遮蔽了空間所蘊含的秩序變遷、關系重組等豐富內涵及聚合社會資本、建構社區共同體等深刻價值,而空間的這些內涵與價值皆是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認同關涉居民的價值認知與主觀能動性,系“村改居”社區治理的內驅力所在,加之它與空間關系甚密,因而基于空間之維建構“村改居”社區居民的文化認同,是促進“村改居”社區善治和社區共同體建設的創新舉措。
一空間建構文化認同的意涵與理路
現代化進程中空間格局不斷嬗變,空間的多義性得到了更為深刻的闡釋。“村改居”社區作為特殊的社區類型,關涉空間樣態的變革、社區關系及社區秩序的重組。文化認同作為“村改居”社區治理的內在動力,是理解“村改居”社區治理的重要維度。實際上,空間與文化認同具有極為緊密的邏輯契合性,前者不斷為后者注入社區記憶、文化符號、社會資本等資源,并經由物質、意義、交往、權力等具體空間向度對居民文化認同進行多維建構。
(一)多元空間論
空間是理解城市發展的重要視角及濃縮、聚焦現代性問題的符碼與經驗現實之表征,法國政治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反對將其視為靜態存在,而是將它視為“社會的產物”及“社會秩序的空間化”,這種空間化關涉人類社會關系的建構與重組。在此基礎上,列斐伏爾進一步闡釋了有關空間生產的三元辯證法思想——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與表征空間,它作為根植于馬克思、黑格爾及尼采哲學的三重唱,具有極強的哲學思辨意味。大致而言,空間實踐指向物質領域,是一種自然的、物質性的客觀存在;空間表征指向抽象精神領域,通常與社會生產關系及由此所強加的“秩序”相關聯;表征空間則指向社會領域,乃系一種象征性的空間形態。實際上,三類空間辯證統一于社會生產與發展,列斐伏爾通過再繪馬克思的商品生產模式闡釋三類空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其中,空間實踐是商品生產及社會關系的基礎與載體,為進一步實現商品交換及社會關系存續,需運用表征空間內的各類符號表象,而生產關系的諸多表象之中又內含權力關系。由此可見,社會生產與發展有賴于空間實踐之基礎、表征空間之介質,而空間表征蘊含的權力性思維則貫穿于社會生產與發展的全過程。具體到“村改居”社區中,空間實踐與“村改居”社區的物質自然空間(物質空間)相對應,如農田、祠堂;空間表征與福柯的“權力空間”相類似,意指“村改居”社區中由政府、社區管理人員與社區居民互動形成的一種權力空間;表征空間與“村改居”社區中經由社區慶典、節日紀念等儀式活動所構成的場景(意義空間)相契合。基于空間三元論思想,加之吸收借鑒其他學者有關空間的界分以及社會學界關于“社會關系”的闡釋(涉及到交往空間或關系網絡),大致可從物質空間、意義空間、交往空間、權力空間四個向度理解“村改居”社區的生產發展問題。
正如前文所述,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與表征空間系三位一體的辯證統一關系,亦即物質空間、意義空間、權力空間三者辯證統一于“村改居”社區的生產與發展過程,而所謂“交往空間”即由社會關系所構筑的空間,它與各類空間關聯密切,它們共同構成理解“村改居”居民行為邏輯(包括居民文化認同)的空間面向。居民作為“村改居”社區的行動主體,其思維觀念、行動邏輯深受物質空間、意義空間之影響,并由此生成新的社會關系與權力關系,為“村改居”社區治理帶來新的挑戰。當前,撤村并居過程中空間的急遽轉變與居民文化變遷的滯后性形成張力,致使“村改居”社區常表現為“城市的軀殼、農村的精神內核”,居民文化認同日漸消解,這極大阻滯著“村改居”社區善治。因此,為有效實現社區善治,需審思居民的文化認同問題,充分發揮文化認同在“村改居”社區治理中的內在動力價值。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空間是文化的表征,而文化認同作為個體對共同文化的確認,亦可放諸空間之中加以理解。
(二)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作為最深層次的認同,意指個體或群體將某一文化系統(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內化于自身心理與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進行認知評價、規范行為的過程,這種文化系統涵括各類物化形式與精神指向,而與之相關的文化認同能夠促使某些文化符號得以運用、共有的文化理念得到秉承、個體與群體間關系得到確認、共同思維模式及行為規范得以生成與遵循。在文化建設日益重要的當下,文化認同與“村改居”社區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它能夠喚醒居民主體意識、聚合社會資本,助推“村改居”社區共同體之培育,因而在研究“村改居”社區治理時需關照社區的文化轉型及居民的文化認同問題。縱觀文化認同的兩大主流闡釋,它既是個體對自我知覺與自我定義的反映,又是個體與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皆深受空間之影響。蔣福明在闡釋“村改居”社區文化轉型問題時,將社區文化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與制度文化四個面向。有關“村改居”文化認同的研究亦可從這四個向度加以探討,同時基于“空間”之維可以發現,物質文化作為最易被感知的物質實體,它與物質空間最為接近;精神文化關涉居民精神風貌、共同信仰,意義空間與之關聯甚密;行為文化涵括居民的生計生活模式及人際交往,可將其放諸交往空間展開分析;至于制度文化,權力制約監督的合理性與有效性是現代政治學的核心命題,為保障權力的正常運行需訴諸制度化的程序和規則,可見權力與制度關聯密切,因而可將制度文化放置于權力空間加以考察。簡言之,文化認同可具化為物質、精神、行為與制度文化四個面向的認同,而物質、意義、交往、權力這幾個基本空間類型大致與之契合,故而可將空間作為審思文化認同建構的新理路。
(三)空間建構文化認同的邏輯理路
美國傳播學學者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立基于文化屬性,將認同視為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在他看來認同是建構起來的,而文化認同系最深層的認同所在,同樣經由建構而來。基于空間視角審思文化認同的建構過程,可從文化認同的結構要素——認知、情感與行為加以闡釋。其中,物質空間因其記憶載體屬性,主要作用于認知層面;意義空間與交往空間憑借豐富的象征性資源(文化符號)與行動資源(社會資本)主要在情感層面發揮作用;權力空間關涉權力與權利的博弈,深刻影響著居民的主體意識與行為。最終,經由四個向度空間的共同作用,居民的文化認同逐漸強化。
具體來講,首先,物質空間充當文化記憶的載體,能夠經由文化記憶的生產與再生產影響個體的認知,最終作用于個體的文化認同。從記憶附屬論的視角來審視記憶與認知的關系,可以發現記憶是認知的來源與重要組成部分,它為個體認知提供了經驗材料和歷史積淀。物質空間的選址、規模、形態等物質性材料能夠為文化記憶的生成提供敘事語境與背景,當個體進入特定的物質空間場域后,便會依循物質空間的建筑樣態以及附著其中的道具引導建構相應的文化記憶,并憑借已有的文化記憶對所屬共同體進行認知與想象以建構自身對共同體的文化認同。
其次,意義空間與交往空間涵括眾多文化符號與社會資本,它們為個體情感的凝聚、文化認同的生成與強化匯聚了大量的文化性材料——象征性資源與行動資源。一方面,文化符號的互動與聯變特別是作為符號聚合體的儀式展演,能夠促進個體間的意義共享與情感交流。在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看來,人類是“感情的動物”,而諸如此類的儀式互動會產生高度積極的情感能量,最終形成群體團結。另一方面,人是社會的動物,自出生伊始便不可避免地要與他人交往,在人類交往空間中潛藏著大量的“社會資本”,如信任、互惠等,它們能夠促使個體生成更深層次的情感聯結,潛移默化地強化其文化認同。
最后,權力空間中充斥著認知與意識形態,暗含服從之邏輯。權力與權利的博弈向來為學界所樂道,眾所周知,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絕對的腐敗乃系民心所背,是文化認同解構的“催命符”。為此,黨和國家不斷探索出“人民當家做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性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個體權利、主體意識之覺醒。毋庸置疑的是,這一意識的覺醒與強化,促使個體與所在群體形成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激勵他們為維系共同體的穩定發展而自覺行動,從而使得文化認同真正落地生根。
二“村改居”居民文化認同消解之表征:基于空間表象的多維詮釋
個體無往不生活在空間之中,個體行動也與其所處空間緊密相連,并隨著社會空間形態的變遷而變遷,從而為個體的行動邏輯鐫刻了“空間性”之烙印。作為由傳統鄉村向現代城市轉型的過渡形式,“村改居”社區一改原有村落的建筑樣貌、空間布局,面對這種空間樣態的巨變,居民的生產生活實踐、個體交往互動、社區參與意識等皆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并且體現出深刻的空間性。
(一)物質空間:文化景觀變遷,居民文化記憶斷裂
“村改居”社區作為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同樣未能幸免于城市同質化帶來的樓宇林立,而自然性、人文性等鄉村地域特色景觀的消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村改居”居民鄉愁無處寄托的尷尬境況。正如有學者所言,當人們通過地標建筑、歷史遺產等文化景觀記住城市之時,文化記憶便成為人、場所與城市之間的樞紐所在,成為三者交流的共同“語言”。不言而喻,“村改居”社區的建成伴隨著空間布局及公共景觀的變遷,而這種由相對開放的村落和農田向封閉性強的樓宇和綠地的轉變過程便內含著居民文化記憶的斷裂。這種斷裂對個體的影響是綿長而深遠的,它可能致使個體產生一種失落感,即便處于新的生存空間,但因文化記憶斷裂帶來的持續性影響,使得“村改居”居民仍以一種“客居他鄉”的心理感知這一新的空間,難以對該空間產生身份歸屬與文化認同。
村改居作為一種被動城市化現象,在這一進程中,“時間性”效應會導致村民文化認同的轉換遠遠滯后于物質的變遷,而“空間性”效應則會帶來強烈的相對剝奪感,阻礙村民文化認同系統的轉換。在鄉土社會中,土地作為融匯于村民血脈基因中的重要元素,始終是村民維持生計的主要來源和經濟之本。彼時,村落的景觀面貌除卻自由開放式的住宅便是集中連片的農田,農民傍土而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生產生活與時令節氣緊密相連。如“清明前后,種瓜點豆”“清明種瓜,立夏開花”等,種種農事諺語皆點明了農田景觀的季節性以及村民與土地緊密的依附關系。然而隨著“村改居”社區的建成,居民被迫失去了早已融于自身血脈基因中的土地,一改其傍地而生的生活習性與生計模式。此時居民心理層面的身份認知與角色轉換遠遠滯后于客觀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由此產生茫然、不適等不良心理狀態以及病理性焦慮。譬如,福建省龍文區藍田街道在對“村改居”社區的農村“小菜園”進行集中整治時,發現類似的菜園多達412個,這一案例從側面反映出“村改居”居民在撤村并居后其生活習慣與物質空間的不相適應性。可見,“村改居”居民這種相對穩定而持久的鄉土情結容易致使其身份認知混亂,亦不利于他們建構對社區文化的認同。
(二)意義空間:符號表征漸逝,居民社區情結轉化艱澀
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曾指出,人與其是理性的動物,不如說是符號的動物,人是創造符號,并以此創造文化的動物。從中,符號對人類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在傳統鄉村中,通常建有表征特殊意涵的公共空間。例如,祠堂通過村志和一些儀式等方式展現居民的同根同源性,用以充當血緣關系的符號表征;村委會作為村集體事務的處理中心及村莊治理的權威所在,通過選址于村莊中心,實現了地點的中心性與權威的崇高性之融合。再有,景觀等符號是建構地方認同的重要途徑,文化認同作為共同體認同的重要一極,與景觀符號有著深層的關聯。社區景觀符號的存在并與之互動能夠強化居民文化認同,而景觀符號的消失則會導致社區居民文化認同式微。例如,有學者在對寧夏W村撤村并居過程中的寺坊進行長期田野調查后發現,在W村“村改居”過程中寺坊走向分化,其所承載的宗教文化也走向斷裂,居民在自由、自主愈增的同時,也面臨著社區歸屬感與認同感衰落的危機。可見經由撤村并居的系列舉措,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景觀符號走向沉沒,伴隨而來的便是社區文化認同因象征性資源的流失而趨向式微。
另外,儀式作為一種助推群體團結、提升群體凝聚力的符號集合,它能夠經由儀式展演呈現一種瞬間共有的現實,在這種“公共在場”的現實情境與場域氛圍內,它得以發揮情感動員與意義共享的功效,助推居民認同感、歸屬感的生成。然而,隨著“村改居”社區的建成,諸如祠堂、戲臺、廟宇等村民們賴以舉行祭祀典禮、進行各類儀式展演的場所因與現代文明理念沖突而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則是健身場所、活動中心、公共綠地等現代化公共活動場地的建成,雖然它們能夠發揮促進居民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間平臺作用,但其獨特象征意義的匱乏使得社區居民難以形成更深層次的情感聯結與文化認同。此外,在由相對開放的傳統鄉村邁向封閉性較強的單元樓房的同時,村民為慶祝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彼此合作互動舉辦包粽子、做月餅等節日儀式活動,以及互相分享美食的共享儀式也因受限于顯性空間的阻隔趨向消減,這意味著一種富有人情味的、守望相助的“共同體”或將被拆散,居民的生活秩序也因此受到影響,他們對“村改居”社區的文化認同感、歸屬感等趨向下降。
(三)交往空間:社會資本下降,居民情感歸屬式微
從心理學視角來看,文化認同指涉個體對文化的歸屬感與內心承諾。文化歸屬感作為個體對其所在共同體的依戀、忠誠等情感傾向,對共同體的存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現階段,“村改居”社區作為傳統鄉村與現代城市的夾心層與過渡帶,居民的無根感加劇。其原因在于,傳統鄉村基于血緣、親緣建立起的社會關系網絡走向斷裂,加之“村改居”社區充當著流動人口的“蓄水池”,社區居民身份的異質性、復雜性給社區信任、互惠規范等的建立帶來諸多挑戰,致使“村改居”社區社會資本不斷流失,由此導致社會資本之凝聚、整合功能難以有效發揮,居民的社區文化歸屬感隨之弱化。
在言及傳統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時,費孝通提出宛若“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差序格局,用以形容以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為基礎,以自我為中心推及開來,伸縮自如、能收能放的人際關系格局。在撤村并居以前,村民多以務農為生,對土地的依賴性極強,安土重遷構成其重要的文化心理表征。由于祖祖輩輩皆扎根于此,累積而來的人際關系使得村民間的交往甚是密切,村落內部表現為典型的熟人社會。然而在“村改居”之后,社區固有的血緣、地緣關系遭到極大破壞甚至不復存在,居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更導致人們在人際交往中利益權重的上升。隨之而來的是,人倫“差序格局”轉向利益“差序格局”,維持居民交往的情感紐帶演變為工具型表演關系,社區交往空間也由親密化趨向疏離化,居民對社區文化的歸屬感亦因此不斷弱化。
此外,信任作為構成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在社會共同體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充當社會良性運轉的道德價值基石。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基于新功能主義角度,將信任界定為用以減少社會交往復雜性的機制。福山則立足于歷史終結處的人類處境,將信任視為促進經濟繁榮的文化基礎。帕特南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出發,指出社會共同體內部的信任范圍越普遍,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間的信任與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進而越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繁榮發展,而且合作本身也能帶來信任。由此觀之,信任發揮著簡化社會交往、降低社會交往成本、增強社區成員凝聚力等諸多功能。區別于傳統鄉村基于熟人關系、血緣關系建立起的社會信任,“村改居”社區的居民信任感的生成極具復雜性。一則,“村改居”社區居民處于一種被動安置狀態,居民對拆遷政策頗具微詞而相關部門未加以重視,后續補償條款的落實不到位致使居民對基層政府、居委會不信任,阻滯著居民對社區共同體的認同,如有學者在研究杭州某一“村改居”社區時指出,該社區在回遷時因選房規則相對不公及補償款未到位,致使居民最終做出了“集體討說法”的行為,毫無疑問這致使社區信任遭受極大流失,且不利于社區共同體的構筑。二則,“村改居”社區居民構成的復雜性以及居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刻板印象,如慣性地為外來人口貼上“愛惹事”“素質差”等負面標簽,這種居民間身份差異及偏見的存在同樣不利于相互信任感的建立,且亦使外來人員萌生一種不平等感知,消解著他們對于社區的歸屬感。
(四)權力空間:權力格局不平等,居民主體意識薄弱
福柯作為20世紀非常權威的理論學家,其有關權力、社會的論述總是充滿著空間性的寓意和洞見,他指出,社會并非僅有一種權力運作的單一體,而是彰顯著各有特性的不同權力間的并置、聯系、調和以及等級化,由此可見,社會實則是由不同權力所構成的一個群島。具體到“村改居”社區,毋庸置疑,社區工作者為居民提供了許多優質的服務,但這種服務通常是基于一種“改善”的邏輯和不平等的關系。他們習慣性地將居民視為被管理、被教育的對象,缺乏對居民因空間樣態急遽轉型所產生的迷惘、不適等心理狀態的感知與同情,只是一味基于極端現代主義的立場進行社區管理。這種過度追求現代文明理念而對傳統風俗嗤之以鼻的觀念,使得管理者與居民在諸如晾曬被子等日常行為范式方面存有沖突,即追求規范秩序的現代化觀念與享受自由安逸的傳統理念發生對抗,從而造成了居民對社區文化的認同危機。另外,在“村改居”社區中,居委會干部與社區工作者主要源于之前的村干部和村委會工作者,在他們繼續為“村改居”社區居民提供服務時,這種基于舊有的人情關系所形成的社區治理模式,可能會因缺乏公平、公正而產生不良影響,如深圳市寶安區在“村改居”后仍面臨著換屆選舉的“人情票”,小族、小姓的候選人無論能力多強、品質多好,皆難以當選,顯然這種有違公平的選舉會為后續社區治理帶來諸多弊端;同時,該社區存在新老居民“兩張皮”的問題,他們在政治、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享有不平等的權利,極易致使外來居民陷入一種感知上的不平等狀態,解構著他們對社區的文化認同。
三“村改居”居民文化認同重塑之空間策略
空間充任著承載定位功能、情感聯結及詮釋社區共同體價值意蘊的工具性媒介,經由內含其中的符號聯變與互動、場域氛圍的形成與感染以及對重大歷史時刻的情境化再現,可多面向地形塑“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認同。由是觀之,空間為強化“村改居”居民文化認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空間重構”作為一種在具體情境中展開的空間實踐,它通過采用公共景觀再造、呼喚部分傳統文化符號及儀式復歸、完善社會關系網絡、推行網格化管理等諸多策略,能夠有效消弭“村改居”居民在多個空間向度上的文化認同困境。
(一)物質空間:公共景觀再造,重構居民的文化記憶
從時間向度來看,居民因生存空間、交往空間的變遷而產生的迷惘不適等心理變化,可訴諸歷時性的社區記憶建構來得以慰藉。基于這一邏輯,我們可充分發掘空間建構社區文化記憶、最終重塑社區文化認同的功能價值。
在人類悠久的社會生活中,記憶始終是最為重要的權力資源之一,布迪厄在研究符號暴力時提及記憶的作用,他以黑人與白人的交談為例證,指出雙方交談時不單單是兩種集體記憶的交流,更是兩種權力的爭鋒。換言之,社會記憶既受制于權力,同時它本身也是一種權力,能夠在潛移默化之中作用于記憶客體,使之按照它的意愿記憶、思考或行動。因而,應充分挖掘物質空間在實現社區記憶在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指向意義,以契合社區治理主體的現實需要,促使“過去”契合“現在”的需要,利用社區文化記憶引導社區共同體意識,推動個體基于社區記憶框架展開回憶與思考,形成對社區共同體的體認與想象及自我在社區共同體中的坐標定位,從而強化其社區文化認同。
地理空間作為一種記憶生發場域,其被結構化和整理的地方,通常潛隱著特定的記憶。以上海市嘉定區陸巷社區為例,它是一個典型的“村改居”社區,鑒于該社區大多居民都是由附近鄉村搬遷而來,在社區現代風貌建設的同時鄉村記憶愈加失落。受鄉土情結的影響,居民將自己的鄉村記憶澆筑于有失美觀的“菜園”之中,這一種菜毀綠現象雖寄寓了居民的鄉愁與慣習,卻破壞了現代社區的整體美觀。本著留得住鄉愁和“堵不如疏”的原則,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在走訪后發現許多居民對于兒時家中圍墻邊的薔薇花情有獨鐘,便巧妙地將一處社區廢棄用地打造為薔薇花墻,并在此過程中積極鼓勵居民參與薔薇花的種植,由此居民的鄉村記憶得以存續,而閑置的公共用地也因充當鄉村文化記憶的載體,而為“村改居”社區共同體之構筑提供了記憶與認同的塑造點,繼而強化了“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認同。
(二)意義空間:深挖符號資源,構筑居民的社區情結
“村改居”社區作為一種由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文明城市轉化的過渡狀態,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在此交織,而各類符號、儀式作為承載、展現文化的載體,對社區共同體文化的存續與發展、社區情結的構筑具有重要的功能價值。如此一來,推動景觀符號的傳承,深挖儀式資源成為構筑社區情結、強化居民文化認同之意義空間的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祠堂、村志等符號作為社區共同體文化的載體,能夠為“村改居”居民文化認同的建構提供記憶融匯點,故而應對這類文化符號加以承繼。例如,福建省漳州市碧湖街道在“撤村并居”、開展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注重傳統建筑及歷史文脈的保留與承繼,而諸如蔡氏宗祠、萃英廟、古榕樹等歷史文化符號的存續,既構成了碧湖街道獨特的社區景觀,又使得原有的社區文化習俗得以延續。碧湖街道“村改居”社區居民進入宗祠、古廟后,在獨特的場域氛圍中經由圖騰、雕塑等各類符號的互動與聯變,實現了社區共同體記憶的喚醒與固化。此外,還可通過將古榕樹所在地打造成人工島嶼,使其成為見證社區變遷視覺形象上的“城市之眼”,使居民在人工島嶼休憩、觀賞古榕樹景觀之余得以追古撫今,感受歷史悠久的社區文化,不斷提升自身對社區文化的認同感。
其次,儀式作為一種指向性的文化表演活動,它體現著儀式組織者的意圖。因而,在“村改居”社區這一相對嶄新的社區樣態中,社區治理者應創新一些儀式活動,注重與外來人員的精神文化相融合,突出社區某些價值信仰,以重塑社區信仰,強化社區居民的文化認同。譬如,社區可以廣泛借鑒蘊含家庭和睦理念的由婆媳共同參與的舞被獅儀式活動、以和為貴的請長者“吃講茶”而對鄰里糾紛加以調節的行為儀式,等等。借由此類儀式的豐富與創新,不斷凸顯、固化尊老敬老、睦鄰友好等價值觀念,居民也因相關儀式展演而參與互動,實現了社區價值觀的內化和社區情感的凝聚,有助于促進自身鄉土情結向社區情結的轉變,強化對社區的文化認同。
最后,隨著信息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地方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儀式也在媒介場的作用下演變成一種新的儀式傳播類型——媒介儀式。在虛擬空間中,社區成員得以突破時空局限,通過微信、釘釘、微博等社交媒體參與到媒介儀式活動之中。于是,身處不同時空的居民經由微信的圈群化傳播而被連接起來,他們基于數字媒介進行儀式互動,實現了線上空間的“共同在場”。如在春節、中秋節等節日時令中,“村改居”社區居民可通過發送節日祝福、相關表情包等較為靈活便捷的形式實現媒介儀式活動的符碼式參與。同時,媒介儀式的出現也進一步凸顯了“村改居”社區的價值信仰,增強了居民間的情感聯結。例如,山東省西上虞社區在“村改居”30周年紀念日活動中,通過采取“快閃”形式生動弘揚了西上虞社區幾代人艱苦奮斗、眾志成城的干事創業精神,而這種實體空間的儀式展演經由媒介轉播,實現了居民在更廣泛時空范圍內的線上聚合。在這種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中,原戶籍居民與外來居民的身份差異得以消除;而且經由多模態視聽符號交織的媒介儀式傳播,居民能夠深刻感悟西上虞社區的價值信仰與社區精神,并通過觀看、點贊、評論、轉發等形式參與儀式互動,密切與其他居民的交流互動,加強彼此間的情感聯結,進而在更為宏大的“情緒場”與“感染域”中激發情感共鳴,強化他們對社區共同體的文化認同。因此,應當積極挖掘媒介儀式潛力,豐富媒介儀式活動,以促進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居民聚合,進而拓寬“村改居”社區儀式活動的氛圍場與感染域,在虛擬空間內強化個體與社區的情感聯結,增強“村改居”居民的情感歸屬與文化認同。
(三)交往空間:增厚社會資本,強化居民的情感歸屬
毫無疑問,由信任、網絡及互惠規范所構成的社會資本對整合社區文化資源、強化社區居民文化認同具有重要價值。然而“村改居”社區中關系網絡的松散、互惠規范的缺失及居民信任感的下降似乎成了不爭事實。正因如此,可通過重構社會信任、密切居民交往等方式,來增厚社會資本,強化社區居民的文化歸屬感。
就重構社會信任而言,首先,政府應建立健全反饋機制,在吸納民意基礎上,科學研判并有效落實“村改居”配套政策,這里,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區治理的相關經驗可以提供借鑒,該區政府通過探索清產核資摸清家底、制訂方案鎖定成員等方式保障了居民在“村改居”后的合法權益同時,為滿足居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雨城區政府還積極為共享書吧等社區文化娛樂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扶持。經由這些舉措,居民得以妥善安置,生產生活得到極大改觀,政府由此獲得了居民的信任,居民對社區共同體的認同感也隨之提升。其次,社區工作人員應通過調查走訪、民主座談、普及宣傳等渠道,及時掌握居民文化服務的需求傾向與需求變化,科學評估居民最為關注和亟需解決的社區文化難題,積極邀請居民共同參與到社區文化建設的議事決策中,以此增進社區居民對自身以及居委會的信任感,強化居民對社區共同體的認同。再次,物業管理人員應妥善處理、有效化解涉及文化建設的物業管理糾紛,以一種包容平等的態度對待居民在公共場所晾曬被子、種地等行為,積極配合社區工作人員,為其開拓晾曬被子、種植蔬菜等專門性場域,及時就社區居民的物業服務投訴予以反饋。長此以往,社區居民對物業管理人員的營利性及“不近人情”等歧見可以得到極大消解,會逐漸建立起對物業管理人員的信任,助推他們建構對社區共同體的文化認同。
就建構社會關系網絡而言,應當建立、健全密切社區關系網絡的組織載體與交往平臺。一方面,積極探索、組建形式多樣的社區文化娛樂組織,將有著不同興趣愛好的社區居民聚集起來,通過積極組織文化活動等形式密切社區居民間的交往,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同時,還應為社區文娛組織的發展及社區文化建設提供完備的制度保障與充足的資金支持,以促進其良性、長效發展。另一方面,重塑社區傳統、豐富社區文化活動,同樣不失為加強個體之間、個體與集體間的情感聯結,完善社會關系網絡的突破口。例如,內蒙古包頭市某社區巧妙地對傳統的“義倉”制度進行現代意義上的轉換,搭建起誠信友愛的“義倉義集”社區互助平臺。社區居民售賣自身閑置物品,將義賣所得捐于弱勢群體,經由這一方式,達成了助人自助之目的,也極大增進了個體間的情感聯結,這對于重塑居民之間內在關聯、完善社會關系網絡、強化“村改居”居民文化認同意義重大。
(四)權力空間:推行網格化管理,激發居民的主體意識
“村改居”社區是經由撤村并居演化而來的新型社區,它需要應對新的社區公共事務,然而,無論是政府主導下的“家長制”社區管理模式,還是社區工作人員基于改善的邏輯和不平等的關系而提供服務的模式,實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村改居”居民對社區的文化認同。在這種權力不平等的格局下,居民往往只能被動地服從,主體意識淡薄,對社區的文化認同感較低。對此,首先,應當厘清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的邊界,保障社區權益,規避行政色彩濃厚的管理模式對社區居民產生的不良影響。這就需要政府明晰自身的職能定位,專注于提供公共管理與服務,避免過多干涉致使居委會始終忙于行政事務而無暇顧及文化建設。政府還應將自治權歸于居委會,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做到指導而不越位,協作而不越界。就委托社區完成的政務性工作而言,政府也應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避免動用社區集體資產為政務性工作買單,保障社區共同體及其居民的合法權益。
其次,社區應當積極開展網格化治理。網格化管理,顧名思義是將社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并運用現代網絡信息技術構建管理平臺,將社區的樓宇、街道乃至居民都納入到可被觀測的監控平臺上,從而形成多元共治的精細化管理網絡。它與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通過將異常規訓轉化為普遍化監視,來促使權力運作更加便捷化、迅速化,從而有效改善權力運作的空間策略。在這一過程中,可大力吸納社區居民擔任網格管理人員或是樓長,以提升他們參與社區治理、文化建設的積極性。與此同時,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與文化建設,有利于消除居民和社區工作人員之間的不平等性及心理隔閡,促進社區居民與社區治理主體的關系聯結進一步加強。社區治理主體還可以充分發揮網格管理人員及樓長的樞紐中介作用,積極聽取他們的意見反饋,以完善相應的社區規章制度,進而有效推動社區文化建設,強化社區居民的文化認同。如此一來,居民在“村改居”治理的權力場域中便不再處于一種消極的失語現象,當他們的意見建議經由多元渠道得以妥善處理后,其社區參與的效能感隨之提升,主體意識與參與積極性亦將有所改觀,這種由“旁觀者”到“主人翁”的角色轉變同樣會帶來文化認同的強化。
結語
“撤村并居”作為中國獨特的城市化推進方式,毫無疑問,它在助推城鄉一體化建設、改善城鄉發展面貌、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這個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過程中,“村改居”社區相應地成為充斥著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等諸多矛盾元素的社會空間。加之在“村改居”社區治理過程中,社區治理人員大多仍以傳統的“硬治理”方式為主,缺乏有效的“軟治理”策略,致使社區居民雖然在人居環境、生活方式、戶籍身份等方面迅速向城市社區靠攏,但在文化價值層面卻未實現“同步性”,甚至呈現出明顯的文化墮距現象。社區認同作為“村改居”居民對社區的情感歸屬與心理認同,它是社區的向心力、凝聚力及社區發展的內驅力所在,文化認同作為社區認同的內核,更關涉著“村改居”社區的良性持續發展,因此探究“村改居”社區居民的文化認同問題具有獨特價值。結合空間生產理論,將“空間”視為社區治理與文化認同培育的策略裝置,并嘗試建構“物質空間—意義空間—交往空間—權力空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審思“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認同困境并探尋適宜解決之策,將文化認同的建構嵌套于空間分析框架之中,不僅在理論層面有助于挖掘空間本身的豐富內涵與功能價值,更是在現實層面有利于促進“村改居”社區居民文化認同的生成與固化。
Dispelling and Reshap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with a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Space
YANG Hui-rong, LIU Jia-jia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to modern cities, the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due to its uniqueness of “having both rural and urba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gnificance space,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power space in the community lags far behind the change of living space (material space)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of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s into urban residents”. Examining the status quo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changing villages into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hang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are faced with multiple bottlenecks, such as broken cultural memory, dissipation of cultural belongingness,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complex, and weak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material space, significant space,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power space, reshap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public landscape space, digging deeply into symbo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implementing grid management are innovative ways to relieve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s into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pluralistic space; cultural identity
【責任編輯:龔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