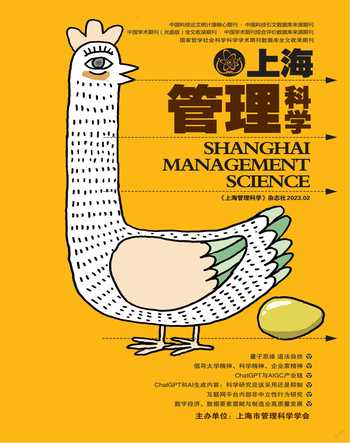倡導大學精神、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
陸雄文
摘 要: ??影響我們科創事業和國家前途的最大瓶頸是教育。人才培養自有其規律,每個孩子各有天性、各有天賦,因材施教是祖訓,培養創新人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教育界的迫切使命。我們必須倡導真正的大學精神、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這是國家社會走進新時代、進行現代性轉型的動力。
關鍵詞: ?大學精神;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
中圖分類號: ?C 93
文獻標志碼: ??A
Promoting University Spirits, Scientific Spirits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Speech Delivered on New Year Forum at ManagementSchool in Fudan University
LU Xiongwen
(Management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bottleneck which impacts Chinas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Talents cultivation has its own way. Each student is unique and endowed with individual gift. It is our ancestors preaching that educat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which is our urgent mission. We need to promote authentic university spirits, scientific sprits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ch serve as the momentum to drive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spirits; scientific spirits; entrepreneurship
今天我們邀請了各個領域的科學家、企業家等諸多大咖和四位新青年代表來同我們分享他們對科學、對事業、對人生的深刻洞見與體驗,相信大家都有知識上的收獲、眼界上的拓展,也相信大家能夠理解我們這個學院每年一度新年論壇為什么不只是聚焦于產業、商業和管理問題,而是延展開來,涵蓋當下這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需要共同關注與面對的時代主題。
過去的2022年,我們所見所聞、親身經歷都令人刻骨銘心、不可忘卻。在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中美博弈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之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迅速分化、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也在大范圍解構、重組,世界貿易增長乏力,VUCA時代更加VUCA,中國在越來越多科技領域遭遇西方圍剿。
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撲面而來,中國的科創熱潮方興未艾。我們學院在2020年啟動科創戰略,致力于以管理賦能科創、引領科創,以求助力中國的科創事業。大半個月前,我受上海市管理科學學會邀請以“管理與科創并舉”為主題做了一個演講。演講結束時,主持人王方華教授點評,他提出一個問題:“雄文院長提出‘無科創、無未來,那是否有科創就有未來呢?” 我的回答是“NO!”
我說,無科創無未來,說明科創是未來的必要條件,但科創仍不是未來的充分條件,為什么呢?我認為我們要走向光明的未來,還要具備一系列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這些條件的不具備、不突破,在過去、在今天都抑制了這個社會的創新發展。
我今天講三個方面:
首先是理念滯后。
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應該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仍然令人困擾。這背后有兩個基本理論問題,第一,今天勞動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力勞動了,那么資本剝削勞動還成立嗎?在馬克思寫《資本論》的年代,資本剝削勞動是科學的論斷,但其內在的涵義是稀缺的貨幣資本剝削有大量供給、甚至供給有剩余的體力勞動。
今天已是科創時代,沒有貨幣資本的科學家以其知識產權作價1個億來融資,風險資本家投入1000萬現金入股,占10%的份額,創始人團隊占90%股權,如果科創失敗,VC資本如落花流水,那么這種情況下誰剝削了誰?如果科創成功,企業價值擴大100倍,那又是誰剝削了誰?是知識勞動剝削貨幣資本,還是貨幣資本剝削了科創企業家?我的回答是,稀缺的科技資本“剝削”了有大量供給、甚至供給有剩余的貨幣資本,這里的被剝削也是貨幣資本家心甘情愿的,所以我要打上引號。而這里的科技資本是不斷增值的資本,是科學技術人員活的勞動不斷創造的資本。我無意說資本剝削勞動的時代已經過去,因為我們現實當中還存在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但是勞動剝削資本的時代也已經正在到來,關鍵是怎么定義勞動和資本。
在今天這個時代,馬克思對資本和勞動的經典定義需要大大拓展和豐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按“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來進行分配”,這是一個重要的理念創新,哪個要素具有稀缺性、排他性、獨占性,哪個要素在生產與分配過程中就有優先性、主導性、控制性。我認為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
第二個理論問題是,私有資本是惡的嗎?資本家的傳統形象是唯利是圖、剝削工人、破壞環境、不正當競爭巧取豪奪,乃至組成利益集團操縱公器。今天的社會物質愈益豐富,法制愈益健全,勞動者保護、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反壟斷措施越來越有力,社會教育水平提升,文明程度提高,越來越多企業家承擔社會責任,回饋社會。當今ESG已日益成為全球商業世界的共識和行動。大多數私有資本家即使有所揮霍,其個人享受總是有限的,他們仍然重視家族傳承,如果他們培養的二代、三代也屬精英人才,則由他們經營的財富就有可能創造比社會平均更高的收益率,則是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他們經營效率低、報酬率低,他們的企業就會在競爭中失敗,要么破產,要么被兼并收購。今天的時代,越來越多私有資本家努力向善,先前有榮毅仁,現在有任正非、曹德旺。
在我們這個社會,我們要警惕的是資本與權力的結合,資本腐化權力、操縱權力,無論其所有制性質!所以我們要設立屏障,阻斷私有資本向公權力滲透的企圖和野心。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私有資本是有原罪的,隨著社會繁榮、文明進步,私有資本也在不斷進化,逐步融入文明進程。
其次,影響我們走向未來的是體制問題。
我舉兩個方面,首先是科研體制,我們的科研體制仍是僵化的、效率低下的。重視產出規模,不以產出質量為重。只講產出,不講投入,不評估投入產出比。研究導向仍然以發論文、評職稱、報獎項、升院士為主線,申報課題、評獎、競爭院士的進程仍然被錯綜復雜、厚實深入的關系網、人情網、交易網所籠罩。大量的資源浪費在申報、評獎過程中,浪費在課題的低水平重復研究中,浪費在儀器設備重復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費在許多不必要的出差和會議中。對于如何激發廣大科技人員、專家學者的創造潛能,缺乏研究和積極舉措,不敢在人力資本本身進行大力度投入。一些大學不能正確理解上面指示,對上唯唯諾諾,搞一刀切,把不應該關閉的、有利于跨學科交流合作、有利于科技成果轉化、有利于教授和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平臺企業、科技園統統關掉了事,關門大吉,讓廣大教授、專家在成果轉讓方面畏首畏尾、怕秋后算賬。
第二個方面,最近一年,資本市場,主要是一級市場遭遇霜降,相對有錢的基金主要是國資背景的基金,然而國資背景基金決策慢、程序復雜、附加條件多,不能響應科創企業融資與發展要求。資本運營應當是最市場化的,然而卻不能完全按市場規律、市場規則辦。這都是我們體制的問題。
最后,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影響我們科創事業和國家前途的最大瓶頸是教育。
我的同事和我在過去三年考察了上百家科創企業,我們發現其創始團隊、核心科技人員80%以上是從海外回來的,主要是美國,少部分是歐洲和日本,他們在海外有學習、研究、工作和創業的經歷,有些還參與科創企業創業或在行業領先企業中擔任研發部門負責人或事業部負責人。他們回國創業已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全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加以整合、加工利用,然后再創新,形成科創產品和服務。
今天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在理工領域停止和限制招收我們的留學生,限制和阻礙我們的學者訪問和交流。中國這一波科創浪潮五年,或許十年會達到頂峰,那十年后,我們自己的大學能培養出那時候能瞄準世界科研前沿的創新人才嗎?二十年后我們同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儲備和能力是更接近了還是差距更大了?我們的科研院所、高校沒有培養出拿諾貝爾獎的人才,一是因為我們的基礎積累不夠、水平不高,二是因為我們教育理念和體系落后。
大學不能造就創新人才主要源于我們的基礎教育沒有輸送大量有好奇心、探究心及初步專業興趣和素養的高中畢業生。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高中,孩子們完全拘泥于課本和課程考試,孩子們的創新思維、開放思維、質疑精神統統成為應試體制的累贅,他們很少人會按自己的天性去發展自己的個人興趣愛好,更不要說在一些專業領域去探究學習、積累知識。他們能考進復旦錄取分數最低的專業,也不愿意去同濟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建筑設計,他們能進金融專業就會放棄去中文專業追逐成為小說家的夢想。其實孩子們都是有天賦的,基礎教育的首要使命應該是去幫助孩子發現天賦、激發潛能,順其天性,給予培植提攜,如若有錯,還可以及時調整。
過去20年,我到訪過許多世界一流大學的一流實驗室,每個實驗室有十多個理工醫博士生,由導師帶著做實驗,中國博士生常占多數,有的占一半以上,但是在整個博士生團隊里面、群體當中排名第一、二的往往是美國本土博士生。問其導師,答曰這個孩子有天賦,他從小開始有興趣,在小學、中學階段就得到老師的扶持、培養,給開小灶、做專題,參加興趣討論班,日積月累,考上自己感興趣的大學專業,然后讀博士,慢慢地就會脫穎而出,成為有天賦的、有創新的人才。
小時候,我讀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深受觸動。一百八十多年前,文人畫家以曲斜疏散的梅花為美,隨即,“直則無姿”“正則無景”“密則無態”成為對梅花的評價標準。為了迎合這種審美偏好,種植梅樹的人不惜砍掉原本筆直端正的枝干、除去原本繁密的枝條,而故意培養旁枝曲干,以此來獲得高價售出的利潤。對著數百盆“病梅”,龔自珍默默垂淚,發誓一一解救之。“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他放任梅樹自由生長,砸掉為觀賞而設的盆子,把梅樹轉植到土地里,解開操縱其生長形態的束縛,以求還原梅花天然的形態。
人才培養也自有其規律,每個孩子各有天性、各有天賦,因材施教是祖訓,培養創新人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教育界的迫切使命。我們的高考體制一考定終身,要求全科優秀、均衡發展,不少搞教育的有的剪枝去葉,有的拔苗助長,以為如此是合理選拔和培養棟梁人才,渾不知自己已經成為“泯滅”孩子天性的劊子手、屠戮未來創新人才的劊子手。我們要救救孩子,否則我們來不及救我們的未來、救我們的國家,更救不了我們自己!
在我們這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地區之間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教育資源分布也不平衡,追求絕對公平既不現實也不必要。恢復高考以來,人為設計的高考配額從來沒有實現絕對公平,一刀切的入學抽簽,優秀校長、優秀教師輪換,也無助于資源配置公平,反而加劇了有限優質資源的錯配。
發展基礎教育,一要增加政府投入,尤其是對師資報酬和師資培養的投入;二要建立適應我們發展水平和狀況的教育使命和目標,要為孩子們建立基本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學習能力基礎,又要幫助孩子發現自己的天賦特長,培養興趣愛好,既使大多數孩子成為這個國家各個領域的合格勞動者,也使其基于自己的興趣特長和愛好,能發揮其潛能,實現其價值,他自己也能享受其過程。另一些孩子有機會進入大學,也是因為其天賦被發掘、被激發、被培養,從而在大學獲得深造和發展的機會。如此,這個國家才有可能成為源源不斷有創新人才支撐的創新國家。
剛才我主要回應了為什么有科創不一定有未來,因為邏輯上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要開創光明的未來, 我們在前提條件上就要改革創新,建立一系列有利的條件束,包括科創實踐,才有可能構成光明未來的充分條件。接下來我就想分享一個觀點,沒有對科學規律的尊重和對科學精神的弘揚就沒有科創的成功。
我清晰地記得,我的初中、高中時代的政治課,特別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和尊重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世界上任何運動都有其規律,自然規律、歷史規律、教育規律、科學規律。曾幾何時,我們很少談論規律了。
三年前,我與同事們講,大疫不過三年,很多人認為我太悲觀。二個月前,我在一個論壇上仍公開這么講,很多人仍不敢相信。其實我講的不是我科學研究的發現,而是人類歷史上無數次疫情演繹的規律。
三年來,在國家動員與強力支持下,我們搞出了疫苗,搞出了特效藥,這是很了不起的,說明我們在醫藥的研發上已有一定的積累和能力,但是在藥的設計上,無論是機理、針對性、有效性,我們仍是有差距的。我們在PD1研發上的一哄而起實際上就是暴露了我們在醫藥研發方面基礎薄弱的窘境。
為什么我們沒有大國應有的諾貝爾獎獲獎人數?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卡脖子”領域和技術?顯然,中國的科學研究基礎還很薄弱,基礎研究水平不高、積累不足,大多數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和前沿發展還有很大差距。短期內,要在大多數“卡脖子”領域突破,達到Me Too、Me Better,幾乎不可能。如此,我們要成就科創,建成創新國家,任重道遠。唯有臥薪嘗膽,花大力氣改革教育體制、科研體制,以二十年、三十年為維度,以造就一個世界級創新人才輩出的局面為目標,著力發掘孩子天賦,因勢利導、因材施教激發人才潛能,滿足科技人員較為優裕物質生活的要求,鼓勵他們潛心研究、成就事業,鼓勵他們積極拓展與國際先進同行交流合作。如此,經過兩代、三代教育工作者、科學技術專家的艱苦奮斗,我們就有可能在多數領域突破“卡脖子”圍困,在少數領域有First in Class的發現和創造,讓別人有求于我們,我們就可以通過技術合作和交換來更大程度地解除西方敵對性壓制。
沒有日積月累的努力和沉淀,我們不可能有突破性的發現和創造,科技創新不能輕信跳躍發展,也不應奢望彎道超車。今天我們要做的、還來得及做的,就是把科學當作老老實實的東西來做。
于是,我們要弘揚科學精神。什么是科學精神?今天上午人禾校長也談到他對科學精神的理解,有很多大師各有自己的闡述,我想從這個時代角度再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和呼吁。
第一是尊重科學規律。第二是實事求是,基于事實和事物本質,運用專業工具和方法,開展探索、研究、提煉、抽象、證明或證偽。第三,堅守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鼓勵積極進取、主動創新,提倡開放辯論、寬容試錯。第四,科學無國界,發展無邊界。第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勵質疑、批判,不固步自封、不迷信權威!
在今天這個科創時代,在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我還要提出一個新的科學精神內涵,即科技向善,科學家要使命驅動、擔社會責任、擁人文情懷。今天上午四位科學家都具有這樣的科學精神,都具有這種科技向善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我們小時候所受的教育,讓我們對科學家充分景仰與敬重,不僅是因為他們將一輩子致力于艱難的科學探索,也因為他們所從事的科學研究的崇高使命和科學創造的巨大價值。我們敬重他們的謙遜、執著和對真理的追求、對未知的敬畏,他們不功利、不狹隘,不為短期的功名利祿而放棄對自己的科學發現的堅守。
在一個物質不夠豐沛、文明開化不足、功利浮躁的社會,有些科研工作者仍會為了功名利祿而去放棄自己的科學信念,比如故意造假、迎合權力,口是心非,厥詞惑眾、排擠同行、貪圖虛名,個別人甚至到了人格分裂、喪心病狂的程度,所以尊重科學、追求真理,是件十分簡單卻又相當不容易的事情。在科學不夠昌明的時代,一些所謂的科學家沒有對真理的信仰、對科學的忠實。他們在實際利益面前做出的選擇,背離了他們的身份和大眾的期待,這就是為什么科學發展很難,科學傳播很難,科學堅守更難。
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能讓真理之光照耀社會前行的道路,能讓科學之光點燃大眾求知的欲望。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當然首先要依賴科學家的踐行、垂范,甚至犧牲。
歷史上,創立了解剖學的尼德蘭外科醫生維薩留斯,在1543年寫了一本附有插圖的著作《論人體構造》,為后來發現血液循環打下了基礎。天主教會認為他的研究“大逆不道”,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宣判了他的死刑。西班牙醫生塞爾維特是血液循環理論的重要發現人之一。他在名著《基督教的復興》中提出了人的心肺之間血液小循環的學說,但他也因此在日內瓦被新教處以火刑。還比如化學家拉瓦錫,他無疑是那個時代最杰出的天才,他制定元素周期表的雛形,設計并制造了無數劃時代的實驗設備,建立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實驗室,以實證主義精神建立現代化學。他堅守真理的底線,將沽名釣譽者拒于科學大門之外,卻被構陷終至殞命。
所以,科學的追求、真理的捍衛,是需要殉道的。雖然布魯諾的學說現在看來也是錯的,因為歷史的局限,科學發現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是在那個時代,他代表了科學發現的極限。科學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不斷去研究、探索乃至犧牲,才能不斷把科學的邊界推延和發展下去。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學工作者都能以殉道的精神去發展科學、堅守真理,但是我們仍然期望他們能夠恪守求真精神的本源,尊重公眾所給予他們的尊重。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知識分子所負的道德責任,是在生產理念的過程中,需要努力去達到思想的清晰和邏輯的延展,要求具有自由獨立精神和徹底思考的能力。
在這點上,我認為當今社會,張文宏醫生做到了。張醫生以他自己的專業為基礎、以實證研究為支撐來發表對病毒和疫情發展規律的看法,對疫情防控策略和方法的建議,既給大眾科普,也為政府獻策。他沒有功利的追求,也沒有迎合的舉動,只有盡其所知,在專家會議上提出分析和建言,盡其所能,在一線診室,包括社區病房和他自己醫院的病房治病救人。他雖然沒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他說出來的沒有謊言,沒有妄語,沒有違背他的專業認知,沒有放棄他的醫者仁心。縱觀他過去三年發表的論文、講話、建議,有個別研究的結果可能需要他進一步解釋和澄清,有個別的觀點可以討論,但是始終如一的見解、前后一致的邏輯已經證明他遵從理性、專業的立場和科學、職業的操守。在我眼里,他已經是這個時代的標桿,有善心和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標桿。他對科學精神的詮釋和恪守,足以支持他不需要去消耗時間、精力和智慧去投入無謂的辯論,他的沉靜已經贏得了這場不在同一級別上的論戰。
人在浩瀚宇宙面前只是一粒沙子,在科學面前再高大的人也是矮小的。雖然迄今為止,我們估計既有的科學知識只回答了人類所遭遇到的各種未知問題的5%,甚至還不到,但是對每個個體來講,科學知識已經是浩瀚無際了,所以我們要懷著謙卑和虛心的態度來學習科學。因為受制于每個個體的有限生命,我們要選擇專業來積累和發展科學知識。
科學的精神要求我們應該秉持自己的專業功底和實證發現來發表意見,雖然有些科學工作者智商很高,可以跨領域學習和研究,但這仍然不足以讓他超越自己的研究去評論和指摘其他領域專家的研究。搞小分子生物學研究的不一定懂傳染病學、公共管理學,其實也沒必要懂,反之亦然。一個科學工作者要去跨行抨擊另一個科學工作者,他的勇氣要么來自對另一學科領域的無知,要么來自把基于自己所在領域的成就建立起來的豪氣甩溢出去、去占領更多領地話語權的野心。這種霸道源自一種無知的傲慢,對自己無知的無知和對自己所從事科學工作應秉持的精神的傲慢。當然個別人還在背后、在不見光的地方有功名利祿的掛鉤,那就更不值得以君子之道待之了。總之,我認為,科學只要同功名利祿結合就會變味、就會變樣。
三年疫情的挑戰與應對給了我們許許多多的拷問和反思的機會,在科學與偽科學、假科學的博弈中,科學沒有始終占領上風。科學研究跟不上病毒的傳播,科學規律得不到社會的尊重,科學精神得不到廣泛弘揚,還有一點,就是沒有把管理當作科學。
管理,是基于大量的實踐觀察、研究、歸納、提煉、總結、創造出具有規律性的科學思想和方法,來提供針對現實問題、具有預見性的方案,并加以提前布局。同時,在方案實施執行當中實時地監控,通過對一些輸入變量可能的異常變化的監測來及時調整相應的策略,以求達到盡可能優的產出,所以管理是非常強調投入產出比的。這是全世界企業發展、產業發展所普遍遵循的原理和規律。如今,全世界管理學院貢獻的管理理論和思想方法早已溢出企業、產業的邊界,而廣泛運用于非營利組織、政府組織、甚至軍事單位。
三年疫情防控,有些政府做得比較好,有些政府做得不夠好,其差別除資源原因外,很大程度在于對管理是不是科學的認識上的差別,以及是否有能力運用科學的管理分析方法、制定合理的決策目標和效益評估機制,從而建立一個系統化、綜合化、彈性適變的防控方案,隨之有效地配置資源,有力地執行方案,并動態調整。
管理對于科創企業成功也有一半以上的作用,所以我們提出管理要賦能科創、引領科創。科創企業不僅科創要有突破,企業還要能盈利、能增長,因此科創企業家要有戰略先見,同時科創企業成長路徑、研發組織、商業模式、融資策略、激勵政策、治理構架、產業化與商業化方案等都有其獨特性,非今天管理學院EMBA、MBA課程知識能夠覆蓋,這也給了我們管理學者契機,從科創實踐出發,找到其管理上的痛點、難點,加以深入研究,從而創新理論、反哺實踐,幫助科學技術專家成功轉化為由系統、科學管理知識武裝的科創企業家。管理與科創必須雙引擎驅動,才能顯著地提升科技創新的成功概率和質量,避免與投資機構、專業中介無謂的博弈消耗,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產品驗證和商業化過程,以每個科創企業的成功助力產業創新和升級。
當然,無論管理的對象是人是事,還是組織、社會,都具有非常的復雜性,而且還會有各種臨時的變化、突發的事件,所以,管理還有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例外原則。今天我們強調管理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95%的管理工作要遵循既有的計劃、規則和標準。這是基于已有的知識和理性加以規范的,但是我們也要允許5%的事件,那些例外事件,要依賴于決策人和執行人個人的經驗、直覺來做出判斷并采取應急的、臨時的舉措,以避害趨利。這也是管理原則。所以管理上要強調容錯,尤其在管理的創新實踐方面,要有更大的寬容心去支持創新,而不應該拿陳規陋習來約束創新、制裁創新、懲罰創新。引發我們國家翻天覆地變化的進程始于4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其實這也是國家治理中例外原則的體現,反映了小平同志的經驗、直覺和戰略洞見、高瞻遠矚。
科創企業的實踐迄今為止少有現成的理論、規范和標準可以加以指導,所以一方面我們要加快科創管理理論創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以例外原則來鼓勵科創企業探索并不斷總結提煉新的管理原則。
管理科學的發展當然離不開管理學院的發展。管理學院是以傳播管理的科學思想和方法,培養專業的管理人才,激發企業家精神,促進經濟發展與繁榮、社會福祉,推動文明進步為使命。一個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的成長與發展,也有其自身規律。每個管理學院如同大學,都是有其使命和定位的,它能夠成為世界公認的一流管理學院,一定是遵從了大學獨立自由、開放多元的理念。如果沒有像復旦校歌中所唱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那么科學發現、知識創新、思想傳播、人才培養就無從談起。管理科學的發展一定是在世界范圍內的知識和信息的交互、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乃至觀點證據的交互指證,才可以發展成一個高等的科學知識體系。
借此機會,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在2022年歲尾,法國環球教育(Eduniversal)全球最佳商學院的排名中復旦管院名列遠東亞洲榜首。這個排名是邀請全球近一千家知名商學院院長來投票,給各地區的商學院進行排名,2022年有73%的院長進行了投票。這個投票不基于任何定量的指標,而基于每個院長個人的觀察和認識。這些模糊的印象匯總起來,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清晰、客觀的評價。我們在這次投票當中再次成為遠東亞洲并列第一名,這是過去十幾年我們一直感到欣慰的地方,因為我們一直被全球同行認為是遠東亞洲前三名的商學院,這同我們的實際發展水平和地位是相符的,也證明了我們確實是按世界一流管理學院的發展規律在不斷地實踐,不斷地發展我們自己的學術和教育,并獲得世界范圍同行的認同和尊重。
我想說的是,辦世界一流管理學院,其實是極其艱難的過程,不僅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長期的耐心,還要有對科學和真理的堅定信仰和追求。這也是許多世界一流大學在其校徽和校訓中所宣示的。
同時,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也一定是遵循有機增長的戰略,日積月累,循序漸進,以質量為優先,經過幾十年的堅持努力才能夠表現出超越同行的優異貢獻與實力。我們看到,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在歷史的若干發展階段,是在當時有遠見的領導者的主導推動下,改革創新,讓其發展躍上一個面向未來的新平臺。有若干次這樣的跨越發展,就足以奠定它廣受同行尊崇的地位。
當今,全球一流商學院還以培養企業家、激發和提升學生企業家精神為優先使命。不是所有管理學院的學生都適合創業,并成為成功的企業家,但企業家精神是可以被激發和培養的,它對于學生在VUCA時代從事職業經理工作也是十分必需的。一般認為,企業家精神意味著創新、冒險、創造財富,也意味著在VUCA時代,要發揮每個個體潛能、創造企業成長機會和空間、對抗不確定性。
我認為,企業家精神對于科創企業成功尤為重要。因此,我對企業家精神認識稍異于傳統。我認為,企業家精神最大的特征與價值在于企業家的自驅力和學習力。經典的學者如馬克斯·韋伯呼喚企業家精神,他認為企業家是自利的,他們因為追逐私利而奮斗,從而促進企業去競爭、去發展、去創造財富,從而促進社會繁榮,并惠及整個大眾。然而我所認識的科創企業家們已是當代中國第四代企業家,同前三代企業家有個顯著的區別在于,他們不是因為貧窮而創業,更多的是因為他們有科學理想,有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他們愿意個人致富,但在財富觀上也更開放,更愿意分享,這些人往往都有使命和情懷。
所以,我認為自驅力是企業家精神光輝的特質,它并不以企業家擁有產權、追逐私人財富為前提。而這種無數個別的企業家的自驅力匯合起來就形成了這個社會經濟驅動的巨大原動力,因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在少數國有企業,董事長或CEO雖然不擁有股權,也無直接掛鉤的經濟利益,比如像寧高寧,卻也有強勁的企業家精神,把企業由平庸發展成為行業翹楚甚至跨國巨頭。
同時,成功的企業家都有很強的學習力,這同其學歷似乎沒有太大的關系,像輟學的比爾·蓋茨,小學文化的李嘉誠都是善于學習的企業家。他們不僅從自己先前的經驗教訓中學習,向同行學習,而且逐漸地跨越行業、跨越文化去學習,有的還進到大學、進到管理學院去進修,逐步匯聚、學習、借鑒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智慧。這些人才是真正聰明絕頂的、會學習的企業家。由此而持續學習,企業家就容易地、更快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變得通透和前瞻,其直覺也更多了理性分析和規律把控的支撐。由此其領導的企業就不會受制于路徑依賴,而是基于對各種廣泛的、有價值的知識學習、吸收,并越發具有超越平庸的競爭力。這也是為什么我特別佩服比爾·蓋茨和李嘉誠,因為他們是當代企業家當中最懂得知進退,也是最善于學習的企業家代表。
所以,企業家精神是先進生產力,代表著這個社會的潛能、動力和方向,是這個社會最值得珍惜的資源和資產之一。對于科創時代,尤其如此。我們可以說,無企業家精神,無未來。
當然有企業家精神,也并不一定有未來,因為它的萌芽、發育、成長也需要環境條件的催化、滋養和呵護,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真正的市場,其前提就是公平、自由的交易機制和充分、有效的法治環境。
當今世界政治形勢波詭云譎,經濟秩序分化重組,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彷徨、去等待。企業家精神會折損、消耗殆盡,科創企業也會挫敗,被打回原形。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歷史時點,面向未來,我們仍然有太多的焦慮、無助和掙扎,甚至有的人還有恐慌。疫情肆虐,沖突不止,然而我們是因為樂觀而活在當下,因為樂觀我們得以長遠期待,并付出努力。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暢想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所理解的人類社會的面貌,想象人工智能時代人可以活多少歲,服務機器人如何服務到家,我們不僅在地面上享受自動駕駛,也可以在空中實現立體自由移動。那時,我們會享受更多的自由,人民也會有更多選擇的權利。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科學技術和文化,最終都會在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分享。我深信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會越來越好。
但在現實面前,我們的樂觀應該是審慎的,我們仍然要回到事物發展規律的認識上去,我們仍然要用科學來武裝自己。為什么要審慎?因為這個未來并不是自動到來的。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可能會走岔,明明應該向左但我們向右了,明明應該向前我們向后了,我們以為是向前了,結果我們是走下坡路。也許我們右拐一下又可以再左拐一下,然后再回到正向的康莊大道上。
盡管科創是今天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但這個主旋律并不是那么的強勁、清晰,可以令創業者一往無前。其實它本身能否引領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引領中國經濟去迎接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必須倡導真正的大學精神、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這是國家社會走進新時代、進行現代性轉型的動力。哈耶克曾經認為,人類心智的成長,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共同問題,其中會產生必然的思想分化和碰撞,我們抱有怎樣的態度至關重要。我們培育什么樣的土壤,才會開出什么樣的花。
今天在我們新年論壇上,科學家、企業家、管理學家的分享,正是對真正的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自然人性最真切的呼喚和頌揚。
我相信,隨著科學精神的傳播和啟迪的不斷深入,我們將無須在發現“病梅”之后才“療之,縱之,順之”,而是在培育之初,就呵護好它們的自然生氣,使其曲也美、直也美,密也美、疏也美。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在春天來臨之前我們也許確實需要像杜鵑那樣啼血鳴叫,相信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踏在新年的起點上,讓我們對科學、管理與文明堅持不懈追問和探索,讓我們以人文之火去溫暖心靈,用理性之光去洞悉未來。在新的一年里,期待我們可以同心共創、攜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