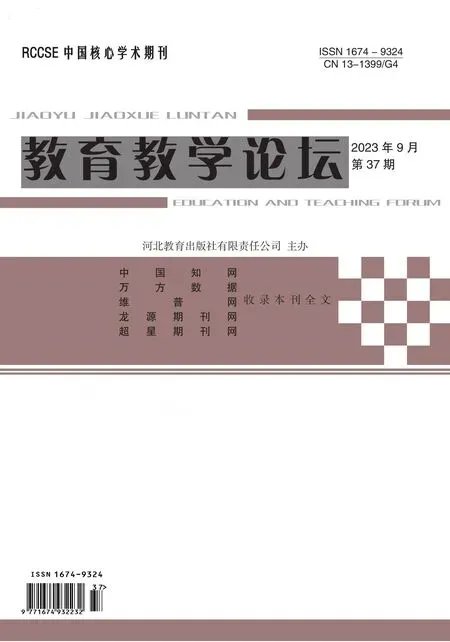多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聲樂教學(xué)
[摘 要] 中國聲樂教育在多種藝術(shù)思潮的交融下產(chǎn)生。自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聲樂走過了數(shù)個(gè)重要的發(fā)展階段。在多元文化視野下,高等院校音樂專業(yè)建設(shè)需要繼承傳統(tǒng),發(fā)揚(yáng)創(chuàng)新精神,承擔(dān)起社會(huì)音樂普及與學(xué)科專業(yè)鼎新的義務(wù)。目前的中國聲樂教學(xué),存在多元文化性不足的現(xiàn)象。基于此,在實(shí)踐教學(xué)中,聲樂教師應(yīng)加強(qiáng)自身的民族音樂知識(shí)儲(chǔ)備,在課程與教材建設(shè)中應(yīng)以對(duì)外傳播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為目標(biāo),促進(jìn)國際音樂交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關(guān)鍵詞] 多元文化;聲樂;課程;聲樂教學(xué)
[基金項(xiàng)目] 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聲樂語音學(xué)視域下中國聲樂作品唱詞正音的理論建構(gòu)與實(shí)踐研究”(20YJC760047)
[作者簡(jiǎn)介] 李偉彤(1989—),女,天津人,博士,浙江師范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講師,主要從事聲樂語言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 G642.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文章編號(hào)] 1674-9324(2023)37-0035-04[收稿日期] 2023-04-06
1916年,北京大學(xué)音樂會(huì)成立,分國樂、西樂二部。1918年,蔡元培在代擬章程中將音樂會(huì)更名為樂理研究會(huì)。1919年1月,“樂理研究會(huì)”再次更名為“北京大學(xué)音樂研究會(huì)”,蔡元培任會(huì)長(zhǎng)[1]。北京大學(xué)音樂研究會(huì)成立之初,設(shè)有鋼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組。1920年增設(shè)歌組[2],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聲樂組導(dǎo)師的是來自英國的紐倫。可以說,中國的聲樂教育,是在多元文化藝術(shù)的交融下產(chǎn)生的。高校聲樂專業(yè)在中國聲樂教學(xué)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到多元性在學(xué)科內(nèi)部的呈現(xiàn)。
一、從“樂歌”課到“聲樂”課
“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茍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shí)為學(xué)校中萬不可缺者。”(見《飲冰室詩話》)[3]學(xué)堂樂歌最早出現(xiàn)在初、高兩級(jí)小學(xué)堂的“樂歌”課中,授課方式以齊唱為主,以沈心工、李叔同為代表的音樂啟蒙教育家采用依曲填詞的方式,將外國的曲調(diào)賦予中國化的意義。此時(shí)的樂歌是音樂啟蒙教育的重要媒介與工具,樂歌的教授與傳唱雖不涉及歌唱的技法,卻為西方聲樂藝術(shù)進(jìn)入中國打下了基礎(chǔ)。五四運(yùn)動(dòng)后,中國出現(xiàn)了早期的音樂社團(tuán),1920年出現(xiàn)在北京大學(xué)音樂傳習(xí)所的前身——北京大學(xué)音樂研究會(huì)中的歌唱課,是現(xiàn)代聲樂教學(xué)的開端。值得一提的是,古琴組附有“中樂歌唱”,專門講授中國聲樂作品。1927年,上海“國立音樂院”成立,由蔡元培兼任院長(zhǎng),蕭友梅任教務(wù)主任。全院分理論作曲、鋼琴、小提琴及聲樂四系,“音樂院”的命名是對(duì)應(yīng)了英文中的音樂學(xué)院(conservatory)。至此,聲樂在中國作為一門獨(dú)立學(xué)科正式出現(xiàn)在院校音樂教育當(dāng)中。
1930年,蕭友梅邀請(qǐng)?zhí)K石林擔(dān)任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xué)校教授,他是將俄羅斯美聲唱法帶到中國的第一人。賀綠汀高度評(píng)價(jià)蘇石林為“中國聲樂的奠基石”[4]。在此期間,第一批留學(xué)海外的藝術(shù)家學(xué)成歸國,周淑安畢業(yè)于哈佛大學(xué),回國后首先在廣東省女子師范學(xué)校開設(shè)了聲樂課,這是中國最早的美聲教育課堂。后又在上海中西女塾、廈門大學(xué)任教[2]。這一時(shí)期的“中國四大女高音”——黃友葵、喻宣萱、郎毓秀和周小燕,后期都成了融匯中西的聲樂教育大家。20世紀(jì)上半葉的聲樂教育以“學(xué)西”為主,音樂教育機(jī)構(gòu)的設(shè)立,學(xué)分學(xué)制的建設(shè)基本照搬國外,大部分的聲樂教育者擁有海外學(xué)習(xí)背景,使得美聲演唱與美聲教學(xué)在中國落地開花。以西洋美聲教學(xué)為主導(dǎo)的聲樂教育在中國持續(xù)了近三十年,直至1949年底,聲樂史上著名的“土洋之爭(zhēng)”,將原本應(yīng)該融合并蓄的民族演唱與美聲演唱推向了對(duì)立互斥的局面。在此之后的聲樂教學(xué),會(huì)非常明確地分出“民美”。“土洋之爭(zhēng)”其實(shí)是新中國時(shí)期聲樂表演與聲樂教學(xué)中多元文化矛盾的體現(xiàn),它將藝術(shù)性與技術(shù)性極強(qiáng)的聲樂學(xué)科現(xiàn)象上升到了文化認(rèn)同的層面。聲樂藝術(shù)雖然是一種用人聲來表現(xiàn)的藝術(shù),但它并不單純是一種發(fā)聲機(jī)制的綜合,而是包含著許多復(fù)雜的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是通過某一表現(xiàn)方式體現(xiàn)出來的,它可以是美聲唱法,也可以是民族唱法[5]。2011年,金鐵霖教授在第五屆全國民族聲樂論壇上提出,“民族聲樂”要進(jìn)入“中國聲樂”發(fā)展階段[6],為民族聲樂發(fā)展指出了方向。現(xiàn)代中國聲樂教學(xué)中的聲樂課,除了教授科學(xué)的發(fā)聲技法,還應(yīng)包含多地域、多民族、多語言、多風(fēng)格的多元教學(xué)內(nèi)容,以體現(xiàn)世界民族與中華民族更加豐富的藝術(shù)文化內(nèi)涵。
二、多元文化在聲樂教學(xué)中的體現(xiàn)
與其他音樂表演形式相比,聲樂表演因其所包含的唱詞語言與肢體語言,為音樂作品的詮釋增加了更多維度。筆者于2015年受國家留學(xué)基金委資助赴美深造,在紐約曼哈頓音樂學(xué)院讀書期間,對(duì)于美國聲樂專業(yè)教學(xué)最大的感悟就是:歌唱技法與藝術(shù)文化修養(yǎng)的全方位培養(yǎng)。專業(yè)課上,教師主要教授歌唱技能,解決學(xué)生在歌唱中的技術(shù)瓶頸,為學(xué)生規(guī)劃合適的選曲類型等;在不同語言的唱詞正音課上,教師負(fù)責(zé)規(guī)范學(xué)生的歌唱語音,配合講授唱詞語言背后的文化內(nèi)涵;在藝術(shù)指導(dǎo)課上,教師的教學(xué)重點(diǎn)在于作品的詮釋與音樂表達(dá)的處理。在聲樂語言訓(xùn)練中,不同語言的正音教學(xué)通常由母語者承擔(dān),比如德語唱詞正音由德國籍男高音教授,俄語唱詞正音由俄國籍藝術(shù)指導(dǎo)教授等。聲樂專業(yè)的學(xué)生在這些課程中除了深入學(xué)習(xí)不同語言的聲樂作品,也能受到聲樂作品中多元文化的熏陶。
在國際聲樂歌唱正音體系中,中國作品是長(zhǎng)期缺席的。由于漢字是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漢語拼音與國際音標(biāo)不通用等客觀問題,導(dǎo)致中國聲樂作品的學(xué)習(xí)門檻很高,這使得我國聲樂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受限。在國內(nèi)聲樂教學(xué)中,意大利語的教學(xué)作品相對(duì)豐富,在教學(xué)實(shí)踐中使用較多,而德語、法語、俄語、捷克語等語言同樣受限于自身的語言語音門檻,中國學(xué)生學(xué)習(xí)時(shí)難度較大,藝術(shù)指導(dǎo)最重要的任務(wù)之一就是掃清學(xué)生學(xué)習(xí)多種語言作品的唱詞障礙。放眼中國的聲樂教學(xué),學(xué)生的歌唱技法、語言、作品處理等問題解決多集中在專業(yè)導(dǎo)師一人身上,期盼一位導(dǎo)師精通多國語言顯然是不現(xiàn)實(shí)的,這就導(dǎo)致目前教學(xué)多元文化不足的現(xiàn)狀。學(xué)生對(duì)于聲樂作品文化視野的開闊度,取決于其聽、看、學(xué)、演的曲目數(shù)量和曲目多元程度。筆者的導(dǎo)師金鐵霖教授在教學(xué)中非常注重對(duì)于學(xué)生多元文化的熏陶和培養(yǎng)。金教授曾提出:“民族唱法的學(xué)生學(xué)習(xí)、演唱過外國歌劇詠嘆調(diào)后,再演唱中國作品會(huì)有不一樣的體會(huì)與感悟。”著名歌唱家張也就演唱過《楊柳,楊柳》(意大利語),宋祖英曾演唱《告別時(shí)刻》(英語),王麗達(dá)曾演唱《復(fù)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燒》(德語)等。郭淑珍認(rèn)為,聲樂表演和教學(xué)不應(yīng)該有一種狹隘的民族觀念,中國人應(yīng)該唱好中國作品,但也應(yīng)該能夠唱好外國作品。因?yàn)樗囆g(shù)是人類的財(cái)富,它應(yīng)當(dāng)屬于全人類;我們演唱中國作品也正是為了把這份人類的財(cái)富介紹給全世界人民[5]。筆者認(rèn)為,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避而不談,而是開放包容。
在國內(nèi)高校的聲樂專業(yè)教學(xué)中,多民族文化的存在感比較薄弱。筆者在中國音樂學(xué)院讀書期間,學(xué)校開設(shè)有漢族民歌課、少數(shù)民族民歌課、說唱課、古曲課,這些都是傳統(tǒng)音樂中重要的藝術(shù)體裁,其所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簡(jiǎn)譜記譜的手寫稿。而這些課程中的歌曲,基本不存在“照本宣科”,而都是“口傳心授”。唱詞雖都記為普通話,但是漢族民歌與少數(shù)民族民歌涉及不同地域的方言。說唱課上,第一節(jié)課學(xué)習(xí)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教師雖是拿著一份歌詞教唱,但說唱唱詞的發(fā)音包含了諸多變音;古曲課上,唱詞所涉及的許多古韻,也是漢字無法充分展示的。這樣所造成的問題就是,雖然聲樂專業(yè)的學(xué)生必修這些課程,但是修畢后,很少有人再去演唱課上學(xué)到的作品,除非自己的導(dǎo)師在某一個(gè)領(lǐng)域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比如中國音樂學(xué)院董華教師的學(xué)生多演唱陜北民歌,是因?yàn)槎蠋熢陉儽泵窀桀I(lǐng)域有著比較高的造詣。另一個(gè)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作品仍處于“詞音皆無形”的原始材料狀態(tài),表演形式多為無伴奏清唱,如果沒有相關(guān)教師面對(duì)面講授,學(xué)生是無法“正確”詮釋這些歌曲的。目前教授相關(guān)課程的師資,大多為音樂學(xué)專業(yè)出身,這就導(dǎo)致了一些優(yōu)秀的民族民間作品在兩個(gè)專業(yè)(音樂學(xué)與聲樂)之間的信息差。目前在聲樂教學(xué)中更常用的,還是唱詞與和聲配器更為規(guī)范的由民歌改編的創(chuàng)作歌曲,比如《瑪依拉變奏曲》《青春舞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等。但是,創(chuàng)作歌曲所包含的民族多樣性與豐富性,是無法與音樂學(xué)領(lǐng)域的民族音樂材料相比的。
三、多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聲樂課程與聲樂教材
(一)中國聲樂的世界話語:開設(shè)漢語唱詞正音課的必要性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中國作協(xié)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開幕式上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5點(diǎn)希望,其中第四點(diǎn)是: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7]。新時(shí)代的音樂工作者想用中國聲樂講好中國故事,就需要在歌唱語言上把握好中國特色。
在所有音樂品類中,聲樂與語言的關(guān)系較為密切,所以,聲樂學(xué)科中語言與歌唱的有機(jī)結(jié)合十分值得關(guān)注。唱詞正音是聲樂專業(yè)基礎(chǔ)學(xué)科的重要內(nèi)容,是與聲樂專業(yè)課、視唱練耳課同等重要的基礎(chǔ)課程,如同數(shù)學(xué)在自然科學(xué)、統(tǒng)計(jì)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管理學(xué)中的學(xué)習(xí)一樣,其基礎(chǔ)性和重要性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當(dāng)代聲樂教育體系中,還沒有形成針對(duì)漢語聲韻演唱的正音體系和具體的正音方法,致使聲樂教學(xué)多偏重于聲音技巧的訓(xùn)練,忽視了歌唱的本質(zhì)——唱詞語韻與音樂曲調(diào)合為一體的有聲表達(dá)。
在正音課程的建設(shè)上,國內(nèi)各院校皆有涉及,但并不完善。上海音樂學(xué)院本科美聲專業(yè)在第一學(xué)年開設(shè)歌唱語音課程,中央音樂學(xué)院美聲專業(yè)在本科第二學(xué)年開設(shè)歌唱正音課,中國音樂學(xué)院美聲專業(yè)在本科第一學(xué)年和第四學(xué)年開設(shè)臺(tái)詞課。在課程內(nèi)容上,上海音樂學(xué)院和中央音樂學(xué)院側(cè)重歌唱中的語言,中國音樂學(xué)院重視訓(xùn)練舞臺(tái)表演中的臺(tái)詞語言。在其他語言的演唱上,比如意大利語、德語、法語等,各高校開設(shè)的課程多以語言課為主,學(xué)生在課上學(xué)習(xí)一些基本語法與簡(jiǎn)單的對(duì)話。與之相比,國外的專業(yè)院校會(huì)針對(duì)不同語種開設(shè)唱詞正音課。在這個(gè)較為成熟的課程體系中,母語正音是優(yōu)先于外語正音的。比如茱莉亞音樂學(xué)院、曼哈頓音樂學(xué)院、曼尼斯音樂學(xué)院,都將(針對(duì)演唱的)英語正音與其他語言正音放在同一課程模塊下有序進(jìn)行。其中,曼尼斯音樂學(xué)院將同一語種的唱詞正音課和語言課設(shè)置為兩門不同的課程,更加突出了正音課的“專業(yè)性”。
漢語唱詞正音課的建設(shè)應(yīng)以漢語普通話為基準(zhǔn),以體系化建設(shè)為目標(biāo)向多民族語言延伸。“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8],本意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更容易獲得世界的關(guān)注。但是在真正的文化輸出中,具有優(yōu)先級(jí)的應(yīng)該是主流文化,而不是需要被搶救的小眾文化。我們演唱中國歌曲的目的正是在于為全人類共同的文明而努力,而不應(yīng)是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chǎng)上,允當(dāng)一種使“共通基質(zhì)”處于黑暗之處的人為的力量[5]。中華大地地域廣茂,民族眾多,56個(gè)民族中哪一個(gè)能代表中華民族呢?著名語言學(xué)家周有光先生講,我國的56個(gè)民族共有80多種彼此不能通話的語言和地區(qū)方言。哪一種民族語言更優(yōu)秀呢?在新聞聯(lián)播、春節(jié)晚會(huì)和國家外事活動(dòng)中,普通話仍然是中國人民重要的溝通方式。漢語唱詞正音體系的建立與傳播,將彌補(bǔ)中國聲樂作品在世界聲樂教育范圍內(nèi)傳播受限的遺憾。一方面,有利于聲樂學(xué)科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下的繁榮發(fā)展,力求在專業(yè)教學(xué)中體現(xiàn)時(shí)代性、科學(xué)性、民族性;另一方面,中國聲樂唱詞正音體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國聲樂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唱詞正音體系中的唱詞語音教學(xué),除幫助母語者完成正音外,還能幫助非母語者更加快捷有效地學(xué)習(xí)演唱中國作品,進(jìn)而促進(jìn)更多的中國聲樂作品進(jìn)入國際視野。
(二)多民族音樂的珍貴資源:編纂多民族語言唱詞正音教材的必要性
練聲曲在聲樂訓(xùn)練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傳統(tǒng)聲樂教學(xué)中,練聲曲并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練聲曲教材不應(yīng)該僅具“練聲”功能,還應(yīng)該在一定體系與規(guī)范下訓(xùn)練學(xué)生處理不同音樂結(jié)構(gòu)中的唱詞語音。目前,我國聲樂教學(xué)中所使用的練聲曲教材,大部分是“拿來主義”,即直接使用國外的教材。國內(nèi)最早編纂的練聲曲教材《晨升69聲字結(jié)合練聲曲》(石惟正教授編著)和《歌唱咬字練聲曲30首》(宋承憲教授編著)中對(duì)于漢語音韻與練聲曲有機(jī)結(jié)合的思路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按照漢語普通話音系編纂漢語音韻練聲曲,不僅有助于唱詞正音的訓(xùn)練,也能夠?qū)h語中的實(shí)際音素與不同的音高、節(jié)奏、旋律以及演唱技巧相結(jié)合,達(dá)到歌唱正音訓(xùn)練的目的。
從世界范圍內(nèi)更加宏觀的應(yīng)用角度來看,國內(nèi)對(duì)于中國聲樂作品唱詞的國際化注音是缺失的。在北美開設(shè)音樂專業(yè)的高校,都會(huì)購買相應(yīng)的歌詞注音數(shù)據(jù)庫,為學(xué)生學(xué)習(xí)多語言作品提供支持。在數(shù)據(jù)庫里,學(xué)生可以根據(jù)作曲家、作品抑或是語言的索引,找到被規(guī)范注音與翻譯的意大利語作品唱詞、德語作品唱詞、法語作品唱詞、俄語作品唱詞、西班牙語作品唱詞、捷克語作品唱詞等,但卻找不到中國作品。所以,基于多民族音樂背景的聲樂教材建設(shè)是音樂人時(shí)不我待的重要任務(wù)。如果中國聲樂作品可以做到標(biāo)準(zhǔn)的國際化語音標(biāo)注,那么一系列標(biāo)注唱詞注音的中國聲樂作品教材就能夠得以出版,繼而通過音系的整理與編配,標(biāo)注多民族聲樂作品。這將使中國聲樂作品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傳播度得到極大的提高,其他國家的高校可以據(jù)此開設(shè)中國聲樂作品課程。甚至在高端的國際聲樂比賽中,我們可以聽到、看到外國選手選唱中國聲樂作品。
綜上所述,建設(shè)漢語唱詞正音課程,編纂唱詞正音教材,是聲樂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終目的,是使專業(yè)院校的學(xué)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唱詞語音,使其擁有獨(dú)立判斷、修正唱詞語音問題,以及正確演唱作品的能力。同時(shí),挖掘豐富的民族音樂寶藏,深入學(xué)習(xí)理解與積極傳播我國豐富的民族音樂文化。中國聲樂要想走向國際,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要想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傳播,就要與國際接軌,降低外國同僚學(xué)習(xí)中國聲樂作品的語音門檻。只有中國作品邁出國門,才能進(jìn)一步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參考文獻(xiàn)
[1]林晨.北京大學(xué)音樂研究會(huì)[J].中國音樂學(xué),2010(2):87-94.
[2]張曉農(nóng).中國聲樂藝術(shù)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241.
[3]錢仁康.學(xué)堂樂歌考源[M]//張曉農(nóng).中國聲樂藝術(shù)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233.
[4]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huì),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參考資料[M]//張曉農(nóng).中國聲樂藝術(shù)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273.
[5]王次炤,郭淑珍.中國作品演唱和教學(xué)述評(píng)[J].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9(2):88-90+93.
[6]金鐵霖.中國聲樂的發(fā)展與未來:繼承、借鑒、發(fā)展、創(chuàng)新[J].人民音樂,2013(11):51-53.
[7]習(xí)近平在中國文聯(lián)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中國作協(xié)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開幕式上發(fā)表重要講話[EB/OL].(2021-12-14)[2023-03-08].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14/content_5660777.htm?jump=true&wd=&eqid=fdd8e57e000b0023000000026487d035.
[8]魯迅.魯迅書信[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2:674.
Chinese Vocal Music Teaching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LI Wei-tong
(College of Art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vocal music educ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multi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Since 1949, Chinese vocal music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importa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inherit traditions,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undertake the obligation of popularizing social music and renewing disciplines.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multiculturalism in Chinese vocal music teaching. Based on this, in practical teaching, vocal music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knowledge of multi-ethnic mus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goal should be to disseminate the Chines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mote international music exchanges,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to the world.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vocal music; curriculum; vocal music tea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