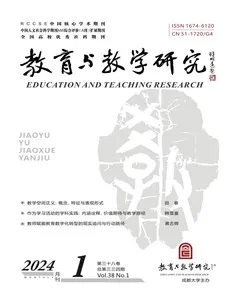作為學習活動的學科實踐:內涵詮釋、價值期待與教學路徑
韓雪童
[摘 要] 作為積極能動的認識活動,完整的實踐應當是由心智與身體共同組成、相互促進且彼此制約的雙重結構。學科實踐是在汲取實踐共通性的基礎上聚焦學科特質、持守學科立場的特殊實踐,鼓勵學生在參與學科關鍵活動的能動體驗中,以“交互”取向喚醒主體意識、以“生成”取向激活創新活力、以“整體”取向孕育核心素養、以“聯通”取向回歸生活世界。學科實踐的落地可以通過營造真實化的實踐情境、甄選結構化的實踐資源、巧設線索化的實踐引導、提供鑒賞化的實踐評價等路徑,使之切實且生動地發生,進而以實踐興趣的催生、實踐選擇的拓寬、實踐能力的提升和實踐智慧的孵育,將知識真正帶入學生的生命。
[關鍵詞] 實踐;身心實踐;學科實踐;學習活動;實踐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2.0[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674 - 6120( 2024)01 - 0027 - 13
實踐活動因其知行合一、身心融合、學用交匯的特質以及學習中心、過程本位、質量為重的旨趣,成為培育學生核心素養的必由之路。《義務教育課程方案(2022年版)》明確提出“變革育人方式、強化學科實踐”的任務要求,以期借助“做中學、用中學、創中學”的模式,塑造學習方式的新樣態以及教學轉型的新方向,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多元學科活動,扭轉“先知后行”的邏輯次序,重建“知在行中”的邏輯關聯,以直接經驗為“錨點”、間接經驗為“養分”,實現發現問題與識別知識、分析問題與剖析知識、處理問題與理解知識、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遷移問題與應用知識之間的融會貫通,讓知識從問題中浮現出來,讓能力從做事中孕育出來,讓素養從過程中生長出來,從而助力高質量課程教學體系的建設。
一、學科實踐的內涵詮釋
探賾索隱方能鉤深致遠。“實踐”是“學科實踐”的根脈與地基,廓清“實踐”的內涵,是闡明“學科實踐”概念的必要前提。
(一)實踐的內涵闡釋
實踐是一種特殊的認識活動。歷史上哲學家對人類認識從何而來的話題爭論不休。在理性論者看來,世界存在固定、永恒、不變、先于人類而存有的唯一本質,人類寄希望于由天賦理性孕育的認識來擺脫不確定的風險。然而,這受到懷疑論者的反對。他們指出,認識者只能靠近、摹寫真理,卻永遠無法獲得、揭示先驗真理。針對理性論的缺陷,經驗論應運而生。人們將尋求確定性的希望寄托于經驗歸納,但受制于歸納范疇的局限性,認識者憑借實驗所察知的現象、歸納的走勢,只是“相對性法則”而非“絕對性真理”。
實踐從經驗論中衍生而來。然而,并非一切經驗中的活動均可被稱作實踐,只有主體作用于客體,并將間接經驗吸收、內化為直接經驗的能動活動才可被稱作實踐,反之,任意操作、機械訓練、強制懲罰類的活動均不是實踐。通常看來,實踐有兩種理解:廣義實踐泛指身心活動,狹義實踐特指與思維對立的身體活動、與理論對壘的行動產物。然而,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1]286,實踐是“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1]296。可見,毛澤東所秉持的實踐乃是廣義實踐,即身心合一的活動。《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將“識字與寫字、閱讀與鑒賞、表達與交流、梳理與探究”歸為語文學科實踐,亦表明語文課標中對“實踐”的界定,也是遵循廣義實踐的身心活動。基于此,本文亦采用廣義實踐的界定,將實踐定義為身心共在的能動活動。
(二)學科實踐的內涵闡釋
自2001年開啟“新課程改革”后,“自主、合作、探究”成為教育界爭相追捧的新型學習方式,然而,學科核心素養的出現,卻遠超探究學習能夠涵蓋的范疇。從應然層面來看,一則,探究學習適用于規律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不太適用于事實性知識和陳述性知識。由于事實性知識和陳述性知識需要學生將抽象符號與真實事物建立起關聯,故而,它們更適合用直觀學習;公理性知識因其是由學術共同體擬定與確證的規范和法則,學生若一味強調質疑性探究,必會跌入相對主義的漩渦,故而,它們更宜用接受學習。二則,探究學習更適用于科學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學習,人文知識的學習更適合采用學科鑒賞、學科審美、學科想象等實踐方式。從實然層面來看,探究學習在實際教學中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虛探究、假探究的現象屢見不鮮。探究學習大行其道的同時,也呈現出偏離目標的亂探究、程序固化的淺探究、質疑一切的泛探究等現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種課堂上經常出現的‘一分鐘探究,教師剛布置好探究任務,一分鐘不到就要學生匯報展示成果”[2]31。如此倉促的探究學習,因其流于形式、脫離實質,終究只能深陷表層化與表演化的泥沼。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學科實踐不要學科探究,相反,學科探究應成為學科實踐的一種類型。
學科實踐是基于學科立場的特殊實踐,作為重要的學習活動,它既保留實踐的基本特征,又具有學科的差異性。“學科立場就是某個學科特有的研究領域、知識結構、話語邏輯、研究范式和價值追求等構成的體系。它規定學科的界限”[3]48。故而,盡管學科間仍有部分實踐是存在共性、能夠且需要互涉的綜合實踐,但學科實踐則是基于不同學科特質的身心共在的能動活動。從整體來看,學科實踐反對教師以灌輸者的身份就理論講理論、學生以旁觀者的身份與理論疏離,而是主張教師以引導者身份、學生以參與者身份,在身心共在的活動中完成對知識的消化、吸收、領會。
學科實踐以對知識的理解和運用為基礎,以解決真實的學科問題和生活問題為主軸,以知識向素養的轉化為追求,有力地回應了傳統學科教學中排斥身體、疏離情境、遮蔽過程、漠視應用的困境。從學科實踐的發生來看,通過對身心素質的整體性調動,將概念知識還原化、觀念假設實驗化、邏輯仿擬具身化、符號空想體驗化,以克服傳統教學活動導致的片面理解、命題識記、倒灌傳遞、虛假探究的弊病,重建學科知識與生活世界之間的關聯。
(三)學科實踐的結構組成
從表層來看,學科實踐包括實踐者、實踐對象、實踐情境、實踐任務、實踐工具、實踐指導手冊、實踐方案和實踐體驗等。從深層來看,學科實踐的結構組成可以從調動要素、內容范疇、過程類型三個維度加以剖析。
其一,學科實踐所調動的要素既包含身體行動,也包含思維推理。通常而言,人們普遍將實踐等同于身體活動,這雖凸顯了身體的價值,卻也陷入“重身輕心”的困局。身體活動確實可以滿足學生天性的需要,他們“依靠身體與外界建立聯系來獲得直接經驗,并且在不斷的身體接觸和體驗中確證和建構自己的意義世界”[4]4。然而,對身心關系的割裂,卻延誤了思維的發展,限制了學生的眼界。因此,雖然對理論知識的學習不能“思而不行”,但是為了獲得抽象凝練的規律、生成天馬行空的想象、理解高深莫測的原理,心智的參與亦不可或缺。換言之,只有身心共在,才能實現“感性實踐一知性實踐一理性實踐”的躍升。“共在”并不意味著“均分”,而是要二者處于動態平衡。在不同類型的知識中,身心發揮的功能各不相同:在陳述性知識中“心”發揮主導作用、“身”發揮輔助作用,主要表現為推理實踐、想象實踐、識記實踐;在程序性知識和價值性知識中,“身”發揮主導作用、“心”發揮輔助作用,重在培養面向情境的現場感知力、時下判斷力和德性踐履力,主要表現為感受實踐、審美實踐、移情實踐、交往實踐、勞動實踐、驗證實踐和道德實踐。當前的中小學之所以要注重“身主一心輔”的實踐,是為了消除認知主義壟斷的影響,此乃矯正“重心輕身”現象的應有之舉。
其二,學科實踐所涵蓋的內容既包括理論知識,也包含經驗知識。鑒于學科實踐是身心參與的能動活動,故而,其所適用的知識不局限于經驗知識,還包含理論知識。理論知識是以符號言語為載體的知識,經驗知識是以原初真實事物為對象、以行動緘默表現為載體的知識。盡管理論知識和現實情境間存在一定的距離,但決不可由此而否定理論知識對擴充直接經驗的獨特價值。盡管經驗學習對直接經驗的積累具有重要優勢,但是囿于個體視域和身體精力的有限性,需要理論符號的補位。然而,理論并非越多越好。例如,精通文學理論的人未必會成為杰出的作家;精通運動力學的人未必會成為優秀的運動員。反過來說,優秀運動員需要了解基本的健康知識、保健知識,卻未必需要精通運動力學;杰出作家了解的寫作手法和文學理論越多,自身的創作能力可能反倒越受限。
其三,學科實踐所參與的過程既包括知識復演,也包括知識遷移。學科知識作為學習活動,既要讓學生親歷認識成果的“再發現”階段,也要使學生體驗認識成果的“再拓展”階段。一方面,在知識復演階段中,學科實踐可一改“先知后行”的理念,以“在行中知”的方式,力求達至“以行習知”和“以行促知”的目標。此處的“行”指身心活動,對技能性知識和品德性知識而言,若不借助“行”,尤其是身體踐行活動,而只是死記硬背,那么學生所收獲的只是“惰性信息”而非“活性符號”,永遠只能是紙上談兵的“符號人”。因而,唯有“在行中知”,學生才能在復演過程中完成對原理性知識的思維推理、對技能性知識的行動體驗,獲得對知識的深度理解和個性轉化。另一方面,在知識遷移階段中,“在行中知”可培養學生面對真實問題、應對突發情況、處理復雜任務的生活智慧,是開啟“以行固知”和“以行擴知”的“鑰匙”,以期推動知識在生活中的轉化力與應用力。
二、學科實踐的價值期待
學科實踐的出現,推動著知識學習從映射、預成、還原、分離取向的被動線性學習,轉變為交互、生成、整體、聯通取向的主動多元學習。以占有結論為目的的被動學習類似于“石筍”的人工打造,以過程體驗為目的的主動學習類似于“竹筍”的有機生長,如此看來,學科實踐的確能夠讓學生學得更牢固、更深入、更豐富。
(一)跨越“映射”取向的藩籬,以“交互”取向喚醒主體意識
“映射”表現著對抽象符號的淺表識記,學習者、學習對象和學習環境彼此分離,學習者折服于恒定唯一的真理,淪為消極被動的接收客體;“交互”表現著對抽象符號的親歷體驗,學習者、學習對象和學習環境相互耦合,學習者建構并創造著更新、迭代的假說,成為積極能動的建構主體。在交互取向的學習觀看來,“認知不是一種外在旁觀者的動作,而是參與在自然和社會情景之內的一分子的動作,那么真正的知識對象便是在指導之下的行動所產生的后果了”[5]184。
學科實踐幫助學生“理解”知識而非“占有”知識,在知識應用與問題解決中化知識為經驗、鑄經驗為素養。杜威( Dewey J)扭轉了單向受動的“經驗”概念,使其同時兼具主動和被動的因素:“在主動的方面,經驗就是嘗試——這個意義,用實驗這個術語來表達就清楚了。在被動的方面,經驗就是承受結果。我們對事物有所作為,然后它回過來對我們有所影響,這就是一種特殊的結合。”[6]153鑒于身心與情境的雙向交互性,學科實踐也體現出活動的發展性:“客觀的物質世界通過人的‘實踐中介的參與,已不再是陌生的、疏遠的、與人無關的感性存在,它本身就是人類實踐的歷史成果,是‘人化的自然;而主觀的精神世界因此也不再是孤立的、抽象的、與現實文化無關的理性觀念、生物本能或‘此在經驗,它本身就是社會實踐的文化成果,是‘自然的人化。”其中,“人化的自然”表現為人不再是對環境的被動順應,而轉變為主動改造,伴隨境遇改變而實現認識成果的可持續發展,此所謂主體客體化;“自然的人化”表現為人在實踐中孕育的能力、觀念、態度、情感、智慧等促進認識經驗的可持續改組、精神意義的可持續增值、生命境界的可持續豐盈,此所謂客體主體化。質言之,對客觀知識的學習絕非打開“百寶盒”提取“現成知識”的過程,只有融入主體性經驗與個性化理解,將二手經驗與一手經驗結合成新的“經驗團”,使其隱含的深層意蘊顯露出來,與個人信念、經驗、情感深度融合,知識的育人價值才能彰顯,學生掌握知識后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二)掙脫“預成”取向的桎梏,以“生成”取向激發創新活力
“生成”并不是對“預成”的完全拋棄,反而是對“預成”的補缺、超越,甚至是修正、替換,“預成”只是“生成”的諸多情況中的一種,正如“簡單性”只是“復雜性”的一種情況、一個方面。學科實踐讓知識處于有序與無序相互關聯、確定與隨機彼此互涉、分形與回歸雙向跨越的“第三空間”。這不僅扭轉了封閉、現成的知識復述觀,而且為開放、迭代的知識分形觀和知識創新觀開辟出多種可能。學科實踐致力于實現從“知如是”到“知如何”的重點轉向,既可激發思維的創新潛力,又可激發身體的創新活力。從過程狀態來看,“推論的探究是連續不斷的;一步跟著一步,利用著、檢驗著和擴充著過去所已經獲得的結論。說得更詳實些,過去的知識結論是進行新的探究的工具,而不是決定它們有效性的準繩”[5]174。同時,考慮到不同學習主體能力的差異,“一切研究即使在旁人看來,已經知道他在尋求什么,但對從事研究的人來說都是具有獨創性的”[6]162。盡管“個體創新”和“人類創新”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程度有區別,但對實踐者個人的發展價值則沒有高低之分。
學科實踐祛蔽知識的“真理幻象”,促使知識學習從“先知后行”的接納性學習轉向“在行中知”的探險性學習。接納性學習將現有知識視作顛撲不破、至高無上、毋庸置疑的“權威”,學生無須對其形成過程進行反思和驗證,只需接受并確信現有結論,對結論記憶得越清楚、復述得越精確,則表明學習成效越好。然而,問題恰恰在于,復雜科學的出現讓確定性走向終結,讓一切看起來早已擁有唯一固定答案的結論具備重新探討的可能。但是,接納性學習卻與復雜科學背道而馳:一方面,這種將結論囫圇吞棗的做法并未讓學生真正理解知識;另一方面,這種將結論全盤接收的做法不僅抑制了學生的批判精神,使其極易被錯誤觀念所蒙蔽,更關閉了知識范式迭代、知識類型延拓的通道。學科實踐的出現,讓學生重新走上探險性學習,它將知識(定理和法則除外)視為待證實和尚待完善的“猜想”,現有結論存在被證偽、改進和優化的可能。因此,學生既要敢于挑戰權威,亦要相信直覺、靈感,更要采取實驗復檢,通過對方案不斷地檢測與調整,提出新穎高效且有理有據的創新方案。
(三)突破“還原”取向的窠臼,以“整體”取向孕育核心素養
傳統要素式教學采取“分裂式思維”,將核心素養視作可拆分和肢解為認知、情感、態度、行動、信念、價值觀等孤立實體要素的簡單組合,把核心素養的培育等同于智育、美育、德育、體育、勞動教育的拼湊疊加。然而,學科實踐卻從“教學做合一”的能動角度,以“系統式思維”,將必備品格、關鍵能力和價值觀念不再當成原子性、零散性、孤立性的要素拼裝或“積木”組合,而是從專題設置和問題驅動的角度人手,調動各要素在處理復雜問題情境中的關聯性與交互性,將大單元、大觀念、大概念的知識結構化整合,從整體維度出發,涵育學科思維、煉化學科表達、強化學科認同、內化學科文化、孕育學科智慧,進而培育整體有機的核心素養。同時,學科實踐還側重對價值觀的培育,以道德信念作為聯通知與行的中介,讓學生在實踐體驗中知知、信知、行知,以期實現真善美的和諧統一。例如,學生對駕駛技能的掌握,不僅要通過交通法規考試,還要掌握必要的行車技巧,但更為關鍵的是要在駕駛中不做違規、違章、違法之事,而這必離不開道德品質的涵育。
學科實踐不再通過肢解概念、分割定義、組合關鍵詞的方式教育學生,而是借助沉浸式的身心體驗活動,幫助學生挖掘知識的內核、領會知識的價值、感悟知識的意蘊。以“公平”為例,學科實踐反對教師以符號講授的方式倒逼學生對“公平”的定義進行無意義的識記,而是通過創設情境、議題討論等手段,助力學生在活動體驗中習得“公平”的實質。例如,教師可創設買粉筆的情境,小賣鋪賣給男生一塊錢一根,賣給女生五角錢一根,讓學生表達感受并探討解決方案。在此期間,盡管教師并沒有直接講授“公平”的含義,但學生卻借助學科實踐,在潛移默化中習得“公平”的內涵。
(四)解除“分離”取向的枷鎖,以“聯通”取向回歸生活世界
學科實踐以“人一知相遇”,彌合生活世界與知識世界之間的裂隙,讓學生在重走知識探究的過程中觸摸歷史、活在當下、展望未來,在從仿真情境向真實情境的過渡中活學活用、一隅三反。學科實踐讓學科知識不再只是枯燥的概念、抽象的符號,而與生活世界中鮮活、生動的事物重建親密關聯。例如,數學中的折扣、比例尺、重量、數量等均有其豐富的生活實例,通過直觀呈現、原生展示、原初體驗,在身心中建立起立體多維的個體理解。以操作實踐為例,從歷時性縱向發展來看,它是個體認識發生的初始階段;從共時性橫向互促來看,它是個體健全生活的必需要素。例如,斤兩、千克,如果學生只靠識別符號,而不去親手掂量、感受重量,則極易被惡意調整的“黑秤”欺騙,欠缺生活智慧。由此可見,教育教學中對身體實踐的關注,能夠讓學生走得更遠、飛得更高,為他們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保障。
學科實踐跨越課堂與生活的鴻溝,通過將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的有機聯通、開放共享,為緘默知識的落地創設機會。正如“沒有人能夠寫出這樣一部關于騎車的說明書,別人閱讀并理解之后,第一次跨上車就能騎著走”,對技能性知識的學習,不能“只思不行”,破解“眼睛看會、手沒會”之桎梏的關鍵,莫過于“具身操練”的回歸。只有在接觸他物、他人、他事的過程中,歷經親手實操、親口交流和親身感受,學生才能真正習得知識。學科實踐并不主張讓學習陷入“只行不思”的陷阱,除了在少數緘默知識的學習中,“思”會阻礙甚至掩抑“行”,對于絕大多數的知識學習,“思行互構”“知行合一”才是正途。總之,學科實踐既回溯了課程的歷史意識,調和焦點事件與背景知識的關系,又顯現了課程的時代價值,促進社會語脈與情境知識的回流,推動學科實踐向真實生活的敞開。
三、學科實踐落地的教學促進策略
學科實踐作為嶄新的學習活動方式,它的實現雖然離不開學生的能動參與,但囿于學生主體意識的未成熟性,尚需要教師的教學引導。這并不是要繁化教導過程、簡化學習過程,而是要適度地給教導做減法、給學習做加法,給困惑深入探究的時間、給身心深度體驗的機會,展開學科知識卷起的“褶皺”,讓學生在親歷經驗聯結建構的過程中實現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盡管不同學科在開展各自的實踐任務時各有側重,但從實踐的共通性來說,仍可從較為宏觀的層面為學科實踐的落地和實踐素養的生成提供建議。
(一)營造真實化實踐情境,催生持續性實踐興趣
興趣作為激活并維系實踐穩定持久的內在動力,有助于學生學習愉悅感的激發。“有價值的活動與快樂之間具有一種耦合關系,這種耦合關系表現在有價值的活動隱含著某種快樂,能夠引導人們從事有價值的活動。”[9]23但是,興趣的喚起不能通過“裹糖衣”或“用快樂行賄”的方式賺取,只能“從個體豐富的生長潛能中自然涌現,并在與事物的關系中顯現出來”[10]50。因而,實踐興趣的催生亟須依憑盡可能貼近真實生活的實踐情境的創設,用興趣活動搭建起聯通舊經驗與新知識的“居間橋梁”。
1.根據實踐驚奇創設情境,以激活實踐動機
“實踐驚奇”是指學生面對嶄新情境時出于詫異與好奇而對實踐情境產生的敏銳洞察與批判質疑。它通常源于遠離平衡態的沖突性條件下所產生的“奇異吸引子”,表現為對初始條件的極端敏感性,這是因為任何細枝末節的改變均可能影響后續過程與最終結果。由于這種變化通常是細小、微妙且轉瞬即逝的,故而,尤其需要教師敏捷地意識到它們,創作出人意料的情節以激活學生的學習驚奇,并迅速捕捉到學生身上的天賦差別。正是因為不同的學生均有其觀念世界和個性差異,所以“教師的解決辦法不是為每個兒童編制相應范圍的練習,而是為水平參差不齊的兒童提供情境,讓他們無論智力結構如何,都能用新的方式了解世界的某些部分”[11]54。唯其如此,學生才能全情投入學科實踐,在貼合最近發展區的問題情境中通過觀察和發問而產生求解的欲望,并主動探究知識的邏輯理路、歷史脈絡和意義系統。
2.根據實踐訴求創建情境,以開啟實踐意向
“實踐意向”是指學生懸置“前見”后,向實踐對象主動投射和主動敞開的實踐意愿。營造滿足實踐訴求的實踐情境,將為開啟實踐意向提供背景支持。生活世界作為“原初的自明性領域”,其中運載著豐富的原初事物,還原并貼合真實生活情境的創設,不僅能讓學生獲得更加直觀、更加具象的原初感知,而且能拉近書本知識與生活世界的關聯,超越課堂教學的邊界。鼓勵學生不只在書本中學語文,更要在自然中學語文;不只在教室中算數學,更要在生活中用數學;不只讓學科被生活喚醒,更要讓生活被學科著色。貼近真實生活的情境創建,將為新知找到學生已有經驗的基點,使其在進入、參與、沉浸于情境期間,引發情感的共鳴,在“人一知”相遇中走向“人一知”互動。
3.根據實踐愿景創生情境,以豐盈實踐知覺
“實踐愿景”是指學生對實踐自由的向往,哈貝馬斯(Habermas J)就將“實踐興趣”置于從“技術興趣”向“解放興趣”躍升的中樞環節。為此,教師亟須從促進學生身心自由發展的目的出發,創設豐盈身心體驗、促使身心解放的實踐情境。鑒于心智活動過剩、身體活動不足的教育現狀,學科實踐依賴的情境應當是助力“知覺”充分涌現的情境體驗場。故而,教師一方面要為實踐情境提供“挺身”與“顯身”的空間,如藝術展示角、實驗操作臺等;另一方面要為實踐情境添置“動腦”與“用腦”的工具,如方案流程圖、報告記錄冊等。身體活動有了心智的輔助,方可讓學生更好地領悟深層的機制與原理,以符號為媒介進行分享與交流;心智活動有了身體的輔助,方可讓學生銜接真實的事物與境況,以身體為手段加以檢驗與應用。
(二)甄選結構化實踐資源,拓寬多樣性實踐選擇
學科實踐的落地還離不開結構化實踐資源的支持,優質有序的實踐資源為學科實踐的開展提供了豐富的選擇。鑒于學科實踐與日常實踐的差別在于學科知識的專業性與系統性,故而,如何選擇與組織學科知識,使之作為學科實踐的支持性資源,成為服務于學科實踐的教導必須直面的難題。
學科知識的挑選宜精不宜泛、宜深不宜淺,須體現出由易到難、由簡至繁、由近及遠的層次性、遞進性的特點。教師既要關注理論知識,又要關注經驗知識,尤其還要關注那些需要教師創設活動情境、學生經歷活動過程才能理解與掌握的知識。教師選擇的學科知識一定是立足本學科體系、圍繞本學科框架、體現本學科精神的基礎知識與核心知識。正如陶行知所說:“一個學校要想培養雙手萬能的學生,自然要多備用的書,少備吃的書,而吃的書中尤須肅清一切烏煙瘴氣的書。”12這就要求教師在選擇學科知識時,應減少事實性知識、增加應用性知識,不僅要包含陳述性知識,更要涉及程序性知識,既給學生的學科實踐劃定價值方向,又為其提供方法參照。例如,當教師在選錄自然科學原理性知識時,不可忽略自然科學實驗性知識,要充分兼顧身與心的不同功用。此外,教師對學科知識的挑選還需結合典型范例,以超越主觀經驗的局限,獲致實踐情境的內在規定性,掌握應對實踐問題的共通性方法論,唯其如此,學生才能在后續的不同情境間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學科知識的組織應遵循如下三重原則:
其一,主題式原則。主題式原則,一方面表現為大概念、大觀念式組織。大概念與大觀念的組織要貫通自上而下的演繹邏輯和自下而上的歸納邏輯,從分形與回歸的雙重制約中,扭轉只見局部、不見整體的窘況。故而,大觀念、大概念的設計既要尋找不同知識節點之間的關系與規律,更要擴展至不同領域之間的交織與生成,通過對學科內部知識的橫向聯通,幫助學生重建經緯交織、系統折疊的經驗圖式。另一方面表現為任務群、任務鏈式組織。這種組織方式以任務問題為驅動內核,通過提出不同年齡和不同年級學生在不同學科中需要解決的關鍵任務,對核心概念與基本原理進行深入解剖與補充,搭建起不斷進階的“概念樹”和“知識網”,推動學生實踐能力的螺旋上升。
其二,個性化原則。與公共性知識組織相比,個性化知識組織為學生的自主發展提供更多選擇空間。密爾(Mill J S)曾言:“人性不是一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規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寧像一棵樹,需要生長且從各方面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的趨向生長和發展起來。”[13]由于不同學生的天賦、潛質、理想均不同,實踐資源如若未能與學生的直接經驗建立銜接,則難以使其內心深處產生共鳴,個性特質也無法充分顯現。故而,在諾丁斯( NoddingsN)看來,“用相同的課程來培養才能截然不同的學生不可能被認作是一種平等的待遇”[14]230 - 231。換言之,由實踐資源組織的課程設置應當是豐富多樣的,是精心為個人裁剪的,而非把每個人都裁剪成平均水平。唯有將不只局限于常模兒童的全部兒童考慮在內,實施針對性的資源組織,才能實現差異化公平。
其三,呈現性原則。盡管人們均生活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并不一定向每個人敞開,因而,選擇實踐式課程資源的目的不是為了遮蓋( cover)世界,而是為了揭示(uncover)世界,教師身為學科實踐的指導者不應代替學生作出實踐的選擇,反而應當賦予學生自由選擇實踐領域的權力。故而,教師應讓充裕多元的實踐資源向所有學生呈現,但無須強求所有學生面面俱到、出類拔萃。換言之,教師摒棄“喂養科學”的呈現式資源組織,旨在“給孩子們提供一種選擇,這種選擇不僅與他們的年齡相適應,有助于實現個性的最佳發展,還能成為他們所接受的公民教育的一部分”[14]232 - 233。同時,不同課程之間并無優劣之分,學生對不同課程的自由選擇亦無高低之別,“開設這些課程并不會讓一個學生變得比其他同學優秀些,但它們標志著一個應該被承認的重要差異”[14]241,助力學生在基于個性的實踐選擇中獲致效能感、成就感、幸福感和意義感。
(三)巧設線索化實踐引導,提升進階性實踐能力
囿于身心發展的有限性,學生學科實踐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必然離不開教師的巧妙指引,根據不同年齡階段學生實踐目的與過程的重點差異,低齡段學生的實踐引導重在保全與呵護實踐興趣,高齡段學生的實踐引導重在理解與洞悉實踐原理。簡言之,教師須把握教導節奏、抓準教導時機,不只幫助學生獲知符號性的淺表語義,更能使學生認知、情感、態度、行為等深層素質結構發生改變。
1.抽象知識心理化,以培育學生的求知精神
面對人類認識“終點”與個體認識“起點”的間距,為促使學生重演新知識的發生過程,教師須將認識成果倒轉回去,將抽象概念進行心理化還原。因而,教師應對既有的學科內容進行適度的解析,竭力尋找其與學生直接經驗相銜接的現象或事物,喚醒學生對善好智慧孜孜不倦的熱望和渴求,以期實現從學科知識向心理經驗的轉化,并保持心理經驗向未知世界的敞開。這是因為“你對自己未知的東西所做出的種種探究決定著你最終將知曉些什么”11]75。例如,教師對“杠桿原理”的學科實踐設計,可營造“一輕一重兩個小孩玩蹺蹺板”的情境,將抽象定理具象化,讓學生在真實感受重量、距離和蹺蹺板的變化中,掌握“杠桿原理”的法則。
2.熟悉知識陌生化,以點燃學生的精彩觀念
教師不宜過早地直截了當地拋擲答案給學生,而應恰如其分地點燃學生的精彩觀念。從教與學的相對獨立的關系來看,教導應該是“告訴學生世界有可能怎樣而非回答世界是怎樣”[15]118,這就意味著教師的教導是將“壓縮”學科知識“泡發”,通過隱藏結論、埋設隱喻、提供線索、敘事回溯等方式,與學生一同去探尋意料之中的知識所隱含的意料之外的復雜性,關注到學生表現的奇異瞬間。教師既要鼓勵學生尋找同一問題的多種可能,也要指引其意識到約定俗成的標準,對除共識性、事實性知識之外的其他知識采取多樣化的評價標準。為此,教師須給困惑以時間、給迷失以機會,拔除一刀切的評價體系,讓學生不再將標準視作唯一的準繩,亦不再對除標準之外的“錯誤”誠惶誠恐、戰戰兢兢,絕對性評價規則的消弭更易促進精彩觀念的誕生。從關心答案到注重過程的轉變,意味著不輕易揭露答案并不是自作聰明的教導花招,而是讓學科實踐得以有效進行的根本所在。
3.符號知識工具化,以鍛煉學生的應用能力
學科知識只有經過學習者融人個人經歷因素的重構,才能真正被感知、被內化、被應用,因而僅憑學科知識的符號表征和思維識記,難以真正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正如地圖冊不能代替旅行,熟記寫作方法不代表寫作能力,若將符號知識作為現成的事實進行簡單復述,只能導致其后果的虛假。學科實踐將符號知識視為處理現實問題的工具,通過學生的親歷體驗鍛煉其應用能力,尤其要強調實踐類型與知識種類的對應性,在彰顯身心關聯性與互促性的同時,勿忘身心各自的功能差異性與不可替代性。為此,教師須將符號知識作為指導性工具而非現成性事實,支持學生在溯源知識原型和復演知識發生的過程中,將知識用作分析問題的手段和解決問題的參照,逐步深化對學科知識的全面認識。
(四)提供鑒賞化實踐評價,孵育差異性實踐智慧
鑒賞化的實踐評價肩負“鑒定”與“欣賞”的雙重使命,是對學生特定情境下合目的性與個體差異性的實踐表現的評價。實踐智慧主要包含心智智慧、身體智慧與價值智慧三維要素,由于實踐智慧中蘊含著共性(采用“鑒定性評價”范式)與個性(采用“欣賞性評價”范式)的雙重制約,鑒賞性的實踐評價自然成為其不二選擇。
1.“鑒賞”從合情境性與差異性兩個方面評價心智智慧
心智智慧主要指借助頭腦思維對情境問題提出思路、制定方案的智慧,由于心智主導的實踐面對的對象主要為間接的理論知識,故而對其評價應關注實踐者的心智對間接經驗的消化、吸收和轉化的成效。一方面,包括對理論遷移應用的合情境性。例如,提問學生兩杯100攝氏度的水倒在一起的水溫是多少攝氏度,如果他們尚未實踐便不假思索地回答200攝氏度,則只能說明“他們已經輕而易舉地理解如何將測量結果相加,但是,從來沒想過什么時候或者是否要將測量結果相加”[11]80,這種表現便是學生回答的去情境性甚至反情境性。另一方面,包括對理論擴充改進的差異性。實踐者在將理論應用于不同情境時,會采取不同視角、不同方法、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尋求解決方案越是與眾不同,表明學生的創新能力越強。質言之,對合情境性的評價,采取“鑒定”的范式,對差異性的評價,采取“欣賞”的范式,二者的結合才能較為完整地反映心智智慧的情況。
2.“鑒賞”從合規則性與風格性兩個方面評價身體智慧
身體智慧主要指借助肢體行為對情境問題進行感知實操、動手創作的智慧。由于身體主導的實踐面對的對象主要為原初的生活世界,故而對其評價應關注實踐者的身體對真實事物的接觸、感受和統覺的程度。一方面,包括其與真實世界“對話”的風格性。所謂“風格性”,即對自身個性潛質的充分彰顯,主要表現為文學實踐、藝術實踐、體育實踐、勞動實踐中超越對專家或他者的模仿而走向個人風格的塑造。另一方面,包括其與真實現象“打交道”的合規則性。身體智慧的衍生雖然是對客觀知識邊界的軟化,但也并非完全拋棄客觀性與科學性。受利己論或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顛倒黑白的任意操作與縱欲癲狂,是不合規的身體智慧。對合規則性的評價,采用“鑒定”的范式,對風格性的評價,采用“欣賞”的范式,二者相互補充、彼此制約且不可替代。
3.“鑒賞”從合群體性與自主性兩個方面評價價值智慧
價值智慧主要指借助道德品質對情境問題開展道德判斷、道德行為的智慧。除置身特定的道德情境外,學科實踐中的價值智慧主要體現為實踐共同體中成員間的互動、交流、合作與協商。其間,學生的表現不僅包括對自身觀點的表達與辯護,還包括對同輩觀點的傾聽與回應。前者表現為自主性,適宜用“欣賞”范式;后者表現為合群體性,適宜用“鑒定”范式。誠然,合群體性并不意味著對權威的曲意逢迎,自主性也不代表著對視域的故步自封。索爾蒂斯(Soltis J F)曾言:“教育的職責不僅僅是傳遞現有的知識和探究方法,而且還要形成個體和群體愿意聽取并批判性地檢驗未來新的知識主張、愿意探尋改進方法論與手段的種種途徑的意向。”[16故而,學科實踐所依附的實踐共同體也應以此作為奮斗目標。達克沃斯(Duckworth E)用亞歷克向同學提出、辯護自己想法,并在與他們討論的過程中匡正自身原有觀點的案例,也在表明:“提出自己的觀點,接受別人的審視,這種勇氣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它和觀點本身是否正確并無關系。亞歷克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正是他慣于提出自己的觀點并為之辯護才為以后提出正確答案鋪平了道路。其他同學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他們不敢質疑亞歷克觀點的話,無論是私下還是當眾,他們將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的答案。”[11]74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
[2]崔允郭.學科實踐:學科育人方式變革的新方 向[J].人民教育,2022(9):30 - 32.
[3]羅祖兵.論課堂教學中五育融合的學科立場 [J].課程·教材·教法,2022(5):45 - 53.
[4]黃英杰,王冬.幼兒運動興趣:內涵、價值意蘊 及實踐路徑[J].教育與教學研究,2022(8):1- 12.
[5]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 [M].傅統先,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
[6]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7]鄒廣文,當代文化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81.
[8]墨蘭德,何者隱而不顯,何者顯而不隱[M]//楊 國榮.思想與文化:第4輯.蔡志棟,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46.
[9]朱鏡人,葛琪,論學校教育中有價值的活動:基 于彼得斯分析教育哲學觀[J].教育與教學研 究,2022(9):17 - 27.
[10]樊杰,蘭亞果,杜威基于關系與生長視角的興 趣與教育理論[J].全球教育展望,2018(5):47 - 55.
[11]達克沃斯.精彩觀念的誕生:達克沃斯教學論 文集[M].張華,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2]華中師范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陶行知全集: 第2卷[Ml.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73.
[13]密爾.論自由[M].許寶驥,譯.北京:商務印書 館.2020:70.
[14]諾丁斯.幸福與教育[M].龍寶新,譯.北京:教
育科學出版社,2014.
[15]魏善春,李如密.從“實體思維”到“事件思維”:過程哲學視域中的教學生活圖景[J].教育研究,2017(6):115 - 124.
[16]索爾蒂斯.教育與知識大概念[M]//瞿葆奎. 教育學文集·智育,唐曉杰,譯,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3:70.
(責任編輯:彭文彬)
Disciplinary Practice as Learning Activities :Connotative Interpretation, Value Expectations and Teaching PathsHAN Xuetong(College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an actively engaging cognitive activity, the complete practice should be a dual structure composed ofmind and body, promoting but also restricting each other. Disciplinary practice is a specific practic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deriving practice convergence, focusing on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adhering to the disciplinary stance . I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awaken subject consciousness with "interactive" orientation, to active innovating vigor with "generative"orientation,to nurture key competence with "holistic" orientation, and retum to live world with "connective" orientationthrough active experiences in participating in key activities of the discipl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sciplinary practicecan be realized through creating actual practical situations, selecting structured practical resources, cleverly setting thepractical guidance with clues, providing appreciative practical evaluation, and more. Therefore, disciplinary practice cantake place and then through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interests, broadening of practical choices, improvement of practicalabilities, and incubation of practical wisdom, knowledge can truly be brought into the lives of students.
Key words : practice; physical and mental practice; disciplinary practice; leaming activities ; practical tea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