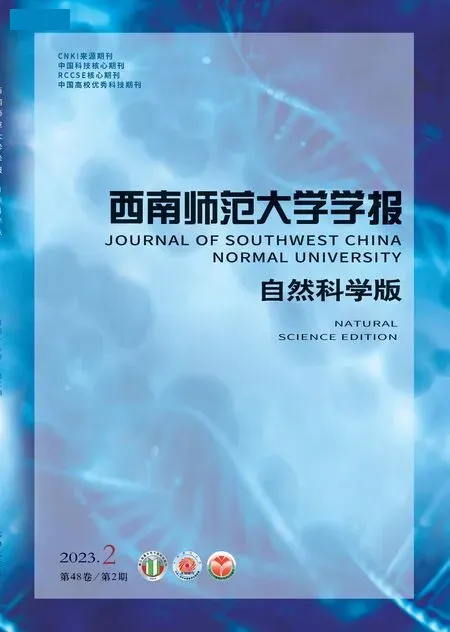偶數階極大子群均為CBNA-子群的有限群①
唐康, 劉建軍
西南大學 數學與統計學院, 重慶 400715
本文僅研究有限群, 涉及的群論術語和符號都是標準的.
近年來, 利用某些特殊子群的性質來刻畫有限群的結構是眾多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文獻[1]通過研究群G的非冪零自中心化子群的TI-性及其次正規性, 給出了G的所有非冪零子群皆次正規于G的判別準則. 文獻[2]通過研究群G的完全Hall-σ集中子群及其極大子群的σ半次正規性, 給出了G是σ可解群和超可解群的若干新的判別準則. 文獻[3]對恰好具有2個非交換真子群的有限群結構進行了刻畫. 文獻[4]研究了四極大子群都弱s2-置換的偶數階有限群的結構.
本文研究了有限群的兩類覆蓋避免子群, 得到了群G的p-超可解和p-冪零性質的一些結果. 設H為G的子群, 如果對任意的x∈G有x∈〈H,Hx〉, 則稱H為G的反正規子群. 反正規子群作為正規子群的一個對偶的概念, 在研究子群的嵌入性質對有限群結構的影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文獻[5]刻畫了每個子群正規或反正規的群. 文獻[6]分類了滿足正規或反正規的CLT-群. 文獻[7]引入了介于正規和反正規之間的子群: BNA-子群.
定義1[7]設H為G的子群, 如果對任意的x∈G, 有Hx=H或者x∈〈H,Hx〉, 則稱H為G的BNA-子群, 此時H也稱作在群G中BNA-正規.
文獻[7]證明了: 如果群G的極小子群和4階循環子群均為BNA-子群, 則G超可解, 并對滿足所有素數冪階循環子群均為BNA-子群的群進行了刻畫.
最近, 文獻[8]定義了CBNA-群.
定義2[8]設G為有限群, 如果G的所有極小子群和4階循環子群均為G的BNA-子群, 則稱群G為CBNA-群.
文獻[8]給出了極小非CBNA-群的完全分類. 本文將沿著上述方向繼續研究BNA-子群對群結構的影響. 為方便敘述, 我們引入以下概念:
定義3設G為有限群, 如果G為偶階非CBNA-群, 且G的所有偶數階極大子群均為CBNA-群, 則稱群G為EBNA-群.
本文將給出EBNA-群的結構刻畫. 我們證明了如下定理:
定理1設群G為EBNA-群. 則G可解, |π(G)|≤3, 且G滿足下列條件之一:
(i)G為極小非2-冪零群;
(ii)G為2-冪零的極小非CBNA-群;
(iii)G=P×N, |P|=2,N為G的2′-Hall-子群. 當|π(G)|=2時,N為極小非CBNA-群; 當|π(G)|=3時,N為CBNA-群.
引理1[7]設G是一個群,H≤K≤G且N?_G. 若H是G的BNA-子群, 則:
(i)H是K的BNA-子群;
(ii)HN是G的BNA-子群;
(iii)HN/N是G/N的BNA-子群;
(iv)G的每個極大子群都是G的BNA-子群.
引理2[7]設H是群G的BNA-子群, 則:
(i)H的正規閉包HG要么是H, 要么是G;
(ii) 若H次正規于G, 則H正規于G.
設H是群G的子群. 如果對任意的x∈G, 有H與Hx在〈H,Hx〉中共軛, 則稱H為G的類正規子群. 顯然, 正規子群和反正規子群都是類正規子群. 而我們可以得到類正規子群和BNA-子群的如下關系:
引理3設H是群G的子群. 則下列命題等價:
(i)H為G的BNA-子群;
(ii)H為G的類正規子群, 且對G的任意滿足H≤K≤G的子群K, 有K≤NG(H), 或者NG(H)≤K.
證先證(i)為(ii)的充分條件. 顯然H為G的類正規子群. 假設存在x∈NG(H)K且y∈KNG(H), 則xy?K且H≠Hxy. 而〈H,Hxy〉≤K, 這與H為G的BNA-子群矛盾.
再證(ii)為(i)的充分條件. 假定存在x∈G滿足x?〈H,Hx〉. 則由H為G的類正規子群知Hx=Hy, 這里y∈〈H,Hx〉, 即xy-1∈NG(H)〈H,Hx〉. 由已知條件可得
〈H,Hx〉≤NG(H)
故y∈NG(H), 這意味著H=Hx. 所以H為G的BNA-子群.
引理4[9]設群G是一個CBNA-群. 則G超可解.
引理5[10]設p′-群H作用在p-群G上,
若H平凡作用在Ω(G)上, 則H平凡作用在G上.
引理6[11]設群G的所有p階子群均為G的正規子群, 其中p為一個固定素數. 若|Z(G)|p≠1, 則G的所有p階元均屬于Z(G).
引理7[12]設群G存在2階無不動點自同構, 則G為交換群.
我們將通過完成以下幾個定理的證明來證明定理1:
定理2設群G為EBNA-群, 則下列命題之一成立:
(i)G為極小非2-冪零群;
(ii)G為2-冪零的極小非CBNA-群, 且|G|2>2;
(iii)G為2-冪零的EBNA-群, 且滿足|G|2=2和|π(G)|≤3.
證令M為G的任意極大子群. 若M為奇數階, 則顯然M為2-冪零的; 若M為偶數階, 則由已知可得M為EBNA-群. 根據引理4,M為超可解群, 故M為2-冪零群. 因此,G的任意極大子群均為2-冪零群, 即G為2-冪零群或極小非2-冪零群. 接下來我們只需考慮G為2-冪零群時的情形.
情形1 |G|2>2.
由于G的2′-Hall子群的子群不可能為G的極大子群, 故G的極大子群必為偶數階. 因此,G為極小非CBNA-群.
情形2 |G|2=2.
設
π(G)={p1, …,pr} 2=p1<… 由于G可解, 所以G存在Sylow系, 我們記之為{P1, …,Pr}, 這里Pi∈Sylpi(G). 假設r≥4. 令 其中i=2,…,r. 由已知條件和引理1,P1為每個Gi的BNA-子群. 我們斷言NGi(P1)=P1,Gi. 令 K=Giπ(K)={q1, …,qr-1} 其中 2=p1=q1<… 則K有Sylow系{P1=Q1, …,Qr-1}, 這里Qi∈Sylqi(K). 令 其中s=2,…,r-1. 由引理3, 我們有NK(P1)≤Ks或Ks≤NK(P1). 若對于任意的s都有NK(P1)≤Ks, 則有NK(P1)=P1. 如果存在某個t, 有Kt≤NK(P1), 則引理3再次說明 Kl≤NK(P1)l∈{2, …,r-1}{t} 因此 NK(P1)≥KtKl=K 這就說明了NK(P1)=P1,K, 斷言成立. 如果NGi(P1)=Gi, 則由引理3必有P1?_G; 如果NGi(P1)=P1, 則必有NG(P1)=P1. 令A為G中的奇數階極小子群. 由引理2及G為2-冪零群, 可知A?_G. 不論哪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說明G是CBNA-群, 這是一個矛盾. 極小非2-冪零群與極小非CBNA-群的結構分別由文獻[13]與文獻[8]給出. 當π(G)={2,q}, 我們可得以下結論: 定理3設群G=PQ為EBNA-群, 其中P為G的2階子群,Q為G的Sylowq-子群. 則下列命題之一成立: (i)G=〈a,b,c|a2=bq=cq=1,ba=b-1,ca=cb=c〉; (ii)G=P×Q且Q為極小非CBNA-群. 證首先證明群G為超可解的. 當G冪零時, 顯然(ii)成立. 不妨設G非冪零. 令K/L為G的主因子且滿足K≤Q. 則K/L為初等交換q-群. 由文獻[13]得 Q=F(G)≤CG(K/L) 故G在K/L上誘導的自同構群的階為2. 再由文獻[14]的引理1.3,K/L為q階循環群. 顯然,P作用在Q上, 也作用在Q/Φ(Q)上. 由完全可約定理得 Q/Φ(Q)=V1/Φ(Q)×V2/Φ(Q)×…×Vd/Φ(Q) 其中Vi/Φ(Q)為Q/Φ(Q)的q階P-不變子群,i=1,2,…,d. 令 則Qi為Q的P-不變的極大子群. 由假設及引理2,PQi為CBNA-群, 且Qi的任意q階子群均為PQi的正規子群. 接下來我們分兩種情形來討論: 情形1 存在k使得CQk(P)≠1. 令x為CQk(P)中的任意q階元, 則x∈Z(PQk). 由引理6,Qk的所有q階元均屬于Z(PQk). 由于Qk為P-不變q-群, 且應用引理5, 我們可以得到PQk=P×Qk. 因此 [P,Qj∩Qk]=1 [P,Φ(Q)]=1j≠k 假設|Q/Φ(Q)|>q2或Φ(Q)≠1. 再由引理6, 得到[P,Q]=1, 所以G冪零, 這與我們的假設矛盾. 因此Q為q2階初等交換群. 易驗證G滿足(i). 情形2 對任意k都有CQk(P)=1, 但CQ(P)≠1. 由CQ(P)∩Qi=1知|CQ(P)|=q. 令V=CQ(P)Φ(Q). 則V為Q的P-不變真子群, 從而PV為CBNA-群. 假設Φ(Q)≠1, 則由引理6, 我們得到[P,Q]=1, 從而G冪零, 矛盾. 因此Φ(Q)=1. 重新取V1≤CQ(P), 與情形1類似, 易證G滿足(i). 最后我們假設π(G)={2,r,q}, 得到如下結論: 定理4設群G=PM為EBNA-群, 且M=RQ, 其中|P|=2,R和Q分別為G的Sylowr-子群和Sylowq-子群. 則下列命題之一成立: (i)G為極小非CBNA-群; (ii)G=P×M且M為極小非CBNA-群. 證由于P為G的2階Sylow子群, 故G為2-冪零群, 即G存在正規2-補群M. 由G可解知G存在Sylow系{P,R,Q}. 當CM(P)=1時,P為M的一個2階無不動點自同構. 由引理7,M交換, 故M為CBNA-群, 從而G滿足(i). 下面假定CM(P)≠1. 由于PR為CBNA-群, 所以R的任意r階子群均為PR的BNA-子群. 由引理2,R的任意r階子群均在PR中正規. 若r||CM(P)|, 由引理6,R的所有r階元均屬于Z(PR). 再根據引理5, 我們可以得到PR=P×R, 從而CR(P)=R. 同理, 若q||CM(P)|, 則PQ=P×Q. 故有rq||CM(P)|, 即G=P×M. 因此PH為CBNA-群, 其中H為M的任意真子群. 因此M為極小非CBNA-群, 故G滿足(ii). 不失一般性, 不妨設 CR(P)=RCQ(P)=1 則 NG(P)=CG(P)=PR 因|P|=2, 由Frattini論斷知 G=NG(P)PG=PRPG 故Q≤PG. 又由 PG=〈Pg:g∈G〉=〈Px:x∈Q〉≤PQ 可得PG=PQ. 由引理2,P?_PQ, 故CQ(P)=Q, 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