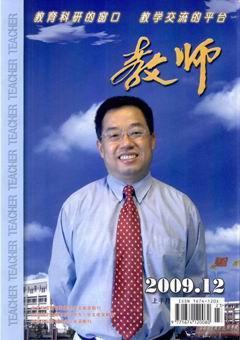言語感悟——語文閱讀教學的鑰匙
譚紅根 彭文玲
摘要:在新課改中,中學語文閱讀教學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許多教師覺得無從下手。本文提出語文閱讀教學應從言語感悟開始,以此為抓手,去有效開展閱讀教學。
關鍵詞:言語;語言;感悟;對話;體驗
夸美紐斯說過:“一切知識都是從感官的感知開始的。”我認為,閱讀教學是從言語對話的體驗開始的。
閱讀是對信息理解和接受的一種思維行為。就中學語文閱讀教學而言,以語言為唯一的鑰匙去解讀文章,快速、有效地對問題做出判斷,是中學語文教學的寶貴經驗。然而,在新課程改革中,有不少的語文教師或過分關注對作品的整體把握,或過度關注探究性學習,或過分關注靜態的文本,而忽視了對言語或語言的感悟,從而使學生走入了“主觀揣摩”的迷宮,無法真正地披文入情,產生真實的體驗感。其實新課標有“閱讀優秀作品,品味語言,感受其思想、藝術魅力,發展想像力和審美力”“根據語境揣摩語句含義,理解結構復雜、含義豐富的語句,體會精彩語句的表現力”等的表述。因此,閱讀是主體從言語作品中獲得意義并滋潤精神的活動過程。語言品味是既能讓學生理解文本獲得人文素養,又能增加思維能力,增強語感能力的有效途徑。
語言是能指,言語是所指;語言是靜態的,言語則是動態的。在閱讀教學中,我們必須從作品語言品味切入,使之還原成為言語意義,從而進行對話與體驗。例如,陸仙霞老師教小說《哦,香雪》時,并沒有生硬地從小說的人物、環境、情節的要素入手,而是從語言的角度切入賞析。以“五彩繽紛”一詞作為全文的抓手提問,“五彩繽紛”的內涵是什么?課文哪些內容體現了“五彩繽紛”?這句話在文章里起了什么作用?如果用“立竿見影”“驚心動魄”“刻骨銘心”替代“五彩繽紛”可以嗎?在這一系列討論中,人物形象及作品的主題自然凸現出來了。然后又抓住題目中“哦”字進行語言賞析,問學生“哦”字為什么不用“哇”“啊”“嘿”“嗯”字。通過討論,同學們馬上可感受到“啊”過分大氣,小山村、小姑娘、小火車站、小事情,用“啊”來感嘆不妥。“哇”太現代化、洋氣,與閉塞的山村不符。“嘿”太隨意輕松,我們只要讀一遍《哦,香雪》,就會發現文中的情感是非常復雜的。“嗯”只是表贊許,簡單化了。只有“哦”字,含蓄凝重,充滿深情,意蘊豐富,既有同情、贊嘆,又有對小山村姑娘們追求現代文明的不容易的感嘆,能使人聯想到許多香雪們在變化著。
再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的教學,從“無限的趣味”這一言語感悟入手,將隱藏在語境深處的精義挖掘出來品讀。在一般情況下,“無限的趣味”讓人想到的一定是十分奇特的、罕見的、美妙的事物,但是,魯迅明明說,這里只是菜畦、石井欄、皂莢樹、桑椹、蟬、黃蜂、叫天子。可以想象,成年人肯定覺得沒有什么趣味,但是,魯迅卻說:“翻開磚來,有時會遇到蜈蚣;還有斑蝥”,這一切,都是有“無限趣味”的證據。我們把它還原一下,在成年人心目中,蜈蚣是毒蟲,斑蝥的俗名叫做屁蟲,和“樂園”“趣味”不但沒有關系,反而是很煞風景的,而魯迅卻特別強調斑蝥放屁的細節:“用手按住它的脊梁,便會啪一聲,從后竅里噴出一陣煙霧”。這什么“趣味”呢?還要說“無限”!是不是應該改成:“雖然有點可怕,但是在我當年看來,還是挺好玩、挺有趣味的。”這樣一來,從表層語義來說,好像是用語更恰當了,但是,從深層的含義來說,卻大煞風景了,因為,這樣一來,就沒有孩子氣的天真、好奇和頑皮了,而是大人的感覺了。
在教學中,要善于從作品文本中抓住那些異乎尋常、不合乎自我習慣的語言表達,抓住不同版本的不同語言等,進行言語品味,你的教學也許會鮮活而富有情趣。葉圣陶先生在談到閱讀教學時曾說:“文字是一道橋梁,這邊的橋堍站著讀者,那邊的橋堍站著作者。通過了這道橋梁,讀者才和作者會面。不但會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也就是說,閱讀其實是讀者滿懷深情地踏上語言這道橋梁,去晤見作者,并觸摸作者靈魂的過程,也是讀者默默地與作者進行心靈對話,獲取智慧、經驗和情感體驗的過程。
要通過語言與言語,正確地與文本對話,科學地解讀文本,既要體現文本的人文性、藝術性,又要體現出工具性、技術性。尤應注意當前那些被炒熱的情感、價值之類的人文目標,應該具體而自然地融化在文本本身的解讀過程中,融在反復吟讀、品味領悟、比較、探究之中,而不是生硬地注入,更不應是時髦的裝飾。只有在準確解讀文本語言的基礎上,才能深入剖析文本的人文內核。進而提高讀者的人生境界,真正實現文本的教育教學價值。
(作者單位:譚紅根湖南省株洲市第四中學;彭文玲湖南省株洲市第十九中學)